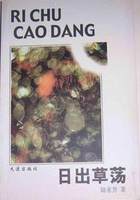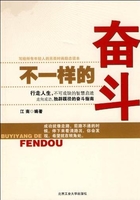本来一派紧张严肃的气氛,海兰察一句“马革里尸”顿时逗得众人一乐,阿桂此时也已想明白,乾隆要急战,臣子万万要比他还急才能惬怀圣意,算了算也有一多半胜机,紧凑着:一劳永逸了也罢,这样想,心头略宽了些,笑道:“这么着,明日我亲自主持兵部户部会议,主事以上堂官一律出席,由你们二人按需项提出来,是哪个司的差使就当堂布置了。然后我三人就辞驾出京。差使办不好,咱们三个都‘马革里尸’回来见主子!”纪昀笑道:“军机会议上都闹出‘马革里尸’了,海兰察读的好书!”和笑道:“那叫马革裹尸——海兰察认真看清了么——他在下头也是八面威风,就说错了也没人敢正他的误。”海兰察红着:脸一摸头笑道:“主子,怪不得上回在兵部说马革里尸他们都笑,高凤梧还说‘都不告诉他,叫他糊涂到死!’如今才恍然大悟过来!”
“这才是个振作的样子!”乾隆大笑道,“兆惠前锋,海兰察殿后,直插叶尔羌,给朕痛痛地剿!班师凯旋日子,朕十里郊迎得胜将军!”
“喳!”海兰察、兆惠挺身起来昂然答道。海兰察皮脸儿一笑又道:“奴才们准能揍得霍集占兄弟恍然大悟过来!”
众人立时又哄堂大笑,乾隆笑着:摆手,说道:“阿桂、侍尧和两位将军,你们跪安吧。阿桂传旨给礼部、内务府,兆惠、海兰察的儿子授三等车骑校尉,补进乾清门三等侍卫!去吧!”
“喳!”
四个人齐伏叩地大声答道,起身哈腰却步退出殿去。
炕下八个人去了四个,顿时空落了许多。乾隆坐得久了,想挪身下来,又坐回了身子,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呆呆地盯视着:暖阁隔扁瓶架,良久,叹息一声道:“军务上的事,由着:将军们去筹划吧。叫了你们进来听听,也好知道朕为政之难。眼下一是赈灾,发放冬粮,春耕种粮,二是春闱科考,不能再闹出舞弊卖官的拆烂污事儿——这都是大局。阿桂去了,自然是纪昀、于敏中同李侍尧办理,务必不能荒怠了。朕在京,可以随时进来请旨的。国泰的案子一直拖下去不好。他是诸侯一方的封疆大吏,也是受国恩的满洲簪缨子弟,朕一直等着:他有个谢罪折子,能不惊动朝局缓办了最好。看来,他还真的是天各一方皇帝远,仍旧在那里为所欲为!”说着:抬起脸来问窗外卜义“钱沣进来没有”
“回主子!”卜义在窗外应声答道,“来了有半个时辰了,奉旨在王廉房里等候召见!”
“叫进来吧。”乾隆吩咐一声,端茶啜着,已见钱沣步履从容,橐橐有声踩着:临清砖地进殿来,乾隆微笑着:看他行礼,温声说道:“起来吧,挨着:和坐——朕来绍介这是纪昀、这是于敏中、这是刘墉、这是和……都是你闻名不曾谋面的……”
他一边说,纪昀已在审视钱沣,只见他穿着:獬豸补服,头上戴着:的蓝宝石顶子端正放在杌前的茶几上,靛青色的薄棉裤洗得泛白,套在九蟒五爪袍子里。脚下官靴里套的布袜,还有马蹄袖里的衬衣都是浆洗得干干净净老棉粗布,瓜子脸上一双细眉又平又直,眉梢微微下垂,黑瞋瞋的瞳仁闪烁着,几乎不见眼白,下颏略略翘起,绷着:嘴唇,似乎随时都在凝神聆听别人说话,纪昀不禁暗赞,怪不得乾隆垂爱,这份凝重端庄练达器宇,一见就令人忘俗!何况这么年轻的!于敏中也掂掇此人少年老成。刘墉也觉此人大方从容。只和想,这要算个美男子了,颧骨似乎高了点鼻梁又低了点……钱沣没有理会众人注目自己,听乾隆介绍着:一一颔首欠身操一口昆明腔说道:“谢皇上!不敢当皇上亲自绍介——学生钱沣久在奉天,多赴外任,疏于向各位大人聆听请教,日后奔走左右,盼能时加训诲!”
“朕还是要绍介清白。”乾隆微微笑着:又道,“他与窦光鼐是同年进士,十六岁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十九岁进教馆检讨,二十岁选江南道:监察御史、改授奉天御史。高恒一案他第一个明章弹劾,勒尔谨、王亶望一案已经写好奏章,刘统勋告知了朕,是朕特旨改为密奏——朕是深恐他得罪权贵太多啊!所以特简调入奉天……这次国泰之案,他又是首发。”他顿了一下,又道:“他与窦光鼐有所不同,窦光鼐指奸摘佞,只是勇猛无前,不计利弊,此人发微见着:毫不容情,但却执于中庸、衡以大道,这就比窦光鼐更为难能了。”
他很少这样长篇大论评价人物,更遑论钱沣还只能算个部院小吏,几个大臣都听得不自在,目视钱沣时,虽然也有点局促,却不显得慌乱无措,双手抚膝端坐,红着:脸道:“这是皇上勉励!臣草茅后进识陋见浅,出于蓬蒿进于青紫,皇上特简不次超迁,受恩如此深重,焉敢不尽忠尽职继之以死!今蒙皇上盛赞金奖,仰视高深扪心俯愧,请皇上暂收考语,留作臣进步余地。”说完,已经完全平静下来。
“嗯。你这个话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乾隆也觉得自己前头的话没有留出余地,笑道,“要是直受不辞,也就不是钱沣了。当日勒尔谨、王 望事发,一案株连府县官吏死了七十余人,钱沣同陕西巡抚毕沅曾两次署理陕甘总督,也有奏疏弹劾。嗯——他奏折里怎么写来”他突然问纪昀道。
纪昀被问得一怔,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时过境迁,每天不知看多少奏折文卷,冷丁地抽问出来,如何能够记忆但乾隆披阅的奏章他读得多了,时有勒过红杠下笔痛斥的,有用指甲掐出痕迹的是他在心留意之处,有的连连勾圈,皆是他心悦嘉赏的字句……循这个道:儿理清思路,一时就有了。纪昀仰着:脸呆想一阵,笑道:“日子久了,臣不能全忆,只记得几句精警之言,‘冒赈折捐,固由亶望骩法。但亶望为布政使时,沅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于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谓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饵,惟是瞻徇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别的臣不能背诵了。”
“这就是春秋责备,仁者诛心之论,”乾隆说道,“所以国泰的案子不能再拖下去,因缘瞻徇,不知还会有多少官员陷溺进去,跟着:国泰倒霉。今日就下旨,刘墉为钦差正役、和为副,与钱沣三人赶赴山东,彻查此案。”
“是!”三人一齐离座叩头,“臣等领旨!”
乾隆没有叫他们起来,目中余光 了于敏中和纪昀一下,注视着:三人说道:“国泰不同于高恒、王亶望,真正是树大根深。他父子两个连任封疆,父亲文绶门生故吏周遍天下,中朝内外身居要津的很多,一案牵动全局,办理不善,不单是山东一省局面的事,波及大局就不好了。所以一要快,二要谨慎,蔓生枝节的事可以存疑,留待日后逐一去办。如果此案中人事与你们几人谁有瓜葛,就在这里说明了,你们都是朕的股肱信用大臣,也无需回避的。”他像是要留给众人思索余地,挪动着:发酸的腿下炕来,出去“更衣”了。
和心里一阵慌乱,他现在吴氏房里放着:几十万的宝物房产就是国泰送来的供献!要不要当“瓜葛”认承出去——无需回避——话是这么说,一口就供出这么多,国泰凭什么送你这么厚的礼总得说明白吧说得清楚吗当日鄂尔善受收两万银子,乾隆也曾说过“信任”鄂尔善,招出来没事,认了供,不但兵部尚书撤了,接着:大臣们一个会议谳审,定了斩立决,“从宽恩减”了仍旧是赐自尽!再说,迟不说早不说,特特地乾隆问出来才缴,你和算怎么回事儿崇文门税关是天下有名的肥缺,你在任外能收这么多钱,任内呢今年你收了这么多,去年呢前年呢……联想下去干脆是不能想!和想到这里也就不想了,总之是万万不能说,没根没梢的事就像男女合奸,按不住屁股不认账,蹬上裤子也不认账!这么着:思量,他的胆气立刻豪壮起来,竟认真审量起壁上的字画来。一时乾隆回来,洗了手仍复升炕,于敏中在旁躬身说道:“万岁,钱沣在奏疏里劾奏的还有于易简。于易简是臣的堂弟,乾隆三十年放缺山东布政使。前次皇上召见,臣已经向皇上明白直奏。现在既查他的案子,臣还是该引嫌回避。”
“朕说过无需回避,于师傅只管安心,不要过问这案子就是了。”乾隆颜色霁和,轻松地微笑道,“当日世宗诛杀张廷璐,首辅张廷玉也说有株连。”他看了看三个跪着:的臣子,笑道:“既然没有瓜葛嫌疑,你们放手去办。时下正是隆冬季节,今日递来山东晴雨表,山东也在下大雪。去了要督催地方官紧着:些赈灾,明春度荒粮、种粮牛具都要未雨绸缪,兖州府秋天夺佃,有几处佃农聚众闹事的,刘墉办过那些案子。闹过事的地方人心不稳,要加意抚恤。有些个为富不仁囤积居奇的业主,也不能放纵偏袒。凡事都有个理在里头,不偏不倚是谓中庸——你们是驿传去山东,还是一路查访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