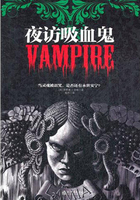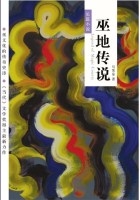“进来!”康熙大声说道。三个大臣躬身而入,眼见康熙无虞,不由地吁了一日气,依次跪了。
这时午牌刚过,地震来得更凶。巍峨的五风楼、大大小小的民房、一街两行商店、殿宇馆客随着大地一起一伏婆娑起舞;天空中黄尘与暗红的彩云搅在一起翻滚,笼罩得宇宙一团昏黑;一会儿风雹雷电齐作,紫蓝色的闪电照着街衢上一张张惊惶恐怖的面孔。从永定门、哈德门到东直门一带人烟稠密的地方,人们扶老携幼偎依在一起,孩子在母亲怀抱里挣扎着大哭大叫,大人们却一个个用呆滞的目光仰望苍穹,祈佑平安。远近不时传来高房危楼轰然倒塌的声音,整个北京城鸡飞狗叫、孤鸣狼嚎似地惶惶不宁。
一等侍卫善扑营总领魏东亭与表妹史鉴梅行合卺礼才过三天。由于史鉴梅娘家已没有人,熊赐履夫人便把她接了去,权作回门礼。原说好了于明日回来,出了这种事,史鉴梅哪里还顾得了这些?便从熊家马厩里拉出一匹狂躁的枣红马,勒一勒缰绳飞身而上,狂抽猛打驰回虎坊桥——魏东亭的官邸。
刚过西华门,却见自己的丈夫魏东亭手挥宝剑正与一个双手持戟的红顶子武官在马上厮拼,便勒住了马在旁凝神观看。
那个武官四十多岁,足比魏东亭高出一个头,半截铁塔样地稳坐战骑,面白无须,眉如卧蚕,身手十分矫捷,一般烂银画戟舞得风车一般。魏东亭是康熙跟前武功最高的侍卫,却因不善马战,无论怎样勾刺劈挑,总占不到上风。史鉴梅因为空手,不及细想,便从头上拔下一枝银簪,在手里掂掂分量,权作暗器,一甩手便向那人后心飞去。不料那人着实了得,竟在马上凭空向后一翻,银簪“嗖”地平射过去,正好磕在魏东亭的剑上,被打得无影无踪。史鉴梅不禁大怒,“啪”地声解开束腰金带,纵马一跃加入战团。正打得难分难解,忽听城门口一阵洪钟般的笑声“哈哈哈哈……虎臣贤弟,新婚燕尔,夫妻竟有如此兴致,共战关西马鹞子!”
“图军门!”
三人一齐住了手,见是九门提督图海戎装佩剑,手中赉着诏书,大声喊道“圣旨:着王辅臣即刻觐见!”
魏东亭与王辅臣联袂而入。此时大震已经过去,储秀宫附近已完全恢复了平静。时而袭来的余震,大殿窗棂门扇虽然仍旧发出咔咔的声音,已不再那么吓人。丹墀外二十名宫女、四十名太监按序排着,众星拱月地护在康熙周围,两柄宝扇、一面长纱屏围在身后。杰书、熊赐履和索额图挺身长跪在一旁,一切与日常朝会没有两样。
魏东亭因有数日不上朝了,见康熙行了一跪一叩的礼,便起身立在康熙身旁。王辅臣是第一次入觐,在陕西平素闲谈时,虽也听说过一些宫闱秘闻,圣上如何私聘落第举人伍次友为师,如何庙谟独运,用魏东亭一干新进少年智擒鳌拜,可是现在真的与这些人相见,激动之余又有点儿好奇。他一边行三跪九叩觐见礼,一边偷眼打量,见康熙脚蹬青缎凉里皂靴,身着酱色江绸丝绵袍,外套着石青单金龙褂,浑身丝毫不带珠光宝气,颀身玉立,风度娴雅,含笑看着他行礼。康熙又见王辅臣不住地瞟自己,便欠了一下身子,笑道:“王将军,请起来说话!”
“喳!”王辅臣响亮地答应一声立起身来。
“好一表人材!久闻将军虎背熊腰,果然名不虚传!”康熙一边极口夸赞,呵呵笑着踱至王辅臣身前,端详着说道,“听说因你未奉特旨,被魏东亭堵在西华门外交上了手,不知胜负如何呀?”
“魏将军乃圣上驾前擎天玉柱,臣何能及!”王辅臣完全没想到康熙这样随和,绷得紧紧的心松和下来。
“那也不见得。”康熙抬头遥望着发黄的天空,轻轻叹了口气。方才听禀,太和殿东边已经震坍,毓庆宫只留下淳于殿无恙,他的心是沉重的,想了想话锋一转问道:“朕委纳兰明珠至陕,锁拿山陕总督莫洛和巡抚白清额进京问罪。你从那边过来,这件事办得怎样?”
王辅臣摸不清康熙问话的意思,一时没有开口,良久才回奏道:“白清额已经革职监护,莫洛在钦差大臣到达之前,去巡视山西未归,明大人已经派人去传。”
“朕不是问这个,”康熙笑道,“西安百姓递来了万民折,称颂他二人清廉,恳请朝廷免其重罪,你在平凉多年,朕想问问是否当真。”
“当真!”王辅臣与莫洛素来不睦,但莫洛是清官,山、陕两省有口皆碑,是说不得假话的。他咽了一口口水,清清嗓音又道:“莫洛居官多年,为母亲做寿,竟借了五十两银子,此次查抄白清额府,只存白银十六两,这些都是实情,臣不敢欺瞒!”
“听说你与莫洛不睦?”
“回皇上的话,”王辅臣忙跪下答道,“臣与莫洛、瓦尔格将军之事乃是私怨,皇上所问乃是国事,臣不能因公废私,亦不敢因私废公。”
“好!”康熙不禁击节赞赏,回身坐到椅上大声说道,“国家大臣,社稷重器,应该有这等气量——你是什么出身?”
问到出身,王辅臣身子一颤,连连叩头答道:“臣祖辈微贱,乃是库兵出身。”
库兵出身的人是富而贱,虽然有钱,却被人瞧不起。因为银库重地,怕库兵盗窃,出入时都要剥得一丝不挂。但是每月月例,又无法养家餬口,只好从小就用石头、蒜杵将肛门渐渐撑大,出库时将银块夹带在肛门中。这是人人皆知的秘密,王辅臣一向视为奇耻大辱,讳莫如深。但皇帝垂询又不能不如实回话,所以“库兵”二字未出口,眼眶中已是含满泪水,声音也显得有点哽咽。康熙也觉意外,怔了一下长叹道:“朕倒不知你出身微贱如此。”接着又提高了嗓音慷慨说道,“自古伟伟丈夫烈烈英雄比卿出身寒贱的多得是!大英雄患在事业不立,余事都不足道——张万强!”
“奴才在!”
“立传朕旨给内务府,王辅臣举家脱籍抬旗,改隶——”康熙沉吟片刻,觉得既做人情,就不如做得大些,于是果断地说,“汉军正红旗!”
“喳!”
张万强就地扎了个千儿,转身快步退出储秀宫。王辅臣感动得泪流满面,要不是君前不能失礼,早已痛哭失声了,只是饮泣叩头。
“你好自为之,”康熙沉着地说道,“朕本想留你在京供职,朝夕可以相见,但平凉重地,没有你这样有能为的战将,朕更不放心。西边、南边麻烦事很多,朝廷要倚重你马鹞子呢!”
旁边的人听着这几句话轻松平淡,但“西边”在王辅臣听来却如雷声轰鸣一样。他早随洪承畴南征,江、浙平定之后便改归平西王吴三桂节制。吴三桂待这个调人自己麾下的王辅臣是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比对自己的子侄辈还要好,即使凋至平凉,吴三桂每年还要接济他数万两银子。所以这话出自康熙,是意有所指的。王辅臣当然也闻者会心,不能不表明一个态度。想到此,王辅臣忙叩头道:“皇上委臣以专阃,寄臣以腹心,待臣大恩如天高海深,上及臣祖宗、下被臣子孙,臣若背恩负义,不但无颜于人世,亦不齿于祖宗!请主上宽心。一旦西方、南方有事,臣虽肝脑涂地,也不辜负圣恩!”
“朕不是对什么人不相信,”康熙显得有点激动,双目闪烁生光,只有此时才能看到与他年龄不相称的老练与成熟,“朕委实舍不得你这样的人才远离北京在边陲吃苦。”他一边说,一边从座后拿起一对四尺多长的银制蟠龙豹尾枪,想了想,又将一枝放回,加重了语气说道:“这对枪是先帝留给朕护身的,朕每次出行都要把它们列在马前——朕知道你在那边过的并不如意,不日就有诏调莫洛入京,饷也可先拨一些去救急。没法子,钱一多半都给人拿去了嘛——你是先帝留下的臣奴,赐别的东西都不足为贵。这里把枪分一枝给你,你带到平凉,见枪如见朕;朕留一枝在身边,见枪如见卿——”说着,豆大的泪珠已淌了出来,康熙被自己的话感动了。
“圣恩探重!”王辅臣面色苍白,激动得不住抽泣,“奴才虽肝脑涂地,不能稍报万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皇上!”说罢,颤抖着双手接过枪来。缓缓却步辞了出去,刚出垂花门,再也控制不住感激之情,竟掩面放声痛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