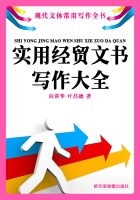吴三桂愣了半天,始终不解其意,眼看着张氏盛气进院,越走越近,只好红着脸跺脚大声骂道:“世蟠小畜生,躲了初一还有十五!妈拉巴子,越大越不成器,你不给卞大人赔罪,老子把你扔到老虎圈里!”说着,也不看张氏,头也不回地去了。
“这是——”张氏被这突如其来的闹剧弄得莫名其妙,只见阿紫不慌不忙走到床边,伏身叫道:“世蟠,王爷已经去了,你出来吧,回头等他气消了,赔个罪不就完了?”顷刻之间,两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冠冕堂皇地扬长而去……吴三桂想到此,不禁开心地哈哈大笑,把正在专注看戏的耿精忠和尚之信笑得莫名其妙。耿精忠便同:“老世伯为何突然发笑?”
“唔?”吴三桂一怔,忙笑道,“此女慧中秀外,丽质清才还在其次啊!她在这里少住些时,老夫还要叫她进京,应熊儿那里得有这么一个人侍候。”
“王爷,”胡国柱没有理会他们的谈话,在旁欠了欠身子问道,“应麒世兄回来了么?”
吴三桂听了摇头道:“这个纨袴小儿,不知在西安干些什么!自他和汪士荣去后,不但没有信来,连马鹞子的信儿也没有了!”尚之信、耿精忠这才知道,汪士荣到陕西王辅臣那里去了。吴应麒是吴三桂的侄子,自吴应熊羁留京师,三桂便视他如子,其实办事稳当也不下吴应熊。吴三桂心里发急,才肯这样发作他。耿精忠听吴三桂说起马鹅子,便笑道:“王辅臣这人我知道,是个意马心猿、首鼠两端之辈,老世伯和他打交道,要当心些了。”
吴三桂一笑,从袖中抽出一封信来递给耿精忠,说道:“老夫也不是好惹的,你和之信看看这个!”此时阿紫她们已经歌歇舞止,带着九个姑娘朝吴三桂等人蹲了个万福,便跟随着张氏一群姬妾到后头去了。
夏国相一直到人退尽,见耿精忠正聚精会神地看信,便用扇背敲着手心笑着对吴三桂道:“不妨再派保柱将军出去走一遭。”
“你说是去西安?”吴三桂转脸问道。
“不!”虚弱不堪的刘玄初一直没说话,此时一手捂着胸口,轻咳一声道,“应该到北京。”胡国柱在旁听着,眼中放出光来,插言道:“刘先生说得对,保柱将军到北京,估量明珠也该回去了,寻个机会除了他。”明珠是康熙八年进上书房参赞朝政的,在擒拿鳌拜中出了力,钦差赴陕途中,请天子剑杀掉了胡国柱的亲信郑州知府兄弟,胡国柱一直对此耿耿于怀。这个皇甫保柱是吴三桂麾下第一得力侍卫,号称“打虎将”,有短檐走壁的本领,杀掉明珠这个小白脸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吴三桂对杀明珠是赞同的,只是不满意胡国柱的心胸狭隘,只“嗯”了一声没再言语。
“扯到哪里去了!”刘玄初好容易透过气来,但仍有点气喘说道,“杀一个明珠有什么用?只能打草惊蛇!保柱此行,是为了保护大世子返回云南——有杀明珠的功夫,还不如顺便查访一下伍次友的下落呢!”
“伍次友。”耿精忠已看完了信,转手递给尚之信,沉吟道,“是不是辅佐皇上清除鳌拜的那个书生?”刘玄初道:“对,就是他。他本来是要入阁拜相的,如今赐金还山,孤身在外到处讲学,替朝廷招揽文人,这人比明珠值钱多了。我已关照衮州郑春友、刘士杰等人,请他们留意搜罗……”
“腐儒一个!”胡国柱却不以为然,“王爷要搜罗这样的书呆子,我能从夹袋里掏出一把!”
吴一桂听了一笑,立起身来对众人道:“这阵风凉起来了,进里头吃茶说话吧。”几个人这才发觉还坐在看戏的台阶上,有点不伦不类,便一起站起身来。
穿过挂满了吴三桂一幅幅拙劣不堪手书的列翠轩大厅,几个人随吴三桂进了东厢书房,围坐在大理石屏前的长案旁。侍卫只有保柱一人进来,守护在三桂身后。刚刚儿坐定,王府书办匆匆忙忙地进来,向吴三桂禀道:“王爷,云贵总督卞大人的禀帖,请王爷过目。”说着双手递上一份通封书简。
吴三桂皱了一下眉头,心不在焉地接过来,看了几行,转脸间道:“这件事你晓得首尾么?是从云贵向内地进药材的事。”书办道:“卑职知道。王爷去年秋天已下令禁运药材到内地,这几个商人犯了令,弄了十车药材,都是茯苓、大麻、三七、麝香、鹿茸、金鸡纳霜,到卡子上给扣了。他们告到总督衙门,卞大人连人送过来,请王爷处置。”吴三桂沉思了一下,突然冷笑一声:“哼!他不过是出难题给我。那几个商人现在何处?”
书办道:“都押来了,在大院垂花门外。”
“叫他们为首的进来,在轩外头候着!”说着便起身,笑着道,“你们先议着,稍候一时我就回来。”
那药商早已跪在院中阶下,见吴三桂慢条斯理踱出来,头重重地在砖地上碰了三下,恳求道:“王爷千岁!求王爷开恩……开恩……这十车药材如若不能发还,小的只能投河自尽了……”
吴三桂眼中闪过一丝怜悯的光,缓缓地说道:“孤早已下令禁运药材,你为什么这么大胆?”
“回王爷的话,”药商连连叩头,硬咽着回道,“因内地山东、河南一带遭了水,瘟疫传了开来,小的在那儿的分号伙计来说急用这些药。小的并不敢故犯王爷禁令,因请示了知府衙门才运的。常言说医家药店以治病救人为本……”
“咹?什么救人为本?”吴三桂厉声说道,“难道孤王我是以害人为本?”见药商吓得只是磕头,吴三桂口风一转,叹息一声道,“不过你也确有你的难处。你的这十车药,我全买了,如何?”
药商抬起了头,惊讶不解地看着吴三桂悲天悯人的面孔,结结巴巴地说:“这……这……”
“我们云贵近来也有瘟疫,而且时常有瘴气伤人的事,”吴三桂道,“这么做,也是为我云南贵州人着想,所以金鸡纳霜、黄连、三七、麝香这类药断然不能出省!你是商人,想发财也是自然的事,我给你指条生财之道如何?”药商先还叩头称是,至此,又惊异地抬头看了一眼吴三桂。吴气桂笑笑道:“告诉你们会馆那些商人,咱们这里缺的是马、粮,满可以到内蒙、直隶贩些回来,必定叫你们吃不了亏!”
“好王爷!”药商道,“粮食还好说,从中原贩马进云贵犯朝廷的禁令啊……”
吴三桂冷笑一声道:“甭和我讲这些生意经,你们这些人有的是办法……”说着一甩手走了。便听耿精忠笑道:“姜还是老的辣,老世伯可谓一石双鸟,妙!”吴三桂只点头笑笑,坐了问道:“二位贤侄,王辅臣的信怎么样呀?”
“这是一份卖身契!”尚之信已看完了,呵呵笑着把信在桌上又舒展了一下,“老世伯,有它在,马鹞子已成五华山的护山神了!”他兴奋得目中熠熠闪光,顺口读道:
“……方今天下督抚藩镇皆有同心,待王为孟津之会。王乃前朝旧臣,当年之事,出于不得已,今天下机杼在握,王若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千古之大业也……”
尚之信边念,边连声赞道:“妙哉,姓王的本是行伍出身,能为此文,颇不容易!”
“这未必是他的亲笔。”夏国相冷冷说道,“他是专阃建牙上将,寻个由头杀掉写信的人,这封信便一文不值了。”一句话说得人家又沉默了。
“不但要腹有良谋,更要胸有人志!”刘玄初此时精神好了一点儿,见大家神色沮丧,便笑道,“国相这话当然对,不过王辅臣确是心怀异志,只要好好笼络,不愁不为我所用。所以我看也不能把这信看得太轻。”
“胸有大志”是对吴三桂讲的。这个刘玄初,自十七岁入吴家幕府,己是四十多年。吴三桂素来敬重他,但在大事上,有很多并不听他的。清兵未入关,刘玄初便劝吴三桂早作南撤打算,让李自成与清兵先打,巧收渔翁之利,吴三桂不听;顺治末年朝廷下诏各藩裁兵,吴三桂倒是听了刘玄初劝告,谎报南明永历在缅甸境内蠢动,不但没裁兵,而且捞了大批军饷,但不料吴三桂竟假戏真做,逼缅王交出永历帝朱由榔,亲令绞死在迫死坡,一下子在天下人面前弄臭了名声,刘玄初从此气得得了咯血病;康熙六年,刘玄初劝吴三桂与鳌拜言归于好,搅乱政局,吴三桂却又想渔翁得利的好处,竟置之不理,坐看康熙成了气候……想到这里,刘玄初脸上泛起一阵潮红。他看看上头穿着团龙黄袍的吴三桂,一直恨吴三桂不争气,又觉得光复汉业目下也只有靠他……刘玄初喘了一口气,又道:“三王实力如今都在这里,几天会议我都在场,其实这就是一次小孟津会,竭诸侯之力攻伐夷狄。不过目下兵力不过五十万,粮饷虽多,却靠朝廷供应,一旦断了这粮源,立时就会显得拮据,如今有什么动作是很不明智的。”说着便喘。
“依先生看该怎么办?”耿精忠久闻刘玄初是吴三桂的头号谋臣,听他讲解透彻,心里暗暗佩服,在座上略一躬身问道,“先生以为何时举事为宜?”
“此乃非常之举,”刘玄初神色庄重地说道,“不但事关诸公身家性命,而且事关百万生灵涂炭!此举不成,清家天下便固若磐石了!所以心里再急,也要慎上加慎。我们雄踞云贵粤闽,占铁盐茶马之利,兼山川关河之险,先要把治下百姓生业弄好,不要光指朝廷那几两银子过日子——内修政务,外连藏回,养马练兵,结交统兵将领。朝廷一旦撤藩,等于授我口实,便可结兵誓师,一战可胜!”他略停一下又道,“据我愚见,舍此别无良策。”
尚之信在广东号称魔王,杀人如麻,这些话听来虽有理,他却觉得积重难返,不如速战速决,于是含笑说道:“果然好!不过请先生留意,朝廷也在这么做,而且我们无法和他比!去年擒了鳌拜,便立即下令停禁圈地,秋季又是大熟——北方七十郡蠲免了钱粮;听说又调于成龙为河道总督,黄淮的治理也就是眼前的事;康熙元年士子应试不足额,今年听说满京都是公车会试的举人!他占了中央形势,时不我待呀!”
“我并没有说慢慢来。”刘玄初手扶椅背,听得很认真。等尚之信说完,便笑道,“我说持重,是内紧外松,加紧准备。他们的难处也很多——一多半岁入拿来给我们,又要免捐收买民心,又要治河,哪有钱来打仗?民心也不稳,黄淮决口灾民很多,北京的朱三太子也搅得很凶……”
“朱三太子?”耿精忠不禁问道,“我在北京怎么没听说?”
刘玄初拈须笑道:“王爷在北京出入宫禁,朱三太子怎么能光顾到你?”正说间,外头守护的将军马宝匆匆进来,双手递一张名刺给吴三桂。吴三桂看时,上面写着:“年眷同学弟杨起隆拜”,不由笑着对尚之信和耿精忠说道:“云南地面邪,说曹操,曹操到,朱三太子来了!”大家听了不禁愕然相顾,吴三桂见刘玄初微微颔首,从嘴里迸出一个字:“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