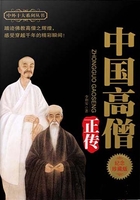司马光在洛阳,前后花了十九年时间修撰《资治通鉴》,如今终于完稿了。这部记载一千三百余年间历史的编年史巨著,凝聚了司马光一生的心血,但他仍有一件心事未了。那就是眼看新法施行日久,危及民生社稷,他却无法向朝廷进言,为皇上分忧。如今他已满头白发老态龙钟、体衰力弱,特别是几年前一次中风,遗留下的腿疾,更令他行动不便。但他仍坚持要将书稿面呈神宗,希望借此重提他对于新法的建议,这样在有生之年,也算为国家君王尽忠了。
司马光叫儿子司马康、助手范祖禹整理好书稿,拿大箱子装好,自己坐着马车,不顾一路颠簸,风尘仆仆地赶到汴京。神宗正卧病在榻,听说司马光进献《资治通鉴》进京,连病都好了一半,立刻到睿思殿接见。
睿思殿里已摆满了大红木箱子,部分书稿已进呈书案之上。司马光一瘸一拐地进殿施礼参拜。神宗见司马光垂老之态,慌忙叫免礼赐座,动情地说:“司马公老了呀!朕的股肱之臣老了呀!”司马光感激不已,垂首叩谢。范祖禹和司马康在一旁也拭泪不止。神宗说:“司马公呕心沥血,才完成如此皇皇巨著,功德无量,这可是我大宋名垂青史的大事!”司马光拜谢道:“老臣资质驽钝,才庸学浅,不敢有负陛下钦赐书名之重托。如今书稿告竣,进呈朝廷,老臣死而无憾了!”神宗命内侍予以褒奖赏赐。
司马光正思忖着如何跟神宗提及变法之事,见神宗面带病容、精神不济,便问道:“陛下正值盛年,为何呈此病容?”神宗凄然长叹:“一言难尽哪!举国上下之事,常令朕心力交瘁,故此大病了一场。”司马光忙进言说:“陛下勤政爱民,心系天下,可也要保重龙体呀!”神宗说:“新法是朕一生心血,如今施行多年,天下在肩,如泰山压顶,容不得朕有片刻懈怠啊。”司马光见神宗意志仍然坚定,一时难以说动,就把反对变法的心思暂且放下了。
王珪、蔡确听说司马光进京献书,一大早就进宫面见神宗,害怕圣心大悦,授之重任,就商议进宫试探虚实。二人进睿思殿来拜见过神宗,又向司马光施礼。王珪道:“君实一向可好?曾闻君实大病一场,奈何老夫公务在身,未能前去洛阳探视,请恕罪。”司马光素来不喜欢王珪的为人,见他故作亲热,冷冷地说:“多谢宰相垂爱,司马光尚能苟活而已。宰相日理万机,肩负天下,岂能因一废人而误苍生大事呢?相公能有此言,司马光已是受用匪浅啦!”
王珪见司马光语带讥讽,只得尴尬地赔笑。蔡确在一旁,见风声不对,过来圆场:“司马公成此巨著,功不可没呀!”司马光笑说:“若无圣上鼎力支持,焉有此书?若无同人呕心沥血,焉有此书?司马光不敢贪天功为己有啊!”蔡确无话可说,跟着王珪佯装翻阅书稿。
神宗翻看书稿,连连点头称赞。蔡确瞅着机会,不无谄媚地说:“司马公道德文章为本朝第一,苏轼虽然是当今文坛领袖,也未必能著如此鸿篇巨制。”王珪早提醒过蔡确,让他不要在神宗面前提及苏轼,以免圣心悯恻,又要把苏轼召回。这下蔡确拍马屁拍漏了嘴,当着司马光和神宗的面说到苏轼,王珪不禁连连叫苦,忙说:“他哪能跟君实相比呢!”
司马光冷笑道:“二位差矣!若苏子瞻担此重任,恐怕这样两部书都已完成了。”王珪说:“君实何以如此贬低自己啊?”司马光怒道:“自己贬了,就省得别人蛊惑圣上贬。你们一再贬低苏轼,但天下读书人却越来越把他视为文章泰斗。苏轼在黄州,文章道德日进千里,岂是你们贬损得了的?”说完从袖中掏出一卷文章来说:“陛下,这是苏轼在黄州所作《赤壁赋》,如今天下传抄,人人争诵,定成为我大宋空前绝后的千古不朽之作。请陛下御览。”
神宗见大臣争执,心中早烦了,忙止住争吵,拿《赤壁赋》读罢,不禁拍着书案赞叹道:“好个苏轼,真是大手笔,不愧为文章泰斗!前不久误传苏轼已死,后来读到他的《念奴娇》词,让朕的病几乎好了一半。如今这《赤壁赋》更胜一筹,朕的病要完全好了。”说完,神采飞动。王珪见司马光故意提及苏轼,知道他是有备而来,忙对神宗说:“苏轼素来矜才使气,谤毁新法,圣上贬他到黄州,就是让他戒除骄浮之气,慎言慎行,这也是圣上爱才之心哪!”
司马光见他巧舌诡辩,大怒道:“王珪!人称你三旨宰相,果真名副其实!苏轼秉忠报国,尽心民事,岂是你等乡愿宵小之徒可以理解的?你只会庸碌为官,把苏轼排斥朝外,是怕他回朝坏了你宰相的位子吧!”
王珪气得连连咳嗽,答不出话来。神宗问道:“王珪,这《赤壁赋》天下争诵,人人皆知,唯独朕不知道。你身为宰相,有如此好的文章,如何不进呈给朕?”王珪支支吾吾,愈加猛烈地咳嗽,不知是老来病重,还是借咳嗽掩饰内心的慌乱?蔡确在一旁吓得不敢说话。司马光说:“宰相大人要保重啊,苏轼还有好文章等你呈递呢!”
神宗语重心长地说:“王珪啊,自从苏轼被贬以来,朕曾三次欲用苏轼,第一次朕欲擢他为国史编修,你推荐了曾巩,现在曾巩已病故两年了;第二次,朕欲擢他为江宁太守,你们却说边境有事,好,朕也就只顾边境之事了;这第三次,朕欲擢他为江州太平观,你为何还没有为朕拟旨啊?今日你说说,是你不同意呢,还是翰林学士院的李定从中作梗啊?”
王珪吓得浑身打战道:“陛下,天下乃陛下之天下,圣上要任用谁岂是臣子所能干预的?臣等曾研究过苏轼的生辰八字,与任用太平观命格不合。”
神宗发怒道:“哼!岂可以生辰不合而废用人才!”王珪惶惶低头,连连应承:“臣这就去翰林院拟旨。”神宗说:“不必了。朕要亲自拟旨。调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汝州靠近京畿,这明显是将要擢升重用之意。王珪此时也不敢再找借口搪塞,忙说:“陛下英明,臣等遵旨。”
神宗冷笑道:“王珪,你遵旨倒快!曾有人对朕说,汴京人给你编了一首歌谣,你可知道?”王珪遍体流汗,结结巴巴地说:“老臣……不知。”神宗说:“汴京人说你是三旨不离口,背后下狠手,表面善拍马,实是大奸猾。”神宗旁边的张茂则都不住地冷笑。
王珪吓得面如土色,跪倒在地连连磕头,声泪俱下地哭诉:“陛下,老臣陪陛下读书多年,虽非有才,但忠心尚在;承蒙圣恩,重用为相,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陛下明察,司马光刚一回朝,就要结党反对新法,故而劝陛下重用苏轼。陛下,老臣是为新法大业,大宋社稷着想啊!”
神宗长叹一声:“王珪,让朕说你什么好啊!是你一直排挤司马光、苏轼、吕公著等人,朕是明白的,朕不是昏君!你在朕面前说恭维话,说好听话,朕不怪你。但你为什么就是不说实话,有用的话?若是司马光、苏轼在朝,朕会招致永乐之耻吗?是你们使朕受辱,屡屡出错!朕不是昏君,如今却要担昏君之名!”神宗情绪激动,不禁触动病体,猛烈地咳嗽起来。张茂则急忙过来捶背。
司马光不发一言,看来圣上擢用苏轼的心意已决,自己不必多费唇舌了。神宗稍稍平静下来,对王珪说:“王珪,你也是朕的老师,朕不追究你的责任,因为朕还要给天下读书人做个尊师重教的好样子。可你不能有恃无恐,好自为之吧。”说完摆摆手示意王珪退下。王珪失魂落魄,缓缓退出殿外。蔡确狼狈地在一旁扶着。王珪步履蹒跚、目光灰暗,突然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来,口中嗫嚅着:“完了!完了!”蔡确连忙把他扶回去休息。
苏轼在黄州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开春后,东坡上的麦子长势喜人,苏轼依然每天下地劳作,回到家或是去救儿会帮助朝云照顾婴孩,或是在书房读书,督促两个儿子作诗习文。苏迨、苏过已经长大了,跟随父亲和哥哥在黄州,粗食淡饭,亲事耕稼,早已明白安贫乐道的真谛,现在成长为敦厚好学的读书人了。王闰之跟着苏轼饱经忧患,人虽显得老了,但心中宁静安闲,再无一句怨言。苏轼觉得家和人闲,内心万分满足。农事闲时,就到江中垂钓,偶尔钓到几尾鲜鱼,便拿回家亲自烹煮,与巢谷对酌几杯。
江中春水大涨的时候,徐君猷带着朝廷量移汝州的诏令来拜访苏轼,告诉他圣上同时还授予苏迈饶州德兴县尉的官职。苏轼摆下浊醪款待徐君猷。徐君猷举杯说:“徐某宦游半生,能与子瞻同治黄州,实在是三生有幸。如今子瞻奉旨北归,必定受到重用,可以脱离苦厄,重振羽翼了。”苏轼摇摇头笑着说:“徐公客气了。苏某当初获罪至黄,不以为忧,今日蒙恩别黄,不以为喜,万事已不必萦绕胸中。五年来多蒙太守照应,苏某感激不尽,除了这一杯水酒也无可报答啊。”说完,一饮而尽。徐君猷说:“子瞻胸怀之旷达,实在令老夫敬仰。如今且收拾行装,等离别之日,老夫必定亲来饯别。”苏轼感激不已,又连连敬酒,还把救儿会及雪堂、东坡等田产交由太守代为掌管,请他料理一切。徐君猷欣然应允。
第二天,苏轼邀请众位好友来雪堂相聚,陈慥和柳氏、潘丙、佛印、参寥和善济等人都来道贺。苏轼举起酒杯哽咽道:“诸位,圣上下旨,调任我为汝州团练副使,不日就要启程离开黄州了。转眼来黄州已五年了。黄州是我的祸,也是我的福。祸,在于黄州是我的患难之地,日子过得艰难;福,在于我虽然艰难,却能喜获诸位的高情厚意。来,诸位,苏某谢谢你们,先干为敬!”
陈慥举酒说:“恭喜子瞻兄,汝州与京城近在咫尺,陛下此意是要重用子瞻啊!”
苏轼又饮了一杯,接着说:“不瞒诸位,五年前来黄州,我日日都想离开。如今我却不想离开,真的不想离开。这雪堂、这临皋亭、这东坡,是我亲手所建,亲手所种,我怎么愿意舍弃荒废它们呢?可惜啊,放旷如苏某,也不能免俗,不能违抗圣命,只能身不由己,随波逐流而去。不说这些了,来,我再敬诸位,多谢诸位在苏某危难之际真情相助!我当永志不忘!”
众人都满怀惆怅,举杯回敬。参寥独自念经默诵,为苏轼祈祷。佛印却大笑说:“子瞻兄来黄州五年,所作奇诗妙文无数,功德无量,正得益于此地山水秀丽、民风淳朴,子瞻何不谢谢它们?”苏轼举杯大笑:“佛印大师说得对!苏某受此磨难,如今文人也做得、农夫也做得,正是黄州赐我之福啊!”说罢起身沥酒于地,望着这熟悉的江山,自己亲手耕种的土地,亲手栽种的树木,恋恋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