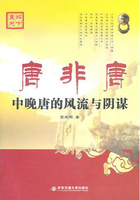——在暨南大学的讲演
“文艺学”题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念大学中文系,有一门课叫“文学概论”,又常常叫做“文艺学”。老师讲课时总是把文学理论叫做文艺学。那时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叫《文艺学引论》,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的讲稿。毕达可夫被认为是权威,他讲的被认为是最新的理论,时髦得很。其实,后来知道,他并不是当时苏联最具权威性的文学理论家,而且当时苏联的文学理论也只是世界文学理论界的一种或几种观点,有的理论还常带点儿僵化了的庸俗社会学的味道,并非世界上最新理论的代表。我们是见和尚就拜,不管他念的什么经--只要是苏联和尚。
后来发现,翻译苏联文学理论着作时,“文艺学”这个中文词译得不准确。究竟最初谁这样译,搞不清。原文只是文学学,而没有“艺术”的含义,俄文里还有一个词可译为艺术理论或艺术学。为此,我请教了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俄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有关专家,如吴元迈、周启超等,他们也都这么说。据说,这个俄文字出现在1929年苏联的一本文学理论集子中(波斯彼洛夫的老师编辑,也收了波斯彼洛夫的文章)。周启超近期翻译的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一本书,即将之译为文学学(书名译为《理论诗学》),维·叶·哈利捷夫着,1999年初版,至今已出了三版,36万字。
另,曹卫东在《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发表的《认同话语与文艺学学科反思》一文中说,文学学(文艺学)最早从德文来。他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梳理,认为文艺学来源于19世纪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东方学--古典学--文学理论(文艺学)。但曹卫东的说法尚欠明晰和精确。
又有朋友说韦勒克对此有所考证,于是按照朋友的指引,查了韦勒克《批评的概念》一书。果然,书中考证了“文艺科学”这一术语在德国被使用的情况:
“‘文艺科学’在德文中就保存着其旧日表示系统知识的意思。”
“在德国,‘文艺科学’这个名词取代了西方所使用的‘批评’。这个名词取得了成功,而类似的词组如‘文学的科学’却没有在西方流行。在法国,这一类企图和主张有着很长的传统:例如J.J.安培在他的《论诗歌的历史》(1830年)一书中就说文学哲学和文学史是‘文学科学’的两个组成部分。但是‘文艺科学’这个名词只在德国扎下了根。卡尔·罗森克朗茨在1842年评论几本书时简述了当时德国‘文艺科学’的情况,他比较随便地使用了这个名词。我在一份1865年出版的期刊上也找到过这个词。1887年恩斯特·格罗斯以《文艺科学的目的与方法》为题做了讲演。恩斯特·爱尔斯特写了一部两卷本的专门论着《文艺科学原理》(第一卷,哈勒,1897年;第二卷,1911年)……”。
“在德国以外,‘文学的科学’并没有得到通用。荷兰人亨利克·克里门斯·缪勒于1898年在爱丁堡做了题为《文学的科学》的讲演。罗马尼亚人米歇尔·德拉哥米赖斯库写过四卷本的《文学的科学》(1928-1929年)。这些都是极其个别的例外。这个说法在盖伊·米绍的《文学的科学引论》(伊斯坦布尔,1950年)中又重新出现。在英文和法文中,‘科学’(science)变得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以致这个名词不能继续通用;而在德国,‘Wissenschajt’却保留着它旧日的比较广泛的意思,所以人们把消除自然主义联想后的‘文艺科学’当作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史的新诗学和批评的口号。1908年狄尔泰的学生鲁道夫·翁格尔主张研究现代‘文艺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但是这个名词显然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新学者们的集合号令。1920年一个名叫西格蒙特·冯·棱皮斯基的人写了一部《德国文艺科学史》,这本书舍弃实用批评而收进诗学和文学史。1923年开始创办《文艺科学与精神史学季刊》,保罗·默尔克也发表了他那本叫做《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的小书,这本书就是以文艺科学与精神史学的对比为其基础的。”
韦勒克此书,还有另一中文译本,书名译为《批评的诸种概念》。
现在,文学学(或者按老用法“文艺学”)遇到点麻烦:据说到了穷途末日了,快要寿终正寝了。因为,紧跟着“文学会消亡吗?”的问题而来的,或者说与“文学会消亡吗?”的问题紧密相连的,就是文学学的命运问题--能否存在的问题,至少是文学学向何处去的问题。
“向何处去?”从大的方面说,无非两种出路:死与活。死--若文学消亡了,文学学亦无必要,死矣;活--若文学不会消亡,文学学自然也不能不存在,活着。
那么,文学学、文学研究究竟会怎么样呢?
不少学者提出来各种设想,各种方案。我们不妨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设想、方案,作些简要评介。
米勒方案:关于“阅读”概念
米勒说“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
“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息在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在这里,现在。”
金惠敏对此作了评述:希利斯·米勒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在电子媒介时代之命运的忧虑,不是毫无来由的杞人忧天,威胁确实存在着,而且就在眼前。对此,米勒是清醒的,而另一方面他又是那么地执着于文学事业,不改初衷。不过,这在他并不是一对矛盾,我们看到,其“执着”是建立在一个清醒的意识之上的,而非对威胁如麦克卢汉所谓的“麻木不仁”。惟其清醒,他才能够“执着”得下去,即惟其清醒,他才能够以变通的方法坚持自己的“执着”,坚持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不可取代性以及与人类的永恒相伴。
面对图像和其它媒介文化的冲击,米勒试图以一个更高的概念即“阅读”(reading)予以海纳:“文学系的课程应该成为主要是对阅读和写作的训练,当然是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但经典的概念需要大大拓宽,而且还应该训练阅读所有的符号:绘画、电影、电视、报纸、历史资料、物质文化资料。当今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有知识的选民,应该是能够阅读、能够阅读一切符号的人,而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在另一处强调:“这里阅读不仅包括书写的文本,也包括围绕并透入我们的所有符号,所有的视听形象,以及那些总是能够这样或那样地当作符号来阅读的历史证据:文件、绘画、电影、乐谱或‘物质’的人工制品等等。因此可以这么说,对于摆在我们面前有待于阅读的文本和其它符号系统,阅读是共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聚集起来解决我们的分歧。这些自然也包括了理论文本。”“阅读”作为米勒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概念,在此具有双重作用:第一“阅读”向一切文本、一切可被阅读的符号开放,因而借助于“阅读”米勒保持了对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的宽容和接纳;但是第二,“阅读”显然又是一个暗示着现代性价值的概念,包括他这里所使用的“符号”(sign)一词,即它总是有所指、有意味、有深度,“阅读”“符号”毫无疑问就是索取符号中的意义,解构论的米勒并不反对这一点,他所反对的只是像新批评那样将文本阅读成一个有机整体,因为它可能窒息文本的异向活动。“阅读”对米勒而言本质上就是文学“阅读”,因此米勒以“阅读”所表现的开放性同时又是其向着文学本身的回归,是对文学价值的迂回坚持,他试图以文字的“阅读”方式阅读其它文本符号。
尽管我们不能由此将米勒当作文学中心主义者,在西方这背后通常就是文化精英主义的观念,但米勒的确赋予“阅读”以文学和精英的色调,并通过“阅读”表现了他人文主义的救世情怀。他深信“文学理论前程无限”,因为它是完成如下两项人文重任的基本工具:一是“档案记忆”,一是“教授批评性阅读,将它作为对抗语言现实与物质现实之灾难性混淆,其名称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的首要方法”。如果说对于米勒而言“文学理论”就是“解构论”,就是一种修辞性阅读,那么文学理论的前景也同样就是属于“阅读”的,其任重而道远也同样适用于“阅读”。其实,米勒总是将此“文学理论”的任务说成是“阅读”的,在阅读中培养我们对传统的记忆,在阅读中构成我们对于所谓“意识形态”的“批判距离”。或许米勒并不特别熟悉法兰克福学派等的批判理论,以及波德里亚的“拟像”学说,但他以“阅读”为基地对媒介扩张所做的回应或反击与这些理论则是同处于一个战壕;而且作为文学批评家,其“阅读”性的辩护更切近于文学,因而更能使我们这些同行接受和信服:
我希望文学研究本身能够以某种方式继续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是如此地热爱文学,我于它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想即使书籍的时代过去了,被全球电信的世纪取代了(我认为这一过程正在发生),我们仍然有必要研究文学。教授“修辞性阅读”,这不足是为了理解过去,那时文学是何等地重要,而且也是为了以一个经济的方式理解语言的复杂性,我想只要我们使用语词彼此间进行交流,不管采用何种手段,语言的复杂性就依然是重要的。
文学研究或“修辞性阅读”的存在是基于文化记忆的需要,更是为了经济有效地掌握语言,我们无法离开语言,因而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抛弃文学。只要有语言,就一定有文学和文学研究。米勒这样的辩护虽然朴素,但道理实实在在,自有其不可推倒的定力,更何况其情真意切的感染力,--这使我们最后想到,执着于文学或美学,本就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只要我们人类仍然存在,仍然在使用语言,我们就会用语言表达或创造美的语言文学。
如果按着米勒的思路说下来,文学学(文学研究)不会死,只是内涵和方式变化了。或者循着第一讲中说到的米勒的思路,该死的文学死了,自然以它为对象的那部分文学研究也该死;而该活的文学活着,自然以它为对象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活着,但是变为把“阅读”作为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概念。
然而,不管怎么说,不论对于外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文学学“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活”。
“再也不能那样活”,那么,怎样活?除了上面说的外国的米勒方案以外,这些年来中国学者一直讨论着各种不同的方案,而且争论颇为激烈。
前几年主要是“本土化”派与“接轨化”派(前者以曹顺庆的“失语症”论为代表,后者以陈晓明的“理论无国界”论为代表)的学术争吵。眼下,前面的争论无结果,又加进一个问题:电子媒介时代、图像时代、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时代,文学学怎样适应?下面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些学者的几种思考。
重建“文艺社会学”
重建“文艺社会学”(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是思考的方案之一:
“因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以及传播方式的普及等导致的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当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
“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杜按:此话不确。审美活动从来不局限于纯艺术)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
陶东风认为,上述情况“深刻挑战了文艺自律的观念,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应“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在我看来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它的对象已从经典文学艺术走向日常生活的文化,进入到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
基于上述情况,陶东风提出应倡导“新的文艺-社会研究范式(不管叫它‘文化研究’还是‘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这种文艺社会学区别于泰纳的和苏联的文艺社会学。它又是对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力图重建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但同时“强调语言和文化活动是具有物质性的基本社会实践”(杜按:不要如此绝对。并非所有语言和文化活动都是物质性的)。“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应该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范式。”
陶东风的设想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特别是就文艺社会学这一具体学科的建设来说尤其如此。但,应对如此复杂的变化了的“现象”(如陶东风所描述者),仅陶式“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够用吗?能抗得住吗?仅提出文学社会学,眼界小矣。
另,陶式文艺社会学,核心是“文化研究”,所以它的名字应该叫“文化-文艺社会学”。
文化研究的出场
金元浦的方案是“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当代世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向传统学术、传统学科提出的巨大挑战的回应。也是传统学术、传统学科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学科的“内爆”涨破原有外壳的必然结果。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作为自律论依据的文学的文学性,现在已溢出文学的边界,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电视、网络、广告、服装、家居、美容、汽车销售以及美食,进入几乎所有日常消费和商业炒作中。而审美性不再是文学艺术的专属性能,而成为商品世界的共性。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已经成了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组织化原则。
文化研究如詹姆逊所言是一种“后学科”,是一种开放的,适应当代多元范式的时代要求并与之配伍的超学科、超学术、超理论的研究方式。文化研究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的努力。作为一种后学科,在总体指向上是反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文化研究在跨学科的范畴之内运行,涉及到社会理论、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传媒研究、文学和文化理论、哲学及其他的理论话语---这些正是广义的文化研究题目下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国的后现代理论所共有的。文化和社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跨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