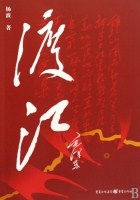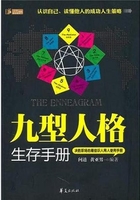便面不得于舟,而用于房舍,是屈事矣。然有移天换日之法在,亦可变昨为今,化板成活,俾耳目之前,刻刻似有生机飞舞,是亦未尝不妙,止费我一番筹度耳。予性最癖,不喜盆内之花,笼中之鸟,缸内之鱼,及案上有座之石,以其局促不舒,令人作囚鸾絷凤之想。故盆花自幽兰、水仙而外,未尝寓目。鸟中之画眉,性酷嗜之,然必另出己意而为笼,不同旧制,务使不见拘囚之迹而后已。自设便面以后,则生平所弃之物,尽在所取。从来作便面者,凡山水人物、竹石花鸟以及昆虫,无一不在所绘之内,故设此窗于屋内,必先于墙外置板,以备承物之用。一切盆花笼鸟、蟠松怪石,皆可更换置之。如盆兰吐花,移之窗外,即是一幅便面幽兰;盎菊舒英,内之牖中,即是一幅扇头佳菊。或数日一更,或一日一更;即一日数更,亦未尝不可。但须遮蔽下段,勿露盆盎之形。而遮蔽之物,则莫妙于零星碎石,是此窗家家可用,人人可办,讵非耳目之前第一乐事?得意酣歌之顷,可忘作始之李笠翁乎?
【评】
借景是中国园林艺术中创造艺术空间、扩大艺术空间的一种精深思维方式和绝妙美学手段。所谓借景,就是把园外的风景也“借来”变为园内风景的一部分。如陈从周先生《说园》中说到北京的圆明园时,就说它是“因水成景,借景西山”,园内景物皆因水而筑,招西山入园,终成“万园之园”。借景是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明代计成《园冶》对借景有较详细的论述:“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畽,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界,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然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笔先,庶几描写之尽哉。”继承古典美学的借景理论,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就随意举出远借、邻借、仰借、俯借、镜借以及隔景、分景等数种加以发挥,他谈到北京的颐和园可以远借玉泉山的塔,苏州留园的冠云楼可以远借虎丘山景--是为远借;拙政园靠墙的假山上建“两宜亭”,把隔墙的景色尽收眼底--是为邻借;王维诗句“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叶令仪诗句“帆影都从窗隙过,溪光合向镜中看”--此可谓镜借,等等。此外还有“分景”和“隔景”:颐和园的长廊,把一片风景隔成两个,一边是近于自然的广大湖山,一边是近于人工的楼台亭阁,游人可以两边眺望,丰富了美的印象--这是分景。颐和园中的谐趣园,自成院落,另辟一个空间,另是一种趣味,这种大园林中的小园林,叫做隔景。
各个文化门类的道理是相通的,由园林中的“借景”,我一下子联想到武术中的“借力”--所谓“四两拨千斤”是也,即通过“借”,把对方的力转换成自己的力,以造成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这是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奇妙之处,也是中国人的绝顶聪明之处。究其根源,还是与中国独特的哲学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看世界事物,一般都是综合的、联系的、融通的,而非分析的、隔离的、阻塞的;中国人的思维常常是“圆形思维”。《庄子·齐物论》云:“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则阳》又说:“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有的学者释“环中”曰:“居空以随物而物自成。”有的说:“以圆环内空体无际,故曰环中。”这都有道理。但我想更应该强调古人思维中内外融通、物我连接、主客一体、循环往复的特点;而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也即构成“思维之园”或曰“圆形思维”。正是依据这种“思维之园”或“圆形思维”,在美学中就出现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出现了他在《与李生论诗书》所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等理论。其思想要旨在于,必须把象内与象外联系起来、融而汇之,透过“象外”、“韵外”、“味外”,并且超越“象外”、“韵外”、“味外”,从而把握“环中”之精义和深层旨趣。这就是超乎言象之外,得其环中之妙,得其“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正因为中国人的这种“圆形思维”,总是内外勾连、形神融通、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所以很自然地,在园林艺术中总是把园内与园外视为一体,把园林与整个大千世界浑然融和,出现了“借景”的审美实践,并从中总结出“借景”的理论思想。真真美妙绝伦!
中国园林中,借景常常通过“窗栏”来实现。李渔在《闲情偶寄》“取景在借”条中所谈的,主要就是运用窗户来借景。他设计了各种窗户的样式:湖舫式、便面窗外推板装花式、便面窗花卉式、便面窗虫鸟式以及山水图窗、尺幅窗图式和梅窗等等。他特别谈到,西湖游船左右作“便面窗”,游人坐于船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而且,因为船在行进之中,所以摇一橹,变一像,撑一篙,换一景。李渔还现身说法,说自己居住的房屋面对山水风景的一面,置一虚窗,人坐屋中,从窗户向外望去,便是一片美景,李渔称之为“尺幅窗”、“无心画”。这样,通过船上的“便面窗”,或者房屋的“尺幅窗”、“无心画”,就把船外或窗外的美景,“借来”船中或屋中了。宗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谈窗子的作用时,就特别提到李渔的“尺幅窗”、“无心画”,说颐和园乐寿堂差不多四边都是窗子,周围粉墙列着许多小窗,面向湖景,每个窗子都等于一幅小画,这就是李渔所谓“尺幅窗,无心画”。而且同一个窗子,从不同的角度看出去,景色都不相同。这样,画的境界就无限地增多了。
窗户在这里还起了一种画框的作用。画框对于外在景物来说,是一种选择,是一种限定,也是一种间离。窗户从一定的角度选择了一定范围的景物,这也就是一种限定,同时,通过选择和限定,窗户也就把观者视线范围之内的景物同视线范围之外的景物间离开来。正是通过这种选择、限定、间离,把游人和观者置于一种审美情境之中。
“借景”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创造和园林美学的“国粹”,而且“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外国的园林艺术实践和园林美学理论,找不到“借景”。
四图:湖舫式
此湖舫式也。不独西湖,凡居名胜之地,皆可用之。但便面止可观山临水,不能障雨蔽风,是又宜筹退步,以补前说之不逮。退步云何?外设推板,可开可阖,此易为之事也。但纯用推板,则幽而不明;纯用明窗,又与扇面之制不合,须以板内嵌窗之法处之。其法维何?曰:即仿梅窗之制,以制窗棂。亦备其式于右。
五图:便面窗外推板装花式
四围用板者,既取其坚,又省制棂装花人工之半也。中作花树者,不失扇头图画之本色也。用直棂间于其中者,无此则花树无所倚靠,即勉强为之,亦浮脆而难久也。棂不取直,而作欹斜之势,又使上宽下窄者,欲肖扇面之折纹;且小者可以独扇,大则必分双扇,其中间合缝处,糊纱糊纸,无直木以界之,则纱与纸无所依附故也。若是,则棂与花树纵横相杂,不几泾渭难分,而求工反拙乎?曰:不然。有两法盖藏,勿虑也。花树粗细不一,其势莫妙于参差,棂则极匀,而又贵乎极细,须以极坚之木为之,一法也;油漆并着色之时,棂用白粉,与糊窗之纱纸同色,而花树则绘五彩,俨然活树生花,又一法也。若是泾渭自分,而便面与花,判然有别矣。梅花止备一种,此外或花或鸟,但取简便者为之,勿拘一格。惟山水人物,必不可用。板与花棂俱另制,制就花棂,而后以板镶之。即花与棂,亦难合适,须使花自花而棂自棂,先分后合。其连接处,各损少许以就之,或以钉钉,或以胶粘,务期可久。
六图:便面窗花卉式便面窗虫鸟式
诸式止备其概,余可类推。然此皆为窗外无景,求天然者不得,故以人力补之;若远近风景尽有可观,则焉用此碌碌为哉?昔人云:“会心处正不在远。”若能实具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过目之物尽在画图,入耳之声无非诗料。譬如我坐窗内,人行窗外,无论见少年女子是一幅美人图,即见老妪白叟扶杖而来,亦是名人画幅中必不可无之物;见婴儿群戏是一幅百子图,即见牛羊并牧、鸡犬交哗,亦是词客文情内未尝偶缺之资。“牛溲马渤,尽入药笼。”予所制便面窗,即雅人韵士之药笼也。
此窗若另制纱窗一扇,绘以灯色花鸟,至夜篝灯于内,自外视之,又是一盏扇面灯。即日间自内视之,光彩相照,亦与观灯无异也。
七图:山水图窗
凡置此窗之屋,进步宜深,使座客观山之地去窗稍远,则窗之外廓为画,画之内廓为山,山与画连,无分彼此,见者不问而知为天然之画矣。浅促之屋,坐在窗边,势必倚窗为栏,身之大半出于窗外,但见山而不见画,则作者深心有时埋没,非尽善之制也。
八图:尺幅窗图式
尺幅窗图式,最难摹写。写来非似真画,即似真山,非画上之山与山中之画也。前式虽工,虑观者终难了悟,兹再绘一纸,以作副墨。且此窗虽多开少闭,然亦间有闭时;闭时用他槅他棂,则与画意不合,丑态出矣。必须照式大小,作木槅一扇,以名画一幅裱之,嵌入窗中,又是一幅真画,并非“无心画”与“尺幅窗”矣。但观此式,自能了然。
裱槅如裱回屏,托以麻布及厚纸,薄则明而有光,不成画矣。
九图:梅窗
制此之法,总论已备之矣,其略而不详者,止有取老干作外廓一事。外廓者,窗之四面,即上下两旁是也。若以整木为之,则向内者古朴可爱,而向外一面屈曲不平,以之着墙,势难贴伏。必取整木一段,分中锯开,以有锯路者着墙,天然未斫者向内,则天巧人工,俱有所用之矣。
《墙壁第三》原文并评:墙壁的美学意义
墙壁第三·小序【原文】
“峻宇雕墙”,“家徒壁立”,昔人贫富,皆于墙壁间辨之。故富人润屋,贫士结庐,皆自墙壁始。墙壁者,内外攸分而人我相半者也。俗云:“一家筑墙,两家好看。”居室器物之有公道者,惟墙壁一种,其余一切皆为我之学也。然国之宜固者城池,城池固而国始固;家之宜坚者墙壁,墙壁坚而家始坚。其实为人即是为己,人能以治墙壁之一念治其身心,则无往而不利矣。人笑予止务闲情,不喜谈禅讲学,故偶为是说以解嘲,未审有当于理学名贤及善知识否也。
界墙【原文】
界墙者,人我公私之畛域,家之外廓是也。莫妙于乱石垒成,不限大小方圆之定格,垒之者人工,而石则造物生成之本质也。其次则为石子。石子亦系生成,而次于乱石者,以其有圆无方,似执一见,虽属天工,而近于人力故耳。然论二物之坚固,亦复有差;若云美观入画,则彼此兼擅其长矣。此惟傍山邻水之处得以有之,陆地平原,知其美而不能致也。予见一老僧建寺,就石工斧凿之余,收取零星碎石几及千担,垒成一壁,高广皆过十仞,嶙峋崭绝,光怪陆离,大有峭壁悬崖之致。此僧诚韵人也。迄今三十余年,此壁犹时时入梦,其系人思念可知。砖砌之墙,乃八方公器,其理其法,是人皆知,可以置而弗道。至于泥墙土壁,贫富皆宜,极有萧疏雅淡之致,惟怪其跟脚过肥,收顶太窄,有似尖山,又且或进或出,不能如砖墙一截而齐,此皆主人监督之不善也。若以砌砖墙挂线之法,先定高低出入之痕,以他物建标于外,然后以筑板因之,则有旃墙粉堵之风,而无败壁颓垣之象矣。
女墙【原文】
《古今注》云:“女墙者,城上小墙。一名睥睨,言于城上窥人也。”予以私意释之,此名甚美,似不必定指城垣,凡户以内之及肩小墙,皆可以此名之。盖女者,妇人未嫁之称,不过言其纤小,若定指城上小墙,则登城御敌,岂妇人女子之事哉?至于墙上嵌花或露孔,使内外得以相视,如近时园圃所筑者,益可名为女墙,盖仿睥睨之制而成者也。其法穷奇极巧,如《园冶》所载诸式,殆无遗义矣。但须择其至稳极固者为之,不则一砖偶动,则全壁皆倾,往来负荷者,保无一时误触之患乎?坏墙不足惜,伤人实可虑也。予谓自顶及脚皆砌花纹,不惟极险,亦且大费人工。其所以洞彻内外者,不过使代琉璃屏,欲人窥见室家之好耳。止于人眼所瞩之处,空二三尺,使作奇巧花纹,其高乎此及卑乎此者,仍照常实砌,则为费不多,而又永无误触致崩之患。此丰俭得宜,有利无害之法也。
厅壁【原文】
厅壁不宜太素,亦忌太华。名人尺幅自不可少,但须浓淡得宜,错综有致。予谓裱轴不如实贴。轴虑风起动摇,损伤名迹,实贴则无是患,且觉大小咸宜也。实贴又不如实画,“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州”。自是高人韵事。予斋头偶仿此制,而又变幻其形,良朋至止,无不耳目一新,低回留之不能去者。因予性嗜禽鸟,而又最恶樊笼,二事难全,终年搜索枯肠,一悟遂成良法。乃于厅旁四壁,倩四名手,尽写着色花树,而绕以云烟,即以所爱禽鸟,蓄于虬枝老干之上。画止空迹,鸟有实形,如何可蓄?曰:不难,蓄之须自鹦鹉始。从来蓄鹦鹉者必用铜架,即以铜架去其三面,止存立脚之一条,并饮水啄粟之二管。先于所画松枝之上,穴一小小壁孔,后以架鹦鹉者插入其中,务使极固,庶往来跳跃,不致动摇。松为着色之松,鸟亦有色之鸟,互相映发,有如一笔写成。良朋至止,仰观壁画,忽见枝头鸟动,叶底翎张,无不色变神飞,诧为仙笔;乃惊疑未定,又复载飞载鸣,似欲翱翔而下矣。谛观熟视,方知个里情形,有不抵掌叫绝,而称巧夺天工者乎?若四壁尽蓄鹦鹉,又忌雷同,势必间以他鸟。鸟之善鸣者,推画眉第一。然鹦鹉之笼可去,画眉之笼不可去也,将奈之何?予又有一法:取树枝之拳曲似龙者,截取一段,密者听其自如,疏者网以铁线,不使太疏,亦不使太密,总以不致飞脱为主。蓄画眉于中,插之亦如前法。此声方歇,彼喙复开;翠羽初收,丹睛复转。因禽鸟之善鸣善啄,觉花树之亦动亦摇;流水不鸣而似鸣,高山是寂而非寂。座客别去者,皆作殷浩书空,谓咄咄怪事,无有过此者矣。
书房壁【原文】
书房之壁,最宜潇洒。欲其潇洒,切忌油漆。油漆二物,俗物也,前人不得已而用之,非好为是沾沾者。门户窗棂之必须油漆,蔽风雨也;厅柱榱楹之必须油漆,防点污也。若夫书房之内,人迹罕至,阴雨弗浸,无此二患而亦蹈此辙,是无刻不在桐腥漆气之中,何不并漆其身而为厉乎?石灰垩壁,磨使极光,上着也;其次则用纸糊。纸糊可使屋柱窗楹共为一色,即壁用灰垩,柱上亦须纸糊,纸色与灰,相去不远耳。壁间书画自不可少,然粘贴太繁,不留余地,亦是文人俗态。天下万物,以少为贵。步幛非不佳,所贵在偶尔一见,若王恺之四十里,石崇之五十里,则是一日中哄市,锦绣罗列之肆廛而已矣。看到繁缛处,有不生厌倦者哉?昔僧玄览住荆州陟屺寺,张璪画古松于斋壁,符载赞之,卫象诗之,亦一时三绝,览悉加垩焉。人问其故,览曰:“无事疥吾壁也。”诚高僧之言,然未免太甚。若近时斋壁,长笺短幅尽贴无遗,似冲繁道上之旅肆,往来过客无不留题,所少者只有一笔。一笔维何?“某年月日某人同某在此一乐”是也。此真疥壁,吾请以玄览之药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