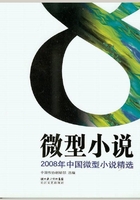剃头匠老梅
--村夫图之八
剃头匠老梅在我的印象里总是那样清瘦,肩上的挑子一头热一头凉。热的一头是一个炉子,炉子上放着一把铁壶。老梅挑起挑子上路的时候,炉下的风门是关着的。挑子的另一头是一只长凳,长凳的面只有一尺半长,半尺宽,凳下的四条脚张的很开,空间里做成上下三层小抽屉。抽屉里放的都是剃头的工具:推子、膏推子用的油壶、刮脸用的刀子,等等。凳子的一头还挂着一条黑色的油光油光的备刀布子。一个男人在凳子上坐下来,老梅伸手把炉子上的风门打开,一会儿,蓝盈盈的火苗就上来了。等把那人的头剃光了,老梅就从热水里捞出一条毛巾来,捂在那人的脸上,然后拿起刀子在凳子边上蹲下来,伸手拉起备刀布子,喳喳几下,刀忍就变得飞快。刀子走在那人的面颊上,青胡茬子就喳喳地响,声音就像菜农蹲在菜园子里割韭菜。
老梅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兵,但是当兵却从来没有扛过枪,他身上背的是一副剃头用的家伙,平时给兄弟们剃头,而更多的时候是跟着团长。团长长着一副又粗又硬的脸面胡子,三天不刮就像野草一样长起来。老梅不但头剃的好,手下的小活也做的干净,掏耳屎,打泪腺,松筋骨,一会儿团长就在他的手下睡着了。有了这段经历,文革中他就成了四类分子,天天要去受批判。有一回批判他,他先要求去厕所。队长袁鳖说,管天管地,管不住屙屎放屁,去吧。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的人影。袁鳖等急了,就亲自到厕所里去找他,一看,他一个人在粪坑边弯着腰低着头站着。袁鳖说,老梅,你装啥熊?老梅说,我先练习练习。袁鳖说,好呀,上台吧。老梅就挑着剃头挑子下了地,社员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先挨批斗后剃头。袁鳖指着剃头挑子说,老梅,这剃头挑子你算是哪一头?老梅指着有火的那一头说,那一头。袁鳖说,放屁,你想冻死我们贫下中农?老梅说,那我是这一头。袁鳖说,放屁,你坐着,让我们站着,你想累死我们贫下中农?老梅左右不是,最后只好说,那我是扁旦。斗完了,袁鳖往凳子上一坐,说,来,给我刮脸。可是一用刀子,老梅的手就颤抖,一不小心就把袁鳖的脸皮割破了。袁鳖很生气,说,你想害死我们无产阶级呀?袁鳖一恼就罚他去菜园子里推水车。
老梅跟着被蒙了双眼的黄牛不停地围着水车转。他突然感觉到水车的结构十分复杂,齿轮式的圆盘怎么正好咬着一节又一节的水车链子?链子上卡着的红色的或黑色的橡胶皮碗儿丝丝地滑过系到水井下的水筒子,就有清凉凉的井水流出来,流着流着就听“碰”地一声响,红色的皮碗就出来了,接着还有水流出来,随后又是“碰”地一声响。只要那头黄色的老牛不停下来屙屎尿泡,老梅就得跟着那水车不停地转,井水就无穷无尽地流出来。怎么会这样呢?老梅想不通,可是老梅的手一摸着水车上的木棍就颤抖。老梅想,完了,我这剃头的手艺算完了,我这手怎么一摸东西就抖呢?老梅感到恐惧,老梅慌慌不安,没人的时候他就从菜地里摘了一个葫芦,拿起一根木棍当剃刀,那个头一样的葫芦一放到他的面前他的手就抖。老梅那天回到家里哭了,老梅哭的很伤心。老梅的老爹拄着拐杖来到他的身边,用拐杖敲着他说,没出息,哭个啥?老梅说,爹,你教我的手艺完了。爹说,咋完子?老梅说,我的手拿不住刀子,一拿刀子就发抖。他爹不再说什么,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布包扔在了他的面前。他爹说,拾起来。老梅把布包拾起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把油亮油亮的剃头刀子。爹往他身边的凳子上一坐,说,这是你爷留给我的,来,在我头上试试。可是老梅拿刀子的手总是颤抖,他看着爹,不敢动手。他爹就生气了,爹说,还站着干啥?老梅说,爹,我这手。爹说,别摆理,刮!老梅只好走到爹的身边,伸出手中的刀子。可是两刀子还没刮下来,他就把爹的头皮割了一道口子,有血立刻注出来。老梅看着爹说,口子。爹瞪他一眼说,瞎当了几年兵,刮!那天把爹的头剃下来,老梅一共在爹的头上留下了二十一道口子,爹的头上伤痕累累,在老梅的眼睛里,爹的头一片血光。可是说来也奇怪,等把爹的头剃好了,老梅的手也不抖了。
多年以后老梅在我们镇子东街开了一个理发店,他仍用老式的理发推子,可是那种推子越来越不好买了,老梅不会用电推子,因而年青人从来不到他哪儿去剃头。到老梅店里去的大多是一些剃光头的老人,再有就是那些长了脸面胡子的人。袁鳖也常常到老梅的铺子里去剃头,他们常常一边剃头一闲唠。有一天袁鳖突然问老梅说,唉,你那剃头挑子还放着吗?老梅说,没有,十多年前就费了。于是两人就生出许多感慨来。那些往事现在讲起来,就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恩舅
--村夫图之九
在我们颍河镇一带有一种手艺人,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把上拧着一根细铁丝,铁丝上系着一绺红布,不用问,那就是打马掌的。我恩舅就是干这营生的。恩舅不是亲舅,和我母亲已经是五伏头上,也就是说恩舅的爷爷的爷爷和我母亲的爷爷的爷爷是一个人。我也算是和他有了血缘关系,别看就这样的血缘关系,恩舅就特别知道和我们家的人亲。恩舅每次推着他的飘着红布绺的自行车路过颍河镇的时候,就一定要往我们家里拐拐,他的车把上不是挂着三四个麻花子,就是滴溜着四五根油条。因而我特别喜欢恩舅到我家里来。恩舅进了我家就姐长姐短的喊我母亲,母亲也就待他特别好。恩舅一来,母亲准会从她的衣兜里掏出二毛钱来对我说,去,给你舅买烟去。可是我买回来的烟恩舅从来不吸,恩舅吸的是旱烟。
恩舅的烟嘴是翡翠的,绿里透亮。他把旱烟袋放在嘴角上,烟袋下装烟丝的荷包儿一晃一晃的,那个荷包上绣着一对鸳鸯。听我母亲讲,那个荷包是一个名叫三妮的女孩子给恩舅绣的,二十岁的时候恩舅曾经和三妮偷偷的相爱,可是三妮的父亲却自作主张把她许给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军官,那个军官曾经在解放开封的时候立过大功。三妮哭哭涕涕在跟着那个军官进了城。有一年那个军官回故乡省亲,我在镇子的东街还见过三妮,那个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吃得白白胖胖穿得像青菜一样的城里人了。我不知道那一次恩舅见没见过三妮,我只知道恩舅一直到三十岁上还没有娶女人,他把那个荷包终日拿在手上,每次见他的时候那荷包都要淡一层,可是荷包总是干净的一尘不染,就像刚刚洗过一样。恩舅到三十岁上那一年才找了一个寡妇。那寡妇是我们镇子东边刘陈庄的,丈夫在焦作的煤矿上挖烟,有一次井下出了事故,他就再也没有出来。恩舅没想到那个寡妇是一个风骚的女人,恩舅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和村里的队长勾搭成奸。风言风语在村子里传荡,后来就传到了我母亲的耳朵里。母亲有一次实在忍不住,就对恩舅说,别光想着在外边做生意,家里的事儿你也得管一管。恩舅说,管啥,不是好好的吗?母亲说,你就不管管你媳妇?恩舅说,她一不怕我吃二不怕我喝,管她干啥。母亲生气了,说,她给你带绿帽子。一句话就把恩舅说愣了。母亲说,你们庄里的人都讲疯了,就你蒙在鼓里。片刻间,恩舅的脸就变得一片灰暗。从此,恩舅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恩舅从此不愿意回家,推着他的车子满世界的转。走到哪个村里找个牲口屋,往草朵里一窝,就是一夜。
恩舅做活都是到生产队里的牲口屋里去。队里拉车的牲口蹄下的马蹄铁磨坏了,就要换下来,不然,牲口就不能走路。我曾经见过一次恩舅给大牲口打掌。打掌的时候必须要先把牲口的蹄掌切平。恩舅的车子后面有一个用生牛皮做成的皮夹子,皮夹里放着大小不等的几把切铲,形状就像鲁智深手上的兵器,只是比那小的多,把不长,二尺左右,顶上装一横棍,可放在肩窝里用力。我曾经偷偷地抱起来过那切铲,乖乖,傻沉。恩舅把牲口的后腿弯起来,架在自己的腿上,就横起寒光闪闪的切刀,只听丝丝的木响,马掌就平了。恩舅从口袋里掏出几只钉子含在嘴里,又在手边的一堆马蹄铁里选出一个和马掌大小相当的马蹄铁来,放在切好的马蹄上。一伸手,一把锤子就从后腰带里拔了出来,三下两下嘴里的钉子就吃进了马蹄里去了,一松手,完了。他的节奏他的动作都快成了艺术了,就像美国的梦之队。人家进球不叫进球,那叫艺术,恩舅打掌不叫打掌,那也叫艺术。可是恩舅空练了一手好手艺,活得不像个男人,他奈何不了他们村里的队长,队长老给他戴绿帽子。恩舅常常生闷气,有时候也喝闷酒。有一年下大雪,恩舅的寡妇女人回了娘家,恩舅就独自一人在家里喝闷酒,然后躺在床上用他的烟袋锅儿吸旱烟,吸了一锅儿又一锅儿,他把烟锅里的烟灰磕出来,丢在床边的瓦盆里。没想到一锅带火的烟灰根本就没有磕进瓦盆里,那火燃着堆在床边的芦苇樱子的时候,恩舅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那场大火在深夜里着起来,映红了半边天。那天恩舅被火烧醒的时候,村里人已经在外边大呼小叫了。恩舅一个人从屋里跑出来,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拿。一场大火把恩舅的家烧了个净光,也把恩舅的女人烧跑了。失火的第二天那个女人回来看了一眼,从此就在也没有回来。恩舅呢?一个人肩上背着他那些重新安装了木把的切铲和锤子,还有那些被火烧红又变黑的马蹄铁,又四处打马掌去了。
恩舅死于1992年,有人在村头的一堆麦秸朵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在他的身边还放着他打马掌用的工具。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家打马掌了,现在到处都通通的机器声,谁家还用大牲口拉车干活呢?没有。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打掌艺人的身影了。马不拉车了,所以这门手艺也绝种了。
染坊
--村夫图之十
染坊的老八,手是蓝色的。染坊就在我们家西边,没事的时候我常常到染坊里去玩。染坊的锅台很高,我站在锅台边踮着脚还看不到锅底。染坊里来一个村姑,递上一个布牌,老八就用他那双蓝色的手在小山似的蓝布里一个一个对。布牌是竹子做的,在破开之前两面都刻上字号,然后一边钻上一个眼儿,分别系上一根细绳子,公的系在要染的白布上,母的呢,就由布的主人拿着。领布时公母对到一块儿,竹丝合缝,看不出一点破裂的痕迹。母亲常常把我们家的土白布送到老八的染坊里去。但是母亲要织花布,用的线就不送,自己染。母亲到供销社里买来几样色,朱砂、空青、石黄、靛蓝……在自家的铁锅里一拐子一拐子的染。线也是自家纺的,母亲的纺车就放在堂屋的山墙下,母亲纺出来的线又细又均匀。夜间醒来,母亲的纺车仍在嗯--嗯--地响。我眯眯瞪瞪地叫一句,妈,睡吧。妈说,你睡。等又被尿憋醒的时候,母亲的纺车仍在嗯--嗯--地响。纺好的线团肚子粗两头尖,一个个码在那儿,白白的耀眼,即使夜间屋里也会亮堂堂的。母亲把染好的线一拐子一拐子地亮在外边的绳子上,红红绿绿,真好看。我从来没有见过染坊的老八染过这种线。线染好了,就把一色一色的彩线缠到竹筒上。一切准备好后,就要上机织布了。母亲每次上土机织布都要选一个黄道吉日,烧上香,跪在堂屋的方桌前磕头。给谁烧香?给谁磕头?不知道。不知道也不敢问,很神秘。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母亲那时敬的是哪一路神仙。开机了,母亲整日坐在织布机上,枣核形的梭子从右手里飞出去,穿过两排稠密的经线,只见母亲脚下一用力,就听呱咚一声布机响,纬线就和经线织在了一起。只是一瞬之间,那梭子又从母亲的左手里飞出来,又听呱咚一声响……那声音一直响下去,花布就一寸一寸地圈粗了。等取下来的时候,那布就能用了。母亲织出的花布手感特别好,摸上去粗粗的,心痒。我们那儿的好多女人都会织这种花布。有的织成花手巾,上街赶集的时候,顶在头上,一街的灿烂。
但织出的白布就不行,还得送到染坊里去染。大多是秋季,要添棉衣了,村姑的篮子里就多了一卷粗布,粗布是白色的。她们赶完集就要拐到镇子东街来,供销社开的染坊就在那儿。一有女人来到染坊里,老八的眼睛就亮了。他忙着拿秤给女人称白布的重量,然后往一个小本上记着。实际上老八并不识几个字,只在耕读里念过半年书,但是老八却好往本子上记人家的名字。叫个啥?老八看着面前站着的女人,很有学问地说。女人说,老捏。老八看着那个女人,抬手挠挠头皮说,咋叫这个名字?那个捏字他不会写。女人就呵呵地笑了,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你写的啥?老八的脸红得像块布,就把本子藏在背后。等那个女人走后,他就在那个老字后面画上两个手指头。两个手指头放在一起就是捏。染坊的门前一拉溜栽有五对高大的杉木桅子,每对杉木桅子上都横着一根同样粗细的杉木。老八是个大高个,不光胳膊长,腿也长。每当看到染坊的门头上冒出蒸气,那就是染好的布出锅了。染布的锅很大,后来我读鲁迅的《铸剑》,就想到了那口染布的锅,当然鼎和铁锅是不同的。老八站在大锅前,用一根竹竿把锅里的布一搭一搭地码在凳子两头。那凳子有三米长,很高,和老八齐胸。两头的布匹搭满了,老八就来到凳子前,一含腰,凳子就起来了,老八一手拿着竹竿一手扶着凳子就出了门,大街上一路滴着蓝色的水珠,老八腿下的深腰胶鞋一路喳喳地往河道里响去。来到河道里,他把长凳放到水里去,用竹竿扯下一搭布,唰--唰--在河里摆,节奏分明,具有乐感。一搭一搭的摆,洗下的蓝色在河面上淌出几道弯弯曲曲的长线,像莫奈笔下的印象派。老八扛着长凳回到染坊门前,用一根更长的竹竿又一搭一搭地把布搭到杉木桅子上去。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蓝得像海水一样的布匹已经搭满了一街,阳光下一闪一闪,微风中一荡一荡。如果张艺谋见了,这小子一准会再来一出《蓝色的海洋高高挂》。
纺车和土布机子二十多前就在我们那里消失了,现在已经没有人穿土布了,所以染坊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前年我回老家时还见过老八一面。使我感到吃惊的是,老八穿的还是一身蓝,土布,当年自己染的。老八的腰驼的很厉害,我几乎看不到他的脸。但他那只提篮子的手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手仍旧是蓝色的。老八是一个例外。多年以来,老八手上的颜色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洗净过?我想,或许那蓝色早已渗到他的肌肉和血液里去了。
重逢
他和妻子从拥挤的车站里走出来,汗水已浸湿了衬衣。
真热。他把手提箱和旅行袋放在地上,然后对妻子说,先找个地方喝一杯吧?
妻子说,也中。
于是,他们又提起行李,朝车站广场的一家冷饮店走去。店里开着空调,扑面而来的凉气给他们凉爽的感觉。一个穿红裙子的服务员走过来,微笑着迎着他们,你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