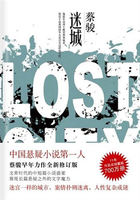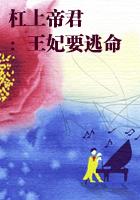佟大板儿是日本人抓的,找安凤阁找梦人隔锅台上炕,不如直接找林田数马。徐德富想想自己和宪兵队长的关系,交情谈不上,眼下种这四百垧地大烟,林田数马特别重视。不久前,陪林田数马去看趟大烟地,茁壮的罂粟令宪兵队长十分满意,一个劲儿地喊幺西。
“找他去!”徐德富决定去找林田数马,不能空两爪子去求人吧?他想日本人喜欢什么,呐摸(琢磨)来呐摸来去,家里的铜鼎舍出来。他有些舍不得,铜鼎是明代的香炉,是同族的巡防军徐将军送给爹徐小楼的,老爷子喜欢,临死前叮嘱徐德富作为传家宝传下去。人要紧,送人就送人吧。相信做一辈子善事的爹也会赞成,尤其为二嫂的事,爹当年可怜田姑娘领回家来,才有了后来的二嫂……爹经常说,对田家姑娘高看一眼啊!他老人家拼命撮合二弟德中和她的婚姻,总因二弟不从分手而告终,令人欣慰的是她遇到了佟大板儿,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得红火火,抚养着德成的孩子,也有了自己的女儿娟儿,突然给抓去当劳工,干点苦大力的活儿倒没什么,开山放炮出意外怎么办?徐德富左想右想,想得很多,才有了舍出传家宝的义举。
“大哥你这是?”佟大板儿问。
徐德富回过神来,举了举手里的装铜鼎的布包,说:“唔,大板儿你回来了,回来就好。”
“我家去了,大哥。”佟大板儿说。
“回吧,回吧。”徐德富说。
佟大板儿走进自己家,二嫂正和丁淑慧絮免腰棉裤,先前二嫂说:“大板儿穿上穿不上这棉裤,两说着呢!”
“瞧你说的,大哥和四凤分头找人呢。”丁淑慧说。
“唉,这年头办事那么容易啊!又是和日本人办事,不易啊!”
“大哥喂埯子(预施的诱饵),大嫂说准备把铜鼎送给林田数马……”丁淑慧说到这儿,猛然抬头佟大板儿进来,喊了声,“啊呀,回来啦!”
一头棉花毛子(飞起的细棉绒)的二嫂一下子愣住,嘴瘪嘟半天,才冒出一句:“打路鬼(怨怼语),惦心死人啦。”
“该烧晌午火啦(做中饭),我下午再来帮你絮棉裤。”丁淑慧寻借口离开。
“在这儿吃吧。”佟大板儿挽留道。
“不啦。”丁淑慧下炕,边走边提鞋。
屋内剩下佟大板儿和二嫂,她问:“你咋蹽杆子(逃)的?”
“没蹽杆子,一个警察带我回来的。”他火急一件事情,边说边解裤腰带。
“干啥?”她问。
“你说干啥?”
“大白天的干啥……”
“多少天没干啥了,憋狼哇的(厉害)。”
“憋冒泡也得憋着,大板儿,你刚回来,大家都要来打听。晚上,晚上再干啥吧。”二嫂哄他,让他弄得也真想干啥了,她问:“警察说什么没有?”
“说啦,安凤阁说四凤救我出来。”佟大板儿说。
到底还是四凤办成了这件事,二嫂心里感激四凤。
“你和我去见四凤,当面感谢她。”佟大板儿说。
“不用动,四凤听说你回来准过来。”二嫂的话音未落,四凤同尹红来,气氛有了微妙的变化,兴奋在她脸上悄悄敛起。
“回来啦,大板儿。”尹红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是风俗的原因,二嫂管徐德中叫二哥,今日仍然叫着,佟大板儿则是妹夫,尹红是嫂子,论年龄佟大板儿比尹红大,可是年龄多大也是妹夫,嫂子永远比妹夫大。
“嗯哪,嫂子。”佟大板儿应道。
“姑父,”四凤关心人要比在场的两位细腻些,看佟大板儿的手老茧加血口子,问,“活儿累吧?”
“哪是人干的活呀!”佟大板儿诉苦,他还没机会诉苦呢!四凤提起劳工的生活,他苦水浸透周身,“干着牛马活,吃着猪狗食。”
一句话包圆,劳工悲惨的境地生动地描述出来。
“日本人修啥,用那么些人?”尹红怀着自己的目的问,她要知道的不是劳工生活。
“上百个勤劳奉公中队,一个中队40人,老鼻子(老多)人啦。”佟大板儿说,“掏空半座山。”
“工程可不小。”尹红继续套弄话道。
“听说是建一座仓库。”佟大板儿说。
话题没进行下去,谢时仿进来,唠了几句嗑儿后说:“当家的叫你们各屋晌午别烧火,都到上屋去吃。”
上屋是习惯的叫法,它家庭权力的象征,在獾子洞村祖屋老院,老当家的,少当家的都住正房宽敞明亮的上屋,搬到药店院子来,真正的上屋是药店的门市房,徐德富住的也是厢房,全院老少仍然叫他当家的,实际他也是当家的,他住的屋子当然是上屋了。
“我刚买回个羊窠郎(扒了皮的羊腔子),伙房加工呢,饭晚一会儿开。”谢时仿说完走出去。
“你去帮做饭吧。”佟大板儿指使妻子,“几十口人,得做一大锅饭,人少忙不过来。”
二嫂扎上围裙,四凤也说去帮厨跟了出去。
“我恍惚看见一个人。”佟大板儿对尹红说,他只能对徐德中和尹红说,在早小张受伤让当家的给藏在他家的里屋,近日又在药店里见过他,心想一定和徐德中两口子有过场(往来),而且非同一般的过场,因此才对她说。
“他怎么样?”
“近几天没见到他,不过挺好的,还当上了勤劳奉公中队长。”佟大板儿说,也怪了,他见到小张,却没见到徐梦天。
小张当上勤劳奉公中队长,这个消息尹红听到很欣慰,起码他顺利进入工地,队长身份有利搜集情报。至于几天没见到他,也许完成了任务,回到了抗联密营。
“他是自愿去的,还是……”他说。
“嗯?”
“我的意思被抓去的,想办法救他出来,那是火坑。”佟大板儿解释道,“在那儿,人不死也得掉层皮。”
“我跟德中说说。”尹红道。
山沟里的毛驴走在平展展的街道上,乐颠颠的摇头摆尾打响鼻,看到同类,咯嘎地叫起来,这一叫不起眼,全镇的毛驴随着叫,谁家要是有死人准借音儿,街上行人投来目光,是看驴还是看驴驮的女人说不准。
驴背上颠儿颠儿一个小媳妇,引起街上顽耍的孩子们的联想,口诵一首诙谐的歌谣:呜哇嘡,呜哇嘡,娶个媳妇尿裤裆!
“爷,你听他们说什么?”横行子道。
“他们玩呢!哎,从现在起你叫谢荣,不能说黑话,以免让人发现我们的真面目。”徐秀云还叮咛,“记住你是我的小叔,你管我叫嫂子,我是你的亲嫂子。
“嗯哪。”
“老奤腔也板着(控制)点,说当地话。”徐秀云一番交待,路过一家叫润古斋的门前,她说,“停一下,谢荣。”
“吁!”谢荣拉住驴,问,“到了吗?”
“没到。”徐秀云望着裱画店的幌子,当然感兴趣的不是那行“苏裱唐宋元明清古今名画”的字,她想到“徐筐铺”,那时她和徐德龙、丁淑慧就在这个房子里开筐铺,令人怀念的岁月哟!徐德龙赌瘾再发,她一气离家出走,后来的事情她不知道,但能想象到,德龙赌输了铺子……她心里苦滋滋的。
“嫂子!”横行子叫她。
“噢,走吧。”徐秀云手指前方,“拐过这道街,就看见同泰和药店了。”
徐家药店在徐秀云到来时刻,主要成员都不在。徐德富和谢时仿去了大烟地,铜刀买来了,他们带上去教长工们割烟浆技术。尹红随徐德中出诊没回来,二嫂陪着徐郑氏到老爷庙去烧香。
“你们是?”店伙计问。
在药店前徐秀云下驴,胳膊弯处挎着布包袱,说:“我们来串门,请禀告老爷太太。”
“他们都出去了。”店伙计说。
“还有谁在家呀?”她问。
“四奶奶。”
丁淑慧?”
“是,四奶奶在。”
“叫她。”徐秀云一听丁淑慧在,心中高兴,扑(投奔)她来的。
“秀云!”
“淑慧姐!”
“你这是打哪儿来呀?”丁淑慧问。
“让我进屋再说不行嘛!”徐秀云说。
“瞧我光顾乐了,进屋,进!”丁淑慧转向牵驴的横行子,“他是?”
“呜,我的小叔。”徐秀云说。
院子里拴了驴,同丁淑慧一起进屋。
“你一走这些年没个音信儿,把我忘干净了吧?”丁淑慧扒查(责备)几句,瞥横行子一眼,说,“你的小叔,找人家啦(再嫁)?”
徐秀云也看横行子一眼。
“嫂子,我去喂驴。”横行子说,想躲出去。
“去吧,加小心谢荣,驴不老实,爱尥蹶子。”徐秀云叮嘱道。
“嗯哪!”横行子出去。
徐秀云编排下去,说:“他哥比他壮,菩派大身(身材胖大)的。”
“干啥的?”
“种地的呗。”徐秀云说。
“体格壮好,种地的好。”丁淑慧阴郁起来,喃喃道,“过穷过富,全全科科地在一起比啥都强。”
是啊,全科对这两个女人来说是一种奢望徐德龙在世的时候,他们三人一起过日子,整天有说有笑,割条子、编筐卧篓……徐德龙重新去赌,徐秀云用离开他相威胁,赌红了眼,没拦住他。
“德龙,忘了我们拉勾上吊撇土垃坷。”徐秀云遗憾道。
本地有一风俗,将土块抛上空中,表示订盟永远不反悔。送人之物的歌谣: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当时站在筐铺前,徐德龙土垃坷抛向天空,是一种告别,告别赌博,可是起誓靠得住吗?
“德龙最终死在赌上。”丁淑慧叹然。
“他怎么死的?”徐秀云闻徐德龙死在赌博上,却不知道细节,“听说和日本人赌。”
“跟宪兵队长角山荣掷骰子,德龙赢了军刀。”丁淑慧说,“德龙心明镜宪兵队长赢不得,他为什么要赢呢,现在我想明白了,争口气。”
“争气?”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丁淑慧说。
一个赌徒能够壮烈地死,为家乡老少爷们争了志气,在那个刺刀和铁蹄的时代,难能可贵。
“全镇大出殡,为德龙送行。”丁淑慧说。
亮子里镇记忆赌徒徐四爷与宪兵队长掷骰子的故事,人们钦佩的是明明赢是死输也是死的徐德龙,他以赌徒独特的式,向世人表明,他不怕日本人。
丁淑慧说大哥在德龙死后,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徐家在德字辈上,徐德龙因赌而名声,吃喝嫖赌抽又是家规所不容许的。当家的长兄徐德富为此大伤脑筋,起初德龙年纪小他只伤脑筋,多次劝诫、管束不成,最后伤心,直至轰出家门。两个人--丁淑慧、徐秀云--在赌徒身边,他戒了一段赌,短短的一段,末了还是回到赌桌,导致徐秀云离家出走。
憎恶男人赌博与徐秀云的经历有关,赌博是她最恨的字眼,心灵上的永远疤痕,她的父亲徐大肚子是三江有名的赌徒,输掉妻子,徐秀云的亲母不堪忍受赌徒将她当筹码在桌上赌来赌去上吊自杀,徐大肚子死得更惨,输得一无所有最后垫了壕沟,实际是街道的排水沟,野狗啃去了半张脸。这样的经历她能不恨赌徒吗?她的经历中还有曲折一段,那就是她和徐德龙的情感故事,青梅竹马却因徐秀云的爹赌钱,遭到徐家当家的徐德富的反对,而没成婚。徐德富给四弟德龙娶了丁淑慧,徐秀云却在被爹输给国兵漏子后,偶遇徐德龙,破坏中断的情缘,伤口一样长好,更准确说徐德龙从赌徒徐大肚子手中赢来了她。
“大哥让德龙进了坟茔地,立了碑。”丁淑慧说。
作为赌徒徐德龙来说,无疑是死后最高待遇。民俗:横死的(掉井、垫车脚、雷劈等)人不能进祖坟地。徐家规定更严:不是寿终正寝或病死,不能直接葬进坟地,埋在祖坟地边儿上,在阴间等到阳间他的岁数到,才由后人迁入祖坟地和先人在一起。徐德龙在壮年被杀,虽不算殇,毕竟属于横死之列,葬在祖坟地边上理所当然,徐德富冲破世俗、打破家规,破例将他直接葬在祖坟地,一切都说明了,是对赌徒兄弟的一种承认。
“过几天我去给他上坟。”徐秀云说。
“这回你来家多住几天吧。”丁淑慧真心挽留,多年未见,有说不尽的话,亲近不够。
“来看看你,住几天我就得回去,婆家……”
“出来了就出来,静心呆几天。”丁淑慧说。
“我几年没来家,挺想你们的。”徐秀云真挚地说。她没什么亲人,徐家人是她的亲人哪。
“秀云,二哥回来啦。”
“二哥?”
“徐德中啊,还带回来俊俏的二嫂,现住在这院子里,二哥当坐堂先生,二嫂当护士。”
“哦。”徐秀云掩饰住惊讶,有个丁淑慧不知晓的秘密,她已经见过二哥徐德中,在一特殊场合--蓝大胆儿绺子上--见过他,消灭角山荣后,他不知去向,怎么回来当坐堂先生?
“你八成记不得他,离家十几年。”丁淑慧说。
“呜,对对。”徐秀云支吾道。
“二嫂和佟大板儿也住这院里。”丁淑慧说到另一个二嫂,未和徐德中圆房后嫁给佟大板的二嫂,“他们有个闺女。”
“小闯子呢?”
“你记性真好,梦人长大了,没人叫他小名啦。”丁淑慧说,“在四平街念了书,日本语学得好,还交了个日本女朋友。”
徐梦人交女朋友的事在徐家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音强烈,他一气之下回到四平街去,有些日子没来家。
“交日本女朋友,大哥怎么看?”
“心里不同意嘴没说”,丁淑慧说,“二哥反对,梦人同他系疙瘩(结仇)了。秀云,老话说得好,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
“你说梦人和日本女孩是……”徐秀云愕然。
“是啦,肯定是。秀云,哪个国家的人有啥,还不是做饭喂猪生孩子。”丁淑慧把事情看得刮风下雨那样简单。
徐秀云理解徐德中,他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她不能对丁淑慧说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