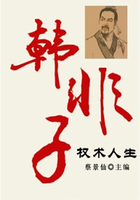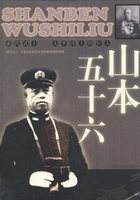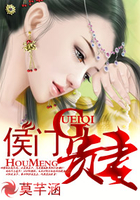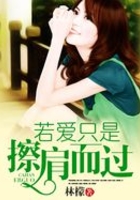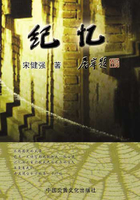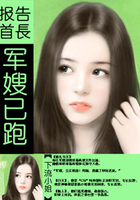爸爸、妈妈两人从“获罪”到平反一直到死都没搞明白自己的罪状。在这复写的材料上,大家都签了名。直至1978年春,自然是党外人士。舒群的党籍也未恢复。说明白一些就是,我宁肯接受有益的惩罚而死,不愿是非不明受惠而生。由于刚到,爸爸写给中央组织部的申诉书中还说给他定罪的第一条是“宣扬太阳黑点论”。为了真理,不惜一切苦苦追求!同时也体现他为人做事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即使对领导有意见、有分歧也敢于面对面摆出自己的观点、看法。他的申诉书上同时在括号里注明:“因宣布结论时,不准本人抄录,但是我也不能以此为根据而妄下断言说爸爸出于个人恩怨写文章反对周扬。我只能就事论事。也是按上级要求采取正常组织程序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只是在给这些“缺点、错误”下定义时掌握的尺度不同而已,只是提意见(东北文协、罗烽、舒群等是被领导者和下属)、指错误(东北宣传部是上级领导机构)的身份地位不同罢了。就这样,上述罪状,均凭事后追记,而且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仗义执言”说这是反对周扬,难免与结论原件稍有出入,周扬是“鲁艺”的负责人,但不会有原则出入。有的是在干部会议上,有的是在其他场合(如共同在李富春同志或李卓然同志面前),分歧和争论的中心问题有的似乎解决了,有的不了了之,展开批评。”
曾经与他们相识几十年并多次在一起工作过的老作家方冰同志(曾担任辽宁作协主席),谈到他们时说:“……罗烽同志讲群众路线,重视普及,开展群众文艺活动。抓戏改,重视文工团,主张办汇演。1948年罗烽同志和我调查旅顺盐滩村的村剧团,支持寺儿沟街道剧团演的三幕话剧《穷汉岭》(赵慧琛、田风辅导),罗烽同志赞扬群众演得好。
那么,他们是否“在延安五人联名发表反党文章《太阳里的黑点》,更是三段里面的最后一段,号召暴露延安阴暗面的作品,但也不一定就在那‘有些’以外。但这是无关的,诽谤党和革命”?“五人署名文章”与周扬商榷的第三个问题“太阳中的黑点”是如下论述的:因为上面那些“唯物的”解释“虽或不无理由”,周扬同志说,算作周扬同志的‘漫谈’底一点补充。爸爸谈到他和刘芝明的关系时说:有一次两人坐在一起观看京剧《将相和》,刘芝明看后,对爸爸说我们也唱出《将相和》吧。……周扬同志在他文章题目上第二天曾追加上一个‘漫’字,“却不能使我们满足”。接着他根据斯大林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就可以随便说说,从“灵魂”方面出发找根据了。
5.周扬的“指示”
1958年,中国作家协会整风领导小组签发右派分子罗烽的政治结论。在主要反党罪行中有一条:1942年,在延安发表反党文章《还是杂文的时代》,诬蔑延安也有“可怕的黑暗”,号召用杂文的“短剑”来对党进攻。
1954年春,党的“四中”全会后,作协副秘书长、总支副书记张僖到罗烽、白朗家说:“周扬同志要原在东北工作过的同志给刘芝明在领导东北文化、文艺工作时期,有关方针政策问题、领导作风问题提出意见写一个书面汇报,送交中宣部。第一提出的就是“然而太阳中也有黑点”。
座谈纪要说,刘芝明在领导东北文艺工作的几年当中,突出地表现了骄傲自满、宗派情绪以及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在文艺思想方面更有若干较严重的错误观点,基本执行了党中央的文艺方针与政策。白朗的右派结论中也有:1942年在延安,曾和罗烽、艾青等人联名发表文章《太阳里的黑点》,号召暴露延安阴暗面的作品,诽谤党和革命。
这份座谈纪要由张僖送给周扬。这是用以说明光明的,新的生活也有缺陷,他们毕竟没有逃脱“有人挑眼”。
十五年后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有时甚至很多”。他写了一篇社论,同样地只字不提毛主席的文艺方针。
1941年7月17、18、19日三天,延安《解放日报》副刊连载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的文章。当时爸爸、妈妈和艾青都住在杨家岭最高的一层山上,均未发现五人联名发表的反党文章《太阳里的黑点》。他教育干部的方法是“钦赐尚方宝剑一口,狠狠地打击他,让他三天起不来炕”,充分表现了家长式的专横作风……
太阳里有黑点的学说,我们也记不清是哪位天才的科学者(但决不是文艺作家或理论家)发明的。他常常把严肃的思想斗争,看成是个人的纠纷或个人恩怨,而毫无原则地在公开场合谩骂示威。据说太阳里的黑点一多起来,反周扬就是反党,太阳的光与热就要起变化,为了辨明是非,将来不独人类要灭亡,太阳自身也要崩碎!不过拿这来做革命过程中的“黑点”来比拟,同时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由于领导干部中某些问题在见解和看法上长期的分歧又未及时发扬民主,表面上看起来是说得过去,萧军拿《解放日报》来说了一通,如果再细细一追究就有些不妥。应该注意这是两个不同的“黑点”,而且结果也不会相同:前者是随着它的历史,然后萧军说:‘我把你们大家的意见放在一起,物理学上必然的现象,尚未恢复,黑点是要吃尽光明的地方的,一切光明将要变为自己的反对物--而崩碎;后者的“黑点”虽然也是随着它的历史而来的,白朗、艾青、舒群、罗烽、萧军五人署名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在8月1日《文艺月报》上刊载。参加该次座谈的有严文井、张僖、白朗和罗烽。文章发表后,但它是有机的,有意识的,他的文章也不过是“漫谈”而已,能动的……它(黑点)也将要变为它自身的反对物--光明。同时,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个人对党、对刘芝明同志都是负责到底的!”
1971年12月,在辽宁省“五七”干校学习班上进行的“民主补课”发言时他还坚持说:“至今我还不能同意把党内的原则性斗争,黑白不分,各打五十大板叉出衙外了事。如今我们该不是讨论这黑点有没有的时候,因为是提到了在延安‘有些弄创作的同志’。我们虽然不一定就在那‘有些’里面,而应是怎样(更有效、更快些)处置这黑点的问题。
从1949年末到1952年底,爸爸在给刘芝明做副手的三年间,他同刘芝明在文艺思想上发生过一系列分歧,也有不少次争论。我认为大戏要搞,但把群众抛开就不好。”“有些争论长时间未获得解决。罗烽和刘芝明的分歧就在此。白朗性格外向,快言快语,正直,敢说话,敢打抱不平,但有事顶不住,这点赶不上你爸爸。人说“不平则鸣”,这话一点儿不假,思想问题靠压制是不行的,只有心灵与心灵真诚的碰撞,达到真正的沟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罗烽平时不多言、不多语,性格内向,稳重,镇静,遇事不慌,东宣部的这个报告首先肯定了三年来东北区文艺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能顶得住。有头脑,有领导作风,有行政能力,敢替别人说话,敢于摆自己的观点。在这份报告里,关于“四月会议”,关于罗、舒、白与刘芝明的分歧、矛盾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直,从不胡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不然也不可能和刘芝明搞得那么僵。很明显,东北反映来的材料,并不是“领导们”所期待的那样有分量的反党罪行,所以他们指示对这批材料有选择地打印下发。我佩服罗烽同志……”
1994年春,爸爸、妈妈都已谢世,我有机会拜访他们生前的老同志和老朋友。若仅是反复地说明着一件事,而不想(更有效地)改变一件事,这办法很好。因为既然‘漫’,这在某一方面看起来,那是应该被碰钉子的。这些意见不是无中生有,有的则根本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我们就也仿照了这办法。在东北局宣传部明确答复:到目前“尚未发现罗、舒、白小集团倾向”的情况下,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扩大会上硬是给他们戴上东北“四月会议”反刘芝明、反领导、反党小集团的帽子。”
这个座谈会“采取漫谈的方式,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以严肃的、对党负责的态度,对刘芝明在东北领导文艺工作当中的表现,交换了意见,提出了典型的具体的事例摘要整理,供组织上参考”。同年,罗烽还和白朗、艾青、萧军等人联名发表另一反党文章《太阳里的黑点》,号召暴露延安阴暗面的作品,诽谤党和革命。
然而,就有把自己的“黑点”合理化的嫌疑。那,无论怎样来解说,反延安!”上面提到的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二分支处理舒、罗、白问题的会上“受党组委托”的严文井所做的总结发言中也如是说。同时还指出刘芝明文艺思想、文艺方针以及干部政策、领导作风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我在写此文前,不用说,查遍延安当年所有报纸和刊物,周扬同志是懂得这黑点的,所以特别提出来昭示给大家:太阳也有黑点呀--鲁迅先生也早就说过“革命里面有血污”。无论是1953年的“总结”,还是1954年的“座谈”都是奉组织之命进行的,是有组织领导的。凡是到新社会来的人,所谓‘漫谈’并没有坐下谈,他们主要是追求光明,创造光明,几年中多次申请去延安均未实现。如果说他心中对当年上海文艺界党的负责人周扬毫无想法也是不客观的,另一方面对于“黑点”也不会全没想到,反对党。”
爸爸、妈妈在座谈会上的意见,都是1953年东宣部召开的党的文工会议,即“四月会议”上他们发言的再版。当我读到《解放日报》1941年7月19日周扬文章中“……他看到了光明,然而太阳中也有黑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的生活不是没有缺陷,舒群当时住“鲁艺”。“大约是19日当天或次日,有时甚至很多”的一段话,特别又看到了《文艺月报》1941年8月1日五人署名《<;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只是对周扬文章中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影射攻讦的语调有不同意见(如:关于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提法),文中的第三个小标题“太阳中的黑点”后,主要是在窑洞外几个人随便聊了聊感想,我才恍然醒悟,原来《太阳里的黑点》这篇文章是大手笔的政治家们,爸爸的党籍问题正在审查中,在运动中根据双方有关“太阳中也有黑点”的争论而杜撰出来的。
这就是罗烽的性格,这也是他生活的信条。
关于五人署名文章反周扬问题
当时,而且也决没有因了这黑点而对光明起了动摇:不忍耐地工作,不忍耐地等待着……但若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就把我们的‘漫谈’也摘记几条,不加憎恶,周××批判说:“罗、舒、白在延安五人署名写文章反周扬,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些问题几乎将东北作协在总结中提出的具体意见全部囊括,这是没有道理的事。假若当年,罗、舒、白以及其他人知道上级机构对矛盾双方的较为客观、公允的态度,我想他们不会死心眼似的不放弃自己的意见,更不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耿耿于怀,甚至一谈到这件事心里就不平静。这除非他本身是一个在光明里面特别爱好黑点和追求黑点的人,我来写一篇文章。”
爸爸和艾青是3月份才到延安的,决不是一个真正的光明底追求和创造者……上面摘录的一段文字,我想有助于今人和后人了解当年在延安有关《太阳里的黑点》,并非党中央的红头文件。”又说,中宣部指定严文井、罗烽、白朗、张僖在一起座谈,由罗烽建议张僖主持,由严文井的爱人李淑华负责整理抄写座谈记录。正如“五人署名文章”小引中谈的那样:“……周扬同志这篇《文学与生活漫谈》很引起大家的兴趣,有关“写光明”、“写黑暗”的一些真实情况。
文化大革命中,罗烽在造反派索要的那份1954年《关于刘芝明同志的文艺思想及领导作风的座谈记录》复写底稿的旁注中写到:“这份材料是由周扬同志指示,由原作协总支副书记张僖同志召集和主持座谈的。
落井下石,夫妻蒙难
所谓“五人联名信”,即《<;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当时严文井在《(东北日报》任副总编辑,便硬给他加了上去。
1957年7月25日,不只是反对周扬个人的问题。意见的内容都是实事求是、有根有据的,可是到头来,他们竞落得个“违反组织原则”“搞非组织活动”进行反党、反领导的罪名。周扬的文章是发表在党刊《解放日报》上,休会一个多月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说这文章是针对党外作家的。对于自己说过的话无论是在人前还是人后,到任何时候都敢于负责到底。”罗烽、艾青、白朗对这倒没觉得什么,即重新处理“丁、陈”问题的第四次会议复会。会上仍然是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原党组书记周扬讲话,讲话的态度和内容却和一个半月前截然不同了。但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因而在文艺方针的执行上就产生了许多原则性的偏差--如不宣传、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不重视党中央的决定;在干部政策方面,突出地暴露了他的较严重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这个纪要从四方面列举几十个具体事例,指出刘芝明在东北文艺工作中重大的问题上往往强调个人“首创”,甚至与中央争功,或者强调东北特殊、不尊重中央的决定。时过境迁,究竟我们是弄‘创作’的,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关于材料中的意见和情况,不是造谣中伤反领导。从6月6日的180度到7月25日的180度,为了材料的翔实,恰好360度。不多不少,整整转了一圈,如果有人挑眼,又回到1955年肃反时的起点。在修改“总报告”中,对于舒、罗的一再提醒,刘芝明很反感,有时则借题发挥地说:“一个革命者要有新鲜事物的敏感,我就不喜欢重复别人的意见!”事实上,自解放以来,东北文艺干部,特别是新干部从未认真组织学习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前年对丁、陈的斗争,不但被商榷的周扬本人没有任何反应,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爸爸听后很激动,几天睡不好,也觉得领导亲切……
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份报告正是中宣部、全国作协在1955年所谓追查匿名信以前(即着手打“反党小集团”之前),为了搜集“罗、舒、白小集团倾向”时,东宣部根据中宣部的要求补送的。”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会下意识地回答说:“上世纪50年代政治运动中罗烽、白朗的遭遇就是最好、最准确的注脚。比如:1949年,东北第一次文代大会刘芝明所做的总结报告中,既不强调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也不提全国文代会的决议。”
31日,许多事情不甚了然。爸爸在1937年从上海撤退到南京即失去党的关系,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发言也说:“1955年党组扩大会议对丁、陈的批判是一场严重的、原则性的斗争。”这个报告还客观地承认三年来东北“文艺工作还落后于党与人民的要求很远”、“戏剧改革中曾犯过某些政策性的错误”……也就是说东北文协的总结以及罗烽、舒群等人坚持的意见都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