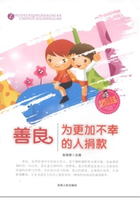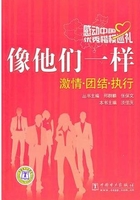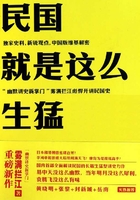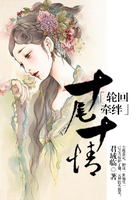到了20年代末,情况大变。那时左翼文艺思潮盛行,以阶级性的眼光来判断文学的价值成为一时风尚。随着创造社大部分成员的转向激进,“五四”的“文学革命”迅速地转向“革命文学”。此时开始激烈地反对文学的个人性和趣味性。对所谓的“个人主义”和“趣味中心”抨击最厉害的是后期创造社的那些人。他们大多数是留日学生,信奉“普罗文学”的思想。最典型的是成仿吾发表于1927年《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这篇文章,此文激烈批判当时的文艺界“就好象许久被人把口封住了一旦得了自由的一样,都是集中在自我的表现”,“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早就堕落到趣味的一条绝路上去的”。他认为这种“遭遇着趣味这种臭气”的倾向不是文艺的正轨:“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艺理论集二》,4~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其实,即使是如鲁迅这样的毕生以社会承担为己任的先行者,他的一贯的激烈之中,也存在着通达的一面,并没有后期创造社同人这般的“彻底”。鲁迅在他的那篇着名的文章《小品文的危机》中,有一些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那就是:“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紧接着这句话,他还说,“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尽管他对这种“愉快和休息”作了限定,即:“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全集》,第4卷,576~577页。)鲁迅的“通达”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基本精神,即一方面把文学的功能定位于改造社会的大前提下,所以,他首先要求于文学的,是作为武器(即“匕首”和“投枪”)的性能,是为求生存而能够杀开一条血路的东西。然而,文学同样感知了那个时代追求个性解放的、对于个人存在及其欲望的尊重的总体氛围,有它的自由性和民主性的一面。因而,它能够注意到文学毕竟存在着那种有限度的和有节制的“愉快和休息”的性能。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在一定的历史空间里,文学的风格和样式是多样并存的,尽管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对立和抗争,但却不会是排他的、更不会是唯一的。这种相对宽松的心理承受,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普泛性的事实。例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影响力相当巨大的文学社团,它们的宗旨各有不同,但却并行不悖,各自沿着各自的路线发展。文学研究会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已经过去了”。据茅盾介绍,这个文学社团的宗旨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实,表现并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与此判然有别的是创造社,他们是倾向唯美的一群,强调“文学除了对于外界的使命之外,总有一种使命对于自己”,“有不少人把这种对于自己的使命特别看得要紧,所谓艺术的艺术派便是这般”(郑伯奇:《创造社的倾向》,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5。)。但即使如此,创造社的作家同样“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烈的关心”,“他们依然是在社会的桎梏之下呻吟着的‘时代儿’”(同上。)。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现在进行的讨论。首先,它说明“五四”当时对于艺术主张各不相同的艺术派别的宽容和大度,同时也恰好证明了即使是艺术自身规律之倾向的社团如创造社者,它依然不能完全脱离苦难深重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就是说,它们的文学依然是沉重的。
革命意识的介入,使原先那种近于极端的文学主张获得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意识的核心是阶级论,即社会人群的阶级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种新兴的理论被有效地嫁接在中国本来就矛盾重重的社会肌体之上。它造就一种幻觉,即认为中国近代以来所苦苦追求的强国新民的理想终于显示出明晰的线路。来自域外的理论使国人的悬念有了答案。似乎它的到来,往日所有的纠结和悬置全都迎刃而解。新文学为寻求社会进步而拥有的批判性,如今非常明确地与激进的政治理念完好地契合了。一向不甚明晰的文学变革的设想,迅即从政治意识的定位中取得了明确的方向感。
大约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色彩很浓的文学理论大量引入并发表,这些文章更加猛烈地批判文学的趣味性,“凡所谓趣味都是这样的,它是路旁的一个迷魂阵”(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艺理论集二》,8页。)。持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全人类社会的改革已经来到目前”,对于当时的文学态势,也有激烈的批评:“在整个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二重压迫下的我们,也已经曳着跛脚开始了我们的国民革命,而我们的文学运动--全解放运动的一个分野--却还睁着双眼,在青天白日里寻找已经迷离的残梦。”(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1928-02-01。该期编辑王独清在“余谈”《今后的本刊》中说:“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一篇最重要的论文,简直可以说是今后同人要从事于新努力的一篇宣言。”本期同时还发表郑伯奇的戏剧《牺牲》,蒋光慈的小说《菊芬》。王独清对此评价说,它们“都充满了革命的情绪”。在这篇“余谈”里他还说:“新时代斗争要开展在我们的面前,处在这样的一个转变期间的我们,应该持一种真实的态度:我们是应该向后退呢,还是应该去欢迎这新时代的来临?……我们要承受新时代将开展以前的朝气,我们要参加催促新时代早临的战线,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做些自觉的工程作欢迎新时代的礼物。”这一期刊物所登的作品、理论以及编者的编后谈,构成了一种“事实”,即“五四”新文学已经转型。而这种转型却是由于中国社会“业已”发生了“新时代”的转变。这是当时创造社同人的愿望和判断。它也代表了中国在抗战爆发前的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个事实,也是当时的“文学主潮”。)
可以说,从近代的文学改良直至“五四”的文学革命,都是在中国社会危机的背景上展开的。试图通过文学的变革以达到消除危机的目的,这种追求的目标的确立及实行,在很长的时期中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和充满矛盾的。但是在20年代末,这种追求由于与强劲的革命思想的遭遇,无啻于给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注入了兴奋剂。仿佛是得到了证实,即新文学所追求的强国新民的梦想,可以凭借着那时流行的那些话语得以实现。一批由留学生引进的新潮理论似乎造成了“事实”:那就是认为一个崭新的社会革命正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因而,当受到“五四”思潮影响的国人,面对着救亡和启蒙两项使命感到踌躇时,因为有了上述那种引进从而使先前的矛盾得以缓解。“救亡”甩下了它的兄弟“启蒙”而单独前行了。这样,当“救亡-革命”的公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早已对此习以为常而不会大惊小怪了。
对于中国文艺界来说,当它“顺利”地处理了上述那一对矛盾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文学的社会性和个人性这一对新的矛盾。这是一对更复杂、更深刻、也更棘手的矛盾。“五四”初期关于“人的文学”的议论烟消云散之后,在它消失的沿途抛撒下一路“个人主义”的碎屑。对个人主义的申讨始于20年代末,盛于五六十年代,而终于90年代。这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路程。它的背景非常复杂,其基本动机则是社会功利。现在不妨再把话题拉回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那场革命文学运动。那时的目标非常明确,即革命是倡导集体性而反对个人性的。而在文学上,则是要以集体的价值和趣味来排斥和替代狭隘的个人主义。革命文学,它天生地总与大众利益以及社会群体的思想性有关。
在这一方面,蒋光慈的论述最多,也最详。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一文就是把文学放置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的环境中考察并提出要求:“现代革命的倾向,就是要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而创造一个比较光明平等的,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与此相对应,他认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的一分子,若这个人的行动是为着群众的利益的,那么,当然是有意义的。否则,它便是革命的障碍”,“革命文学的任务,是要在斗争的生活中,表现出群众的力量,暗示人们以集体主义的倾向”(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原载《太阳月刊》,1928(2)。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二》,4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事情这样开了头,就有源源不断的后续者的发挥。这些后续者越来越表现得自信、坦率且坚定。到了毛泽东,他更以断然的语气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864、8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此后,革命文学的性质与作用似乎就专注于对于个人主义的批判。在一批革命文学家的心目中,个人主义是罪恶的,等同于资产阶级,而集体主义则是圣洁的,等同于无产阶级。
在这一点上,郭沫若的主张最为彻底。他以麦克昂的笔名发表的《桌子的跳舞》,激烈批判中国作家“他们都是些很舒散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只是想绝对的自由”,他们表现的是“极狭隘,极狭隘的个人生活的描写,极渺小,极渺小的抒情文字的游戏”(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1928-05-01。本期编辑后记写道:“革命文学的激潮已经传到四方,知识阶级的青年大众已经完全接受,以后必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革命文学的全运动上,文艺理论的建设与作品行动只是形式上的区别。指导理论的发扬,由指导理论的灯光去照彻有产者家犬的衣裳,点破一切新旧文艺的本性-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今后将更努力于这方面;正确的理论决不是空虚的,它是轰破敌军的强有力的炮火”。)。还有一篇《留声机器的回音》指出,对于“唯心的偏重主观的个人主义者”来说,他们应该克服自己已有的个人主义,来参加集体的社会运动。“就是要叫他们当一个留声机器--这就是第一,要你发出那种声音(获得无产阶级意识),第二,要你无我(克服自己有产者或者小有产者意识),第三,要你能活动(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载《文化批判》,1928(3))这些道理说白了,也就是取消个人主义,不要表现自我,要被动地、无保留地充当集体意识的传声筒。
较之周作人当年“人的文学”的提倡,这是一个明显的倒退。革命把原先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启蒙意识都消解了。这时,明确地对文学家提出要求,即为革命而文学,而不是为文学而革命,落脚点是革命。至于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应该是由“艺术的武器”改变到“武器的艺术”,出发点是武器。(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1928(2)。)文学和艺术到了这时,自然地变成了革命和武器了。由于上述那些理论的推进,新文学在经历了初期的有些庞杂也有些散漫的发展之后,就被迅速地吸引进了革命的隧道。强调社会性和集体性的结果,使文学的“个人主义”受到沉重的打击。那些指向农工运动和底层生活的革命作品,使恋爱也染上革命的色彩。这些无一例外的严肃而沉重的作品,一时间站在了时代主流的位置。他们从批判文学的趣味中心转而批判文学的个人主义。激烈地反对文学的个人主义的结果,伤及了文学的心脏--文学的所有悟性和灵感的核心。这就给此后漫长岁月中的文学悲剧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以20世纪40年代初期那个讲话为标志,直至40年代末的《斥反动文艺》(郭沫若作,载《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香港,1948年3月出版。)的发表,事情可谓愈演愈烈。邵荃麟那时说:“在今天,作为一个进步知识分子来说,只有在同广大群众结合中,进行其自身意识改造,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健康的感性生活,否则便可能走向到个人主义文艺的旧路上去。我们以为今天文艺思想上的混乱状态,主要即是由于个人主义意识和思想代替了群众的意识和集体主义的思想。”(见《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发表时署名为“本刊同人-荃麟执笔”。)
一百年来,我们的新文学就这样以不堪重负的姿态,行进在发展创造的长途上。文艺不仅是疗救社会病苦的药物,后来更成为政治的代言,甚而本身也成为政治。文艺排斥和拒绝轻松和闲暇的结果,使那些不能占据主流位置的写作者受到质疑和打击。他们是主流以外的人,他们的工作长期得不到公平客观的承认。他们被称做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作家。他们置身于支流、边缘甚或是逆流的受轻视和受排斥的地位。在上述那篇《斥反动文艺》的文章中,作者说:“我今天要号召天真的无色的作者和这些人绝缘,不和他们合作,并劝朋友不合作。人们要袖手旁观,就请站远一点,或站在隐蔽的地方。”这种局面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大约占了一个世纪的一半。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文学一直如此沉重,这说明中国新文学的生存环境并不正常。
新文学在行进中,它却又是在不断地试验中。从它酝酿和诞生的时候起,它就一直在尝试着适应中国这个充满危机也充满变数的社会政治现实。它是文学,却又不单纯是文学。尽管在漫长的时间内,有不少的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都在提倡一种“纯”的文学,但文学在中国就从来也没有“纯”过。在中国这个现实里,文学似乎总是天生地和它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兴亡,甚至和政治沉浮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最初的“为人生”到“为大众”,再从“为工农兵”、“为社会”、“为绝大多数”到“为政治”……开始是自然而然的推进,后来就有点着了魔似的“穿着红舞鞋”不停地跳着,再也停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