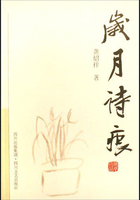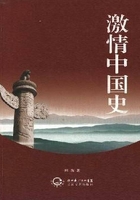因上述现象责怪任何人均无意义。它是历史的阻隔造成的文学畸形。新时期以后十多年来两岸作家、学者以有限的方式进行交流的结果,民间形态冲决时空和意识的樊篱终于有了收效:理解正在纠正误差,友爱正在涤荡偏见,心灵的彼此倾听消弭着文学的歧见。文学先于其他部门取得了从零开始的共识和整合。
随两岸来往最先出现的宗族血亲的寻根潮流而来的,是未曾明指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文学、文化的寻根潮流。台港作家和诗人只要是洞悉中国文学历史渊源和发展情势的,无不乐于承认该地区文学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母体的血缘关系。那里的文学同仁都确认该地区的新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支流脉,它的火种同样是“五四”先驱者所点燃。
也许因为文学总是与心灵的沟通和谅解有关,文学最先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梦。虽然还是梦,但这梦是完整的。文学的交往在这一时期形成的那种超脱的、以信任和友善为基础的格局,给文学以外的那些领域提供了一种恒久而积极的范式。完整的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实现,也许需要时间和耐心,但文学显然不愿无限拖延它的期待。
20世纪90年代带给我们的如下信息是确定无误的:文学中国的整合已在悄悄形成。这种弥合历史裂痕的工作,带给当今中国的显然不限于文学自身的意义。文学以外的那些领域,无疑将从中汲取非常积极的并且是建设性的启示。当被分裂开来的两个部分,各自曾呈现出彼此的单调与贫乏时,二者因整合或至少互补而构成无可置疑的丰富。这个简单的一加一的故事,再一次成为文学中国的现实描写。
随着20世纪40年代的结束,中国文学以台湾海峡这一水域为界线,展开了色调迥异的历史画幅。一边是叱咤风云的胜利者的欢愉,一边则是失去家园的乱世儿女的悲凉;一边展现奠基创业的宏大气势,一边则浸漫着对于往昔的追怀以及无根的飘零感。内陆的雄浑粗犷,与海洋性的灵动浩渺以及南方温暖岛屿的明丽缠绵,这种反差极大的风格的各自展现本来就很动人;对它们进行对比、综合的整体观照,将带给文学以益处则是毫无疑问的。
长久的隔离造成观念和价值上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有时令人焦躁,却因其本身的丰富和复杂,也带来思维的丰裕。近期展现的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差异便是一例,两岸学者的基本态度几乎是反向的,大陆趋于批判而台湾趋于保护。这种反差促使我们积极了解对方,从文化入手而延伸到社会的多层面,最终造成的是对于事实认知的深刻化。
文学将从这种巨大反差的识别和综合中受益。对大陆的文学运动而言,它以往的积弊是由于对创新的畏惧造成的创造力的萎缩,趋同求稳的习性使浅薄的仿效成为风尚。为此,异向的参照和多方的补益不啻是一剂清醒的药石。既然我们曾经为改造、更新文学而向遥远的异方求教,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自己国土上的不同视点和不同价值观念的文学整合。
十年的辛苦经营使我们从交流中先于其他领域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文学中国的概念。我们越过长期的阻隔不仅了解并理解了对方,而且得到一个整体性的文学历史的观照。我们从文学中国的初步整合中发现了彼此的矛盾、差异以及联系,从而促进了彼此的吸收、扬弃和自我充实。这诚然是一种胜利。但随着胜利而来的却是关于文学自身更为长远、也更为艰巨的使命,这就是庄严的下一步:中国文学的整合。
文学中国已经以它的完整形态展现于我们的视野。它将悄悄地、也是不可逆转地从容消解文化上、心理上、精神上的彼此排斥而促成新的融汇。对于当代的中国作家和学者来说,我们缺少的是一个可以包容全部中国文学丰富性的描写角度和叙述体系。我们需要把海峡两岸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多彩文学加以比较综合的广阔视野。当文学中国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时候,随之要求把这种成果转换为完整的中国文学的展示。
具体一些说,我们现今的期待是一种既不是割裂的,也不是一加一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选本体系的实现。这种完整的中国文学的体式不是浅层次的相加和表面化的堆积,而是消化之后把两岸文学加以溶解、调适和重新组织的文学视野、文学体系。我们期待着分裂和对立的结束。我们希望中国文学从今往后是一个不再分割的和高度融合的整体,而排斥被肢解的、破碎的和拼凑的展示。这种整体的中国文学研究,是我们未完成的中国文学梦。
四、参与世界的中国文学
(一)
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关系密切的时代,往往是中国社会处于大转折的时代。这时的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而此种活力恰恰体现在中国能够对自身的处境有清醒的估计上。它从麻木中警觉。它感到了传统文化规范造成的窒息,以及处于这种窒息之中与世隔绝的痛苦。
觉醒的中国魂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先进之士于是视文学为疗救社会病痛--这种病痛首先是国民心灵的沦落--的药石。这时他们便觉察到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方式与现代世界的不相适应,于是“别求新声于异邦”,萌生了向世界文学借助力量的愿望。我们把这种行动称之为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中国借助世界现代火种,烛照中国自远古迄于今的封建长夜之暗影,并点燃国民向着人类现代文明行进的热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高度评价了在大转折关头的中国与世界文学的交流。
中国充当世界弃儿的时间太久了。也许是自弃,也许是被弃,都给中国带来久远的巨大的痛苦。20世纪以来,中国有过两次返回世界的机会。第一次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这一次最伟大的收获,便是中国以西方现代文学为榜样创造了划时代的中国新文学。当时最有影响的一批文学家,无一不受到外国文学的滋养。这个时代所造就的业绩,由于中国社会长达半个世纪的特殊环境和中国固有文化的潜在威慑而逐渐减弱它的辉煌。
这诚如梁启超在20世纪第一年所揭示的中国的弊病:中国“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五四”新文学运动创立的中国与世界文学的联姻,在以后发展中遂告逐渐解体。在一个长时期内,中国曾因标榜自己的唯一革命性而对一切外域文化予以排斥,从而造成了自绝于世的文化禁锢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自足文化心态的恶性延伸。中国于是再度与世隔绝。
(二)
中国文学极端自我禁锢的一个结果,是出人意料地造成了它重返世界的契机。至少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专制与文化封闭,造成了实际的文化荒漠,同时也培养了对于荒漠的反抗愿望。人们憎恨并批判这种禁锢。由于总的开放方针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促使,中国文学终于再度向世界探出头去。
文学的重建工作,在文学受到摧毁的基础上进行。长久的饥饿使人们饥不择食。一批旧版的世界古典名着的重印,给人们以初步的满足。事情开了头便难以收住,人们于是开始新的寻找。凡是可以找到的,都是对克服精神饥渴有益的。这时期人们阅读之广泛和不加选择可以称之为一种新的热病。这种不加选择是对过去的无可选择的逆反。
这情况其实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期即已开始。一方面是破坏书籍的高潮,一方面又是地下读书(主要是西方书)运动的高潮。许多红卫兵的查抄书刊得到广泛传阅早已不是秘密。当时海外出版的《华侨日报》披露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一批在60年代中期为中国作家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以批判为目的内部发行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阅读的西方和苏联的现代哲学、文学着作,在这批青年手中传阅着,形成了一个半狂热的秘密读书运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样几本书:爱伦堡(苏)的《人·岁月·生活》、塞林格(美)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克鲁亚克(美)的《在路上》、萨特(法)的《辩证理性批判》、罗素(英)的《西方哲学史》、怀特(美)的《分析的时代》、德热拉斯(南斯拉夫)的《新阶段》和《译文》上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作。”(贝岭:《作为运动的中国新诗潮》,载纽约《华侨日报》,1986-12-25。)
外国文学以雷鸣闪电般袭击、征服着中国广泛的文学饥饿。在一批没有机会受到文化滋润的青年作家中,读书的驳杂及其导致的影响的驳杂是一个特殊又普遍的现象。顾城自述:“从欧·亨利到杰克·伦敦;到雨果到罗曼·罗兰、泰戈尔……当我再看《离骚》和《草叶集》时,我震惊了。”(顾城:《朦胧诗问答》,载《文学报》,19830324。)后来,“许多荒凉的现代诗星,突然发出了炫目的光芒--波德莱尔、洛尔迦、阿尔贝蒂、聂鲁达、叶赛宁、埃利蒂斯……”(顾城:《剪接的自传》,见《顾城文选》(卷一),19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舒婷自述:“外面,我的戴着袖章的红卫兵战友正强攻物理楼,而我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我完全沉浸在文学作品所展开的另一个世界里,巴尔扎克的,托尔斯泰的,马克·吐温的。”后来,(她也有这样的“后来”)一位老诗人“几乎是强迫我读了聂鲁达、波德莱尔的诗,同时,又介绍了当代有代表性的译诗。从我保留下来的信件中,到处都可以找到他写的或抄的大段大段的诗评和议论”。(舒婷:《生活、书籍与诗》,见《沉沦的圣殿》,298页,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得到启示,当前这一中外文化交流阶段与五四时期有一些显着的不同,五四时期的文学先驱,对于外国文学的借鉴,大体具有定向选择的性质并因此影响了他们的创作道路与艺术风格(只能是“大体”),如鲁迅之于果戈理、郭沫若之于惠特曼、冰心之于泰戈尔、丰子恺之于夏目漱石、徐志摩之于英国浪漫派、戴望舒之于法国象征主义。而此一时期的作家则大体不具备上述性质。这种不具备主观心境与客观条件的不加选择性,体现了一个大空白之后一种匆忙“充填”的特征。由于原有的正常秩序的破坏,无秩序便具备了合理性。中国几代作家经历了政治文化的大动荡之后,可能采取的唯有此种方式。
(三)
如同“五四”时代的文学运动受制约于那个时代一样,现阶段的文学运动亦受制约于这个时代。从表层意义上看,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引进”,其视角有了一个大的转移,即“五四”前后的选择,多半着眼于政治历史,而当今的选择则偏重于文化审美。经过长久动荡之后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使较之那时更具有超功利的选择自由。
人性从被毁灭到再度张扬,人的价值从被湮没到重新确认,较大限度地支持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主体意识。人们以此为前提进行中外文化间交流并进行选择,个人因素重于社会因素乃是必然。我们正是从这种文学交往的无拘束中,看到了自由时代的属性。
一个封闭的社会不可能有如此开放的文化心态,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自由的背后,是一种对于变态的文学时代的反抗。那种依据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的要求而曾受到社会集团意识支配的文学选择已退居次席,更为突出的是张扬个性乃至服从于独特审美需求而进行的汲取与借鉴。但这些特性并不说明文学借鉴与文化交流不具有实际的社会性考虑,更不说明文学的进步与时代社会进步未保持联系,恰恰相反,我们从当时的“淡漠”中看到了受热情驱使的沉默的反抗。
中国文学依然反映了这个古老民族的深重悲哀,只是它以更为成熟的姿态来对待这种别求新声的异域“盗火”。它在更深的层面下寄托了民族的忧患。它于表面的“无选择”中,体现了更为焦灼的、当然有时也更为洒脱的选择。这种选择听凭创作主体的内心驱使。这种内心驱使依然有着遥远的时代的召唤。
现阶段精力旺盛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位会明确地说出自己师承于某一外国作家,或奉某一作家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风格为自己的楷模。我们看不到这种明确的表白或回答。我们只看到那些作家的凌乱而驳杂的阅读书目,以及带有极大随意性的偶然的描述。有一篇报道说邓刚“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有他手头上正在读的那本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为证,他正在研究‘黑色幽默’派的代表作”。又有一篇谈莫言的创作的文章,指出他的《透明的红萝卜》只是孩童感觉的实录以及通过回忆的外化,指出这一艺术效果受一些外国文学的影响,如《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等。这里引用的都是一些推测性的判断,是一种模糊的描写。
但中国作家已经不约而同地醒悟到,要想表达现代生活以及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就必须积极变革自己的艺术。这种变革显然以寻求与过去迥异的艺术形式为目标。最早开始这种探索的是引起各方震动的“朦胧诗”运动。一批激进的青年诗人终于选择了具有异端性质的西方模式,向着依然是最自信同时又体现为最僵硬的传统模式挑战。
这种寻求充满了艰辛。因为它很难被感到完全陌生的欣赏者和批评家所接受,它的不合常规的艺术思维和艺术方式甚至对作家本身都存在困难。但立志要改变以往僵硬模式的中国作家显然已把付出代价的决心付诸实施。
(四)
很难对中国当前借鉴和参照世界文学的状况作出准确的描述。它的难以描述是与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错综复杂及其瞬息万变相联系的。现阶段中国文学已实现了由单一格局向多元格局的转换,且后者业已显示出稳定状态。中国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与接受也体现了同样的趋势,即由某一种或某几种现实功效的考虑而向多向寻求的转换。
对当时全面展开世界性文学交流的情景作出精确的描写,特别是判断西方文学的何种思潮或主义对中国文学有决定性的或主流的影响,显然十分困难。当时文学创作所接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无主流的。莫言自言他的《白狗秋千架》得力于日本新感觉派大师川端康成。有人从高行健的《车站》看到贝克特《等待戈多》的影响。有人撰专文谈论韩少功近作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关系。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谭甫成的《高原》或是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中孩子的形象联想到他们与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中的小孩的联系,他们同样是忍受了痛苦和悲哀而追求理解与自由的精灵。这些中国作品与外国作品的联系与接受影响的关系是明显的。失去主流的文学时代当然也失去了借鉴与引进的主流现象,要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的总流向作出判断几乎不可能,一切都是自行其是的,一切又都是“无秩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