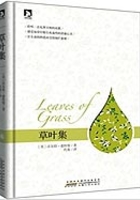这种艺术本质属性在文学中的苏醒,为新时期文学作出了质的规定性:新时期文学的一切变革和探索都涉及了文学自身,而与非文学相剥离。新时期之所以“新”即在于此。当然,这一时期还有若干重要的特征赋予中国当代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点:首先是开放性。前此的文学处于严重的自我禁锢状态中,文学受到褊狭的自以为是的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的制约,以过敏性的排他反应对待一切自认为“不纯”的文学,步步设防、处处设防,以致最后孤立了自己。再就是探索性。一旦意识形态的羁绊得到解除,文学自身规律启动的结果,便是奔涌而出的创作激情。原有的戒律取消了,文学自然地要寻求多种的可能性。整个的形势鼓励着文学冲出传统规范的实验和探索。开放性和探索性是条件,它们造出的结果是多元性。塑造单一的甚至唯一的文学,是一种文学的自杀行为,而数十年来却对此一往情深。封闭的文学设计出名目各异而实质不变的“最好的”方法、风格或标准,把本性属于各式各样的文学改造为统一的、在“样板”规范下的文学。说是百花齐放,实是一招一式都要受到模式的统治。新时期完全改变这种单一性,而以多元性来代替。多元局面的实质在于承认文学的民主化进程,在于承认文学的非主流性。统一规范的瓦解当然造成了文学的失控,但是文学也就是在这样的失控中获得新的生机。
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社会的开放相联系的文学新时期,在独立形态的运行中到达20世纪80年代的终点。一切新的都将变成旧的,何况文学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它的完整形态。文学的发展也如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在不断的推进中新陈代谢。新时期文学不能永远地新下去,终究要有更新的形态出现。但文学又有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点,这就是尽管它服从于新旧替代的总规律,但一切“旧”的并不会因此而消失,消失的只是不具价值的东西。然而“旧”的并非不具价值,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不论新旧都将在文学王国中获得永生。
四、后新时期文学:商业社会的文学形态
后新时期这一概念与社会发展阶段也与意识形态无直接关系,它仅仅属于文学,或者宽泛一些说,涉及艺术或文化。后新时期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但又不同于它的前身。就外在条件而言,它有从属于历史时代与社会的某些决定性因素;就文学自身的条件而言,经历了十余年的充分的、近于完整阶段的发展,为它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提供了充分、令人信服的条件。
中国社会已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政治型转向经济型,社会转轨的阶段基本完成,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明确地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80年代的结束,选择了一个让人全面震撼的时刻,它把当今时代的历史记忆导向了深刻。一方面,它无情地让人面对这个传统社会的深重悲剧性;另一方面,它诱逼更多的人逃避这种遭遇和命运。一百年的历史以其惊人的相似促使一些人惊醒,也促使更多的人沉沦和忘却。
中国以庄严悲壮的心情面对过去的20世纪。从这20世纪回望上19世纪,中国人拥有一个沉重的记忆。世纪末在其他国家和民族那里也许只是时序的更迭,但在中国却易于激起特殊的悲凉情怀。一百多年前那些触目惊心的大事件,如甲午海战、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都会引发某种怅惘和失落感。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距离20世纪的结束越来越近时,一百年的追求和失败,以及对这个世纪苦难的反思,构成中国人特有的世纪末情结。这种世纪末情结是社会和文化的,却更是直接对后新时期产生重大影响的。不论是激情还是隐逸,不论是调侃还是闲适,文学上的种种表现,都可以从这种世纪末的处境中得到解释。
再就是商品社会的形成,带来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因素。这些因素大大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性质。最封闭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今也开始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科技产业。电脑的普及、信息的革命、消费文化的膨胀,给这个古老社会以强烈的冲击。
一方面是西方超前意识的移入,一方面是中国固有积习的充分展现,人口的爆炸,生态的危机,资源的匮乏与毁灭,城市和乡村的污染,还有国营企业的病入膏肓,这一切,又构成了复杂而矛盾的“国情综合”。至于文化上更表现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汇的种种冲突。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长驱直入,吸引相当多的青年的兴趣;而传统文化在主流意识支配下,以弘扬为号召,使一切以往受到革命压抑的观念形态得到空前的弘扬。谈国粹不仅不可耻,而且洋洋自得,国学热迷浸于那些最具革命性的学说的讲坛,至于尊孔尊儒,更是一路绿灯。这一切的兴旺发达,堪与可口可乐、麦当劳、卡拉OK的狂热相媲美。
五、世纪末情绪与“90年代文学”
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是说不清楚的。这是一个不明朗和不定型的社会,良莠不分,鱼龙混杂,华洋交错,非古非今,不中不西。但有一点却是确定的--它已告别了中世纪式的封闭和禁锢。但是新时期那种意识形态的理想和激情已经黯然,不断透漏进来的阳光,叙说着外边世界的风景和节拍。告别了暗夜的社会于是充满了想象,而这些想象又往往由于现实的积重而化为泡影,混乱无序也许就是进入商品社会的常态。原先的有序状态本来不属于这一个历史时期,计划经济的解体就是一种暗示。
至于文学自身,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已经显露出诸多有异于前的新的气象:后朦胧诗的出现、先锋小说的实践、第五代导演、新生代艺术、新潮绘画等前卫文艺实践已相当广泛。80年代最后一年的事件,成为一个启爆的因素促成了文学新时代的转型。其实,这种转型8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孕育之中,是以累积式的渐变来实现这种前后交替的。
20世纪80年代结束以后,文学研究界已经开始注意新的文学转型的现象。当时的思考是在“进入90年代文学”这一命题下进行的。1991年第5期《当代作家评论》发表“文学走向90年代”笔谈,参加笔谈的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的及青年学者,其中有谢冕的《停止游戏与再度漂流》、孟繁华的《平民文学的节日》、张颐武的《写作之梦:汉语文学的未来》、李书磊的《“走向世界”之巅》、张志忠的《批评的陷落》。这是80年代社会震撼后批评界第一次面对着新的文学世界的发言,可以把这次笔谈看做是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思考的先声和准备。
谢冕提出:“无论是从正面或是负面的价值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文学阶段的‘新时期文学’已宣告终结”,“十年前开始的文学急流已经消退,随之而来的是冷静的回望与总结”。谢冕对当时文学的某些迹象表示了不安:“当生活变得不那么轻松的时候,当文学的环境也并不那么良好的时候,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仍然理直气壮把对象当做手中的玩物,是否有点近于残忍!于是,我们不能不从内心发出吁求:停止游戏!”谢冕在1990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年会上,在高度评价新时期文学的同时,就在发言中正式指出这一时期“已画了句号”。至于“新时期文学”以后的文学形态及其命名,当时的讨论还并不明晰。值得注意的是张颐武在他的文章中已经运用“后新时期”的概念,他说:“进入90年代,作为第三世界文化中具有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最丰富的文本存留的汉语文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型。‘新时期’文化向‘后新时期’文化的转移过程已经清晰地显示了出来。驳杂的、零散的、扑朔迷离而瞬息万变的80年代已经逝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张颐武这段话已经包含了对于新的文学时期的预言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