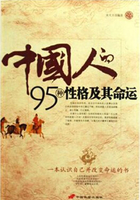我的手一提起笔来就颤抖,心也窝得难受,几次动笔,都半途而止。我明白我不能很有条理地将这篇悼亡文章写出来了。于是,就涂些阿拉伯字母,断开来写。
我和这位亡人在感情上是兄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们之间的感情像最亲密的兄弟那样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同样的两个孤独的旅行者遇到了一起,我们进行着关于人生和命运问题的谈话,我们都在那一刻体验到生命的幸福。本该,我们都期待着,又一个推心置腹的时期的到来,但是,这种可能已经没有了。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人类中的一分子消失了,这同时是整个人类的损失,丧钟在为他而鸣的同时,也就是为我而鸣,为我们大家而鸣。我在接到噩耗的那一刻,立刻被一种强大的打击力量击倒了,胸膛里填满了悲怆。我用“物失其类,不胜悲戚”这句话作为我的唁文,发往省作协所在地建国路71号。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除了生活中必须说的以外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感到痛苦。他的年龄和他的事业正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不该就这么撒手长去的。路遥的猝死给我以强烈的震撼。我痛切地意识到命运之神的冷酷和残酷,意识到生命力的如此虚弱和脆弱,意识到一个活生的人在我们说话的片刻就有理由成为一撮烟灰,意识到墓碑上一个时间概念和一个时期概念之间那一道横杠,是可以随随便便就划上去的。尽管前人早就告诉我们,既然你活着,你就永远处在死亡的威胁中,而最终的胜利者是死亡而不是你,这是人类的悲剧中有力反抗但无力解决的悲剧,根本意义上的悲剧。但是,我的朋友路遥,他是不是死得过早了点,过于急促了点。记得我小的时候,世界上流行脑膜炎,不时有一个街坊邻居的孩子死去,那时,我整日惶惑,羡慕地望着身边那些长寿者和寿终正寝者,我想他们能活到那一把年龄,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业绩,本身就令人眼馋。这一段日子,当年的那种对命运的不信任感,感觉到自己像一棵风中小草一样的孤独无靠的心理,又重新控制了我。我常想自杀,以此来反抗死亡,改变和蔑视死亡。
在这种善良的感情下,路遥时常陷入回忆的是他的初恋。我想那大概是个扎着两根羊角小辫,穿着一件红卫兵衣服,跳跳蹦蹦地爱演文艺节目的北京插队知青。《人生》完成后,他从甘泉回到了延安。我不知从哪里为他弄来了两盒中华烟,接着又弄来了两条。他贪婪地抽起来。那天晚上,延安城铺满了月光。我们两个像梦游者一样,在大街上反复来反复去地走到半夜。“中国文学界就要发生一件大事!”他说,他指的是那一包《人生》手稿。突然,他谈到了他的初恋。谈到在一个多雪的冬天,文艺队排练完节目后,他怎么陪着她回她的小屋。“踏着吱吱呀呀的积雪,我的手不经意地碰了一下她的手,我有些胆怯,怕她责怪我,谁知,她反而用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路遥说。他还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后,在北京,他刚刚回到下榻的房间,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你是谁?你没有事的话,我就挂断电话了!”这时,命运的声音从电话线那头传过来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一位熟悉的老朋友!”说话的人穿着一件红风衣,在马路对面的电话厅等他。他扔下电话,疯了一样跑下楼,横穿马路而过。“我奇怪汽车为什么没有压着我!”路遥说。在他们短暂的接触中,这位女士说,她曾经来过西安,曾经围绕着那座住宅楼盘桓了很久,但是没有勇气去问问他住几号,没有勇气去叩响那个门扉。“哪家阳台上没有花草,哪家就是我。”“她后来嫁给了一个海军军官!”路遥对我说。
我不知道路遥所说的这个故事中,真实的成分有多大,尤其是后来的相遇部分。但是,他确实有过这么一次初恋,而且,他怀着一种可怕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恋情,恋着她。
1983年期间,他回到了延安。那是一个秋末冬初的曰子,大地一片肃杀,一见到我,他就抓住我的手,他面色铁青,他说,这些天来,他脑子里只回旋着一句话,就是“路遥啊,你的苦难是多么深重呀!”他在延安呆了三天,为了安慰他,我在宾馆里陪他住了三天。我说:“作家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充其量是回到延安来吧。我永远是你的朋友。”三天之后,那个有霜的早晨,我又用自行车将他带到了东关车站,送上长途班车。一些天后,我为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先发表在《星星》,后来收入我的诗集。
你有一位朋友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有时心中会生出莫名的烦忧。
你想找路人一倾衷肠,可是,大家都在忙忙碌碌。
啤唤我,啤唤我吧!我会走来,像一只小鸟落在你的肩头,我的充满友情的诗歌,会化作小鸟的鸣歌。
自然,我们的生活无限美好,歌声总是多于忧愁。
但是,谁能保证说,我们没有被命运嘲弄的时候。
有一天早晨一觉醒来,生活突然出现了怪诞的节奏,你的妻子跟着别人走了,一瞬间你是多么孤独!
关于工作,关于住房,关于煤气罐,关于那不唤自来的病疚,以及一切不惬意的事情,包括领导对你的毫无理由的掣肘。
有时候你会拔下一根白发,哀叹生命可悲的短促;有时候你会望着天边大雁,渴望它把你一起带走。
相信吧,我会理解你的,我是你的值得信赖的朋友,不论你陷进痛苦的深渊,或者是误入荒丘。
也许你只剩下一个朋友了,那就是我,我会紧紧握着你的手。
1我的诗歌就是我的翅膀,我会彻日彻夜地在你身边漫游。
一旦你呼唤我的时候,我就踏入你那神秘的国度。
绵绵的人类之爱呀,就是维系我们的纽带,真诚的朋友之间,别担心,谁会欠下谁的人情债。
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有时心中会生出莫名的烦忧,相信吧,我会走来,像一只小鸟落在你的肩头。
如今在读这一首诗的时候,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因为路遥的死,路遥的不完美的婚姻,我在写这首诗时都预感到了。
说起诗歌来,附带说一句。《人生》发表在杂志上后,路遥将杂志拿给我,他有些不自然地说,里面用了你的《我愿你是一只生着翅膀的大雁》的诗,你不会介意吧!我说,我不会介意的,我感到荣幸。“不过,”路遥接着机智地说,“是书中一个叫黄亚萍的人物,偶尔读到你的诗,抄到笔记本上,送给高加林的!你去追究她吧!”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读者读到这里,也许会认为我们是平等的。我想说读者只判断对了一半。是的,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尤其是对我来说,我的娘肚子里带来的那种独立不羁的性格,不愿意让任何东西来制约我。但是,在文学这个技术性问题上,我一直视他为导师,他的“对自己要残酷”的名言,一直成为我鞭策自己的一条警鞭,在陕北这块土地上,他永远是第一小提琴手。有几次回延安,他用嘲笑的口吻对我们这一群说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呢?为一些不值得的事情苦恼和愤愤不平。你们不如抛开这些,去写自己的作品,一天写两千字,一个月就是一个中篇了,再用一个月时间修改和抄出来。发过几个中篇后,谁也就奈何你们不得了。”他这些话总给我以教益。
路遥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也许,他的本身,比他小说中的任何人物都更精彩、更复杂、更具有文学的独特性。可惜,他英年早逝,没有可能再去表现这一切了。这是整个人类的损失!人类整体利益的损失!我曾经多次给路遥说过,我说,如果让你经受一次大的打击,脱离现在的生活轨道,而走向内心自省,一定会有比《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更为精彩的大作品出现的。这次,命运为他提供的打击是疾病。可惜,他没有能战胜它。且让我在无限的惋惜哀痛之余诅咒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