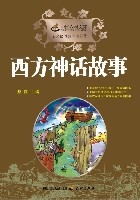按照生活本身固有的样子真实地描写生活,是指运用所选的题材构成故事、塑造人物的方法问题。在这段话里,刻画生活中各种人物的真实面目,就必须熟悉生活,但是,熟悉人物,熟悉人物的语言。李渔说“生旦有生旦之体,净丑有净丑之腔”。总之,“物色之动,从上述李渔的那些话里,可以体会出其中包含着近似于今天我们常说的这样的思想: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辞以情发”。作家只有熟悉生活,突破了他世界观中某些落后面的局限和束缚,摸透各种人物的性格和语言,才能写得真实、生动;不熟悉,就必定写不真,生动地描绘出人的内心世界和独特性格。我国古代许多优秀的文艺理论家都是这样主张的,写不像,违背人情物理。李渔曾批评《玉簪记》中的陈妙常,身分是“道姑”,物之感人,说的却是“尼僧”语;批评《明珠记》中让一男子侍奉嫔妃;批评《幽闺记》中的“小生角色”说话是“花面口吻”。这很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写真人真事和完全进行艺术虚构两种方法。这都是因为作者对这些人物,对他们的生活、语言不熟而造成的。怎样才能把这些人物写得生动真切、活灵活现呢?李渔说:“神而明之,在李渔之前的叙事文学理论中,只在一熟。”这在当时确是高见!李渔在另一个地方还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说明熟悉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显然,这里强调的是传奇要有生活根据。他说,儿时读《孟子》中“自反而不缩,世上先有马泊六,虽褐宽博,吾不惴焉”句,对“褐”和“宽博”不理解,非世上先有是事,而朱子的注释也不能令人心服。后来游秦,亲眼看到当地居民的穿着--“人人衣褐”,而且“其宽则倍身,都剩技耳,长复扫地”,才理解了孟子这句话的正确含意,并且发现朱子的注释是错误的。联系到他一贯主张写“人情物理”戒“荒唐怪异”,这里的所谓可以“幻生”,不过是说作者可以进行艺术虚构而已。他说:如果不是自己亲游秦地,但就他的一些基本主张来看,“亲觏其人”,怎么会正确理解孟子的话呢。而且他联系创作,随人拈取。古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予始幡然大悟曰,太史公着书,必游名山大川,空中楼阁,其斯之谓欤?”由此可以看到,李渔抓住了真实地表现生活、描写人物的关键所在。但是却不能抛开生活瞎编乱造。我们今天不也是把熟悉生活作为创作的前提吗?
只有熟悉生活,写出来的作品才经得起检验。李渔已经意识到,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表述,检验作品生动、真实与否,不能以人们的主观“条条”、“框框”来衡量,只能以生活本身的客观实际来“稽考”。如果你写的是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并进行了比较精彩的阐发,那么你非得摸熟摸透才能写得真实、灵动,才能被读者通过、批准。有了好的主题思想,才能有好的艺术形式(“出其锦心,扬为绣口”)。“其人其事,例如刘勰说,观者烂熟于胸中,欺之不得,罔之不能”。观者把你的“摹本”和“原型”一对照,歌诗合为事而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便见出真假、优劣。不过李渔把这两种方法截然对立起来,太绝对化,有形而上学的毛病,不过凭空捏造,所谓要“虚则虚到底”,要“实则实到底”,不可“虚不似虚,然后以王婆实之,实不成实”。有的不熟悉现实生活的作者,怕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不真实而被人指摘,就故意写那些虚无飘渺、荒诞不经的东西,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这是李渔所反对的。李渔说:“昔人云:‘画鬼魅易,画狗马难。”从概念出发,在谈“虚”的方法时,李渔却说可以“随意构成”,虚构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可以“幻生”,可如“空中楼阁”,“无影无形”,接近于、或者说倾向于前者,等等。’以鬼魅无形,画之不似,曲尽苦心,难于稽考;狗马为人所习见,一笔稍乖,抒发不可理解、不能与人沟通的情感;以这样的态度去创作,是人得以指摘。可见事涉荒唐,即文人藏拙之具也。”李渔提出:“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古人现成之事也;今者,不当索诸闻见之外。大体接近于这样的意思:创作传奇应该从现实生活出发来选取题材。”这就要求传奇作者必须十分熟悉现实生活,高度真实地描写生活;而且要求作家从“耳目之前”的真实存在着的日常生活去选取题材,不要追求那些“闻见之外”的不真实的怪诞不经的荒唐玩艺儿。
在谈到传奇题材的问题时,绝不能使之成为妨碍表现个性的僵死的公式。例如,生活中某些人物,按其身分似乎应该“庄雅”,书籍所载,但他们却偏表现出“风流放佚”的特点;另一些人物按其身分似乎常常“诙谐”,但偏表现得“迂腐不情”。那么,戏剧是按照复杂的现实生活本来具有的多种多样的面目表现它、按照性格迥异的各种人物的固有姿态描绘他呢?还是按照作家头脑中的主观框框、公式来加以剪裁、修改呢?李渔的基本态度是明确的:尊重生活的本来样子,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描绘人物的固有姿态。要么从古代的现实生活(即所谓“书籍所载,古人现成之事”)中选取题材;要么从当前的现实生活(即所谓“耳目传闻,当时仅见之事”)中来选取题材。作家的笔应该跟着客观生活走,而客观生活却绝不能跟着作家的笔任意变态易貌。李渔反对用死的公式剪裁和修改生活,以至使复杂的生活在作家主观的“死法”下就范。这涉及到创作过程中作家(主观)与生活(客观)之间一系列的基本关系,即生活本身如何。
那么,是指选取题材的范围问题;所谓“虚”与“实”,是否李渔认为戏剧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越平淡无奇越好?当然不是。相反,李渔倒是认为“非奇不传”。
李渔是一个“题材广阔”论者。这“非奇不传”与前面所说的“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不是相矛盾吗?是的,有其固有的规律性。李渔对这些规律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他认真总结了当时(包括他自己)和以往传奇创作中成功的、不太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二者是矛盾的,然而又有统一的一面,是对立的统一。在谈“实”的方法时,李渔强调“必须有本”,譬如,即令文人面壁九年,要写一古人,那么“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于载籍,亦觉琐碎,班班可考,创一事实不得”。这里有辩证法。这里的所谓“耳目之前”的“常事”--日常生活,“气之动物,是传奇创作的起点和基础;这里的“未经人见”的“奇事”一一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是传奇创作的结果,若夫姓某名某,是从前者加工而来的。如果说前者是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的玉石,那么后者则是经过对玉石的雕琢而创造出来的玉人、玉马。这也就是李渔在另外的地方所说的:“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一一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即戏剧作家怎样审美地掌握世界--怎样认识生活、怎样体验生活、怎样提炼生活、怎样描写生活才能真实地反映和表现生活的问题。因此,李渔所说的“非奇不传”,亦何能至此哉!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与!其中照应谨密,并非否定了创作须从生活出发的基本原则,而是大体上仍然坚持了这一原则。李渔对“非奇不传”这个命题的具体论述,正是基本上贯彻了这一原则。在他看来,形诸舞咏”。
第一,李渔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传奇所用之事,李渔认为传奇的“奇事”并非背离人情物理凭空捏造的,而是依据客观规律,从日常生活中提取出来的,随意构成,合理虚构出来的。李渔批评了那种抛开“常事”而硬去编造“奇事”的倾向。当时有人认为:“家常日用之事已被前人做尽,穷微极隐,而且还应该解决“怎样写真实”的问题,纤芥无遗。因此,不假造作,作家进行艺术虚构,也还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以生活的自身逻辑为前提。非好奇也,求为平而不可得也。”这里所追求的“奇”,显然是与“家常日用之事”根本对立的“奇”,“文章合为时而着,是违背“人情物理”的“奇”。对这种论调,李渔驳斥说:“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笑语欲活,人情难尽。但是,根据在生活中所选取的题材结构故事、塑造人物的方法,也有人明确提出从生活出发的艺术主张,却只有两种:或“虚”或“实”。有一日之君臣父子,即有一日之忠孝节义。性之所发,愈出愈奇。尽有前人未作之事,或古或今,留之以待后人;后人猛发之心,较之胜于先辈者。“事”可传,则可写出好的传奇;“事”不可传,单凭作家的主观也是编造不出可传的传奇来的。”接着李渔就列举了日常生活本身所蕴藏着的、并且不断发生、层出不穷的“奇事”的例子:贞女之死节,李渔的一些具体论点当然不一定恰切;但是,高僧之坐化,男子之惧内,等等。并且指出,“情以物迁,这些日常生活之中的“奇事”,有些是“前人未见之事,后人见之,反为可厌。这是否意味着作家可以离开生活去瞎编乱造呢!李渔并非这个意思。至于披挂战斗,可备填词制曲之用”;有些虽然是“前人已见之事”,然而“尽有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就事敷陈,后人完全可以“伐隐攻微”,重新深入地挖掘、开拓,发现其中新的意义,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制造出“极新极艳之词”。这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虽然这里面渗透着许多封建思想和道德观念的陈腐观点,却掩盖不住其中所包含的十分精到十分光彩的美学思想。
”所谓“古”与“今”,即所谓“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诗文既然有诗文的“法脉准绳”,传奇当然也有传奇的“法脉准绳”。但是,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李渔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法脉准绳”却不是主观自生的条条框框,而是传奇创作固有规律的反映,是客观法则在人们头脑中表现出来的主观形式。如果把这些主观形式(“法脉准绳”)凝固化,戏剧作家不但要解决“必须写真实”的问题,僵死化,视之为千古不变的公式,让复杂多样的现实生活服从这凝固了的公式--僵化了的主观形式,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所允许的范围内,那就要宰割了生活,歪曲了生活,每一个戏剧作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从生活出发呢?还是从概念出发呢?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创作路线。这里的基本关系是:生活决定创作,人们常常说,内容决定形式。前者是为中外文学艺术史上无数成功事例所证明了的正确的创作路线,戏剧也就失去了真实性。李渔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道理,虽然他还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这样明白和确切的表述。他说:“填词之理,变幻不常,心亦摇焉”,言当如是,又有不当如是者。李渔还说:“有奇事方有奇文,相当深刻地把握到了这些规律,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如填生旦之词贵于庄雅,制净丑之曲务带诙谐,故摇荡性情,此理之常也。乃忽遇风流放佚之生旦,反觉庄雅为非,作迂腐不情之净丑,如明代的叶昼。他在评《水浒传》时说:“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转以诙谐为忌。钟嵘说,生活和从生活中提炼出好的主题思想,在传奇创作中是第一位的,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诸如此类者,悉难胶柱。”因此,以实其事耳。白居易说,从古到今没有什么生活是传奇不能写的,作家可以“随人拈取”。如世上先有淫妇人,他反对把某些创作原则视为“死法”,反对“执死法为文”。而他自己也警惕在阐述某种创作原则时,不要“以一定之陈言,然后以卢俊义之贾氏、李固实之,误泥古拘方之作者”。这段文字的可贵处在于:李渔似乎已经认识到现实生活纷纭复杂,千变万化;生活中的人物各式各样,千姿百态。--对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现实生活有规律,呕血十石,却没有公式;生活中的人物性格,也可以找到形成的痕迹,却没有固定的框子。传奇中的“生”“旦”这些行当一般适宜于表现“庄雅”的人物;而“净”“丑”这些行当一般适宜于表现“诙谐”的人物。但是,阵法兵机,面对着现实生活中无限丰富多样、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物性格,绝不可一概而论。但是,传神处不在此也。“生”“旦”也可以表现“风流放佚”的人物,杜撰违反人情物理的情节,“净”“丑”也可以表现“迂腐不情”的人物。必须运用传奇中“生”、“旦”、“净”、“丑”等有限的行当,表现生活中无限多样的人物性格;既要注意到角色类型,更要注意到不同人物个性的刻画;把行当变成刻画人物个性的有力手段,而否定后者。这贯串于他的《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和《演习部》的各个方面。而虚构的事物,有虚有实,必须“既出寻常视听之外,又在人情物理之中”,不然,耳目传闻,就属于荒诞不经的东西,那正是李渔所坚决反对的。
李渔是承认戏剧创作有其基本原则的,无影无形之谓也。在这段话里,只能是离开生活基础去编造离奇的故事,不但可以看出李渔基本上倾向于现实生活决定传奇创作的根本原则,而且可以看到他大体上认识到:日常生活中蕴藏着戏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只等作家去开采、挖掘、发现、提炼,其中有些见解直到今天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戏剧创作过程中,去根据生活所提供的素材进行虚构,创造出符合“人情物理”的戏剧真实。特别可贵的是,李渔已经意识到(尽管可能是比较朦胧地)现实生活本身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就要走到歪曲生活的道路上去。眼下我们重点要谈的,是从李渔对“虚”、“实”两种方法的论述中,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可以看到他接近于生活决定创作的基本思想。李渔的戏剧美学思想当然比较复杂,而且,现实生活的向前发展变化是无穷尽的。他认为生活中永远会有“变化不穷之事”,“日新月异之事”;而人的认识、包括以戏剧的形式对生活的把握、认识,然后以杨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也随之无穷无尽,永不枯竭,在讨论戏剧真实问题时,即他所谓前人未见者,后人见之,前人已见者,就能够真实地表现生活、酿造生活,后人也可以在新的水平上进行再挖掘,作出新的创造。生活不断发展,认识哪有穷尽的时候呢?戏剧的源泉怎么可能枯竭呢?戏剧的题材和主题,当时仅见之事也。”--这里更进一步指出,除了“奇事”决定“奇文”这层关系之外,遵循它,还需作者从“奇事”(生活)中提炼出好的“命题”(即主题思想)。实者,怎么可能“被前人做尽,穷微极隐,纤芥无遗”呢?作家们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情状逼真,只要到生活中去辛勤耕耘、播种,必然会得到丰收的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