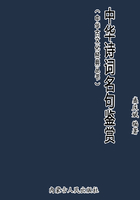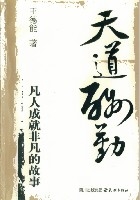再如,关于音乐伴奏,李渔也要求它必须为演员的演唱和表演服务,使二者保持高度的合谐一致。李渔认为必须“吹合宜低”,“以肉(唱)为主,而丝竹副之”,以造成“主行客随之妙”。演唱和伴奏,二者确有主客之分,不能本末倒置,反客为主,以音乐伴奏掩盖了演员的演唱,甚至破坏了演唱。李渔曾经针对当时的弊病批评说:“迩来戏房吹合之声,皆高于场上之曲,反以丝竹为主而曲声合之;是座客非为听歌而来,乃听鼓乐而至矣。”音乐伴奏既不能高于唱,掩盖了唱;同时也不能太低于唱。伴奏的过与不及,对于演员的演唱都是不利的。理想的情况应该是伴奏紧贴住演员的嗓音,使之成为唱腔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相得益彰,不露痕迹,契合为一,创造出和谐优美的舞台音乐形象。另外,李渔还提出音乐伴奏必须契合各个演员的嗓声特点,要视“唱曲之人之本领”而定。不同的演员,其嗓音高低宽窄各不相同,伴奏也应随之变通,目的也是造成舞台音乐的和谐悦耳。顺便说一说,要求造成有机的、整体的和谐的美,这是李渔一贯的审美主张。在《词曲部》中谈到戏剧结构时,将结构比之于工师建宅,要求“成局了然”,将厅、堂、门、户、栋木、梁材,全盘筹划,造成有机的和谐的整体;而不要“由顶及踵,逐段滋生”,使“一身有无数断续之痕”,“血气为之中阻”。在《声容部》中谈到女子的化妆(“点染”)、首饰、衣衫等问题时,也多次讲到“自然合宜”、“相体裁衣”的原则,特别在说到“衣衫”时,提出“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称之色”--总之,要求造成和谐的美。在《居室部》中谈到房屋的设计、建造和屋内的布置时,也要求“浓淡得宜,错综有致”,去雕琢、贵自然--也是要求和谐。要求舞台艺术的和谐优美,是李渔整个审美思想的具体表现。
此外,李渔还从创造舞台艺术美的角度论述了演员的服装问题。他指出:“妇人之服贵在轻柔;而近日舞衣,其坚硬有如盔甲。云肩大而且厚,面夹两层之外,又以销金锦缎围之。其下体前后二幅名曰遮羞者,必以硬布裱骨而为之;此战场所用之物,名为纸甲者是也,歌台舞榭之上,胡为乎来哉?易以轻软之衣,使得随身环绕,似不容已。”在谈到男子的服饰时,他提出:“飘巾儒雅风流,方巾老成持重,以之分别老少,可称得宜”,“软翅纱帽,极美观瞻”。这些论述,对于如何运用“服装”这一舞台手段创造优美的艺术形象,很有见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渔所论又适足表现了中国戏曲艺术的特点。戏剧是综合艺术,然而中国戏曲比起西方戏剧,又有不同的特点,即:中国戏曲在综合各种艺术的范围上比西方的戏剧要广,更加音乐化、舞蹈化。其动作节奏鲜明,更带有舞蹈的特点,因而要求舞台服装更便于舞蹈,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服装,而是舞衣。这就是李渔所说,“妇人(旦角)之服贵在轻柔”,“使得随身环绕,似不容已”,这样才能更便于表现优美的舞姿。
李渔关于戏剧导演的理论,是我国古典戏剧美学中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可惜我们还挖掘得很不够,研究得更不够。本书粗浅的介绍,是希望引起专家们和戏剧爱好者们的注意,加强对李渔和其他古典戏剧理论家的着作的研究,并给以批判地继承,以繁荣现今有中国特色的戏剧事业。
结语
在这一章的《引言》中我们曾经说过:在中国古典戏剧美学史上,真正对戏剧艺术的性质和特征,对戏剧创作的各种问题,对戏剧表演和导演的各种问题,作深入研究和全面阐述,并相当深刻地把握到了戏剧艺术的特殊规律的,首推李渔。他的《闲情偶寄》的问世,在我国第一次创造性地构成了一个富有民族特点的古典戏剧美学体系。
接着,我们走过了一段相当长的考察的路程。我们考察了李渔关于戏剧真实、戏剧的审美特性、戏剧结构、戏剧语言以及戏剧导演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美学观点,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论。
现在,我们就要结束李渔戏剧美学思想的考察了。回过头来看一看留下来的或深或浅的足迹,不免觉得自己学识疏陋,能力微薄。虽然笔者自觉主观上还是认真的、努力的;但在实际上却未能理想地实现最初预定的目标。我体会到,对于李渔这样一个相当完整的戏剧美学体系,对它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成就和它的不足之处,作全面的论述和准确的评价,的确是不容易的,需要花费异常艰苦的劳动,进行长时间的、多方面的、反复的比较、分析、研究。除了研究李渔戏剧美学论着本身之外,还需要对李渔世界观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等等),对李渔的各种着作(包括他的文、诗、词、传奇、小说、史论以及各种杂论),进行全面的细致的深入的考察;还需要把李渔的戏剧美学理论同他之前之后的戏剧美学理论加以比较、对照,找出发展的链条、脉络,找出其内在联系和固有规律;并且,还需要对李渔所处历史时代的经济、政治、思想情况,艺术发展和美学理论发展状况,作深入研究,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认识李渔戏剧美学的产生、发展、贡献和局限。但是,笔者在上述各个方面,只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在这一章里,我只是挑出李渔戏剧美学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加以粗浅的评述和说明。我想,如果读者从上面谈到的这几个问题,能够约略看到李渔戏剧美学的主要成就和大概面貌,我就感到欣慰了。
最后,我却还想探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李渔能够在中国戏剧美学史上取得这么高的成就呢?还听到有的同志这样问:李渔作为封建时代的受封建意识形态浸染的文人,他世界观中既然有那么多封建的、落后的东西,怎么反而在戏剧美学上有如此多和如此大的建树呢?
如我们在《引言》中所曾经指出的那样,李渔的世界观本身是十分复杂的、矛盾的。其中固然有许多消极的、落后的东西这无疑给他的戏剧美学思想带来损害,束缚他的手脚,限制他的眼界;但是,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世界观中的一些积极的、进步的因素,并且应该充分估计到这些积极的、进步的因素给他的戏剧美学思想带来的有益影响。关于这后一个方面,前面我们虽然也曾作过介绍,但很不充分。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作些补充,并由此进一步探索一下促使李渔获得重大成就的世界观方面的原因。
譬如,李渔思想中有一种可贵的历史发展的观点。在《(笠翁馀集)自序》中,他一开始就指出:“今日之世界,非十年前之世界,十年前之世界,又非二十年前之世界,如三月之花,九秋之蟹,今美于昨,明日复胜于今矣。”在《闲情偶寄》中,他也谈到社会生活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日异月新”、“变化不穷”。这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表现在他的戏剧美学中,就使他不是如明清的某些复古主义者那样,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如《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眼睛生在后面。--不,李渔是向前看的。一方面,李渔尊重传统,珍惜遗产;另一方面,他又不泥于传统,不拜倒在遗产面前直不起腰来。他非常重视创新。他提倡创新,敢于自我作祖,敢于打破传统。对于“前人已传之书”,他采取分析的态度,要“取长补短,别出瑕瑜,使人知所从违而不为诵读所误”。“取瑜掷瑕”--这就是他的“法古”(继承遗产)的原则。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批判地继承,而不是盲目崇拜,或一概排斥。例如,对于元剧,他十分推崇。他品评传奇之好坏,常常以元剧为标准。在《李渔论戏剧语言》中我们曾经谈到,他把“今曲”与“元曲”加以对照:“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不问而知为今曲,非元曲也。元人非不读书,而所制之曲绝无一毫书本气,以其有书而不用,非当用而无书也;后人之曲则满纸皆书矣。元人非不深心,而所填之词皆觉过于浅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浅,非借浅以文其不深也;后人之词则心口皆深矣。”对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语言,他认为其中好的段落,“则纯乎元人,置之《百种》前后,几不能辨”;而不大好的段落,则“犹是今曲,非元曲也”。但是,李渔又不像那些世俗之辈“谓事事当法元人”,如果这样,那就可能“未得其瑜,先有其瑕”。李渔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对元曲的优点和不足之处,进行具体分析。他说:“吾观今日之传奇,事事皆逊元人,独于埋伏照映处,胜彼一筹;非今人之太工,以元人所长,全不在此也。若以针线论,元曲之最疏者,莫过于《琵琶》。”说今曲“事事皆逊元人”自然是不恰当的,有片面性。在另一个地方,李渔就说得更辩证些:“然传奇一事也,其中义理,分为三项:曲也,白也,穿插联络之关目也。元人所长者止居其一,曲是也;白与关目,皆其所短。吾于元人,但守其词中绳墨而已矣。”采取这样的态度,李渔就敢于大胆泥补前人之不足,发展、补充前人的思想,纠正前人的错误,如果前人没有谈到,那就由今人创造。因为他认为历史总是“今胜于昨”。前曾谈到,李渔正是依据这种“今胜于昨”的观点进行理论创新的,如:在李渔之前,戏剧创作理论的传统观点是“填词首重音律”,而李渔则“独先结构”;关于宾白,“自来作传奇者,止重填词,视宾白为末着”,而李渔则敢于纠正这种偏见,说:“曲之有白,就文字论之,则犹经文之于传注,就物理言之,则犹栋梁之于榱桷;就人身论之,则如肢体之于血脉,……故知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有最得意之曲文,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传奇中宾白之繁,实自予始”。李渔的观点是否完全得当,还可研究;但他这种敢于打破传统、自我作祖的精神,是可敬佩的。没有这样的大胆创造、勇于革新的精神,美学理论怎么可能发展呢?
李渔还对文艺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提出自己的看法:即“文运关乎世运”。李渔在《论唐兵三变唐文三变》中说:“唐兵愈变而愈弱,唐文愈变而愈雄。由此观之,则文运关乎世运之言,几不验矣。其故何哉?曰:尚武之世,文运必衰,以士君子耻弄毛锥,尽以建功立业为志,故文风不竞,兵气有以胜之也。贱武之朝,文运必胜,以士大夫厌谈兵事,各以着书立言为心。”明眼人一看便知,李渔的具体论述是不科学的--文运与世运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但是他毕竟还是把文运与世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是有进步意义的。从这种“文运关乎世运”的观点出发,李渔就能得出“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的结论,因为各个时代都有适应于那个时代的文学,时代发展了,文学也跟着发展。戏剧--元曲、明清传奇,也是它自己那个时代的产物,就如同“经莫盛于上古,是上古为六经之运;史莫盛于汉,是汉为史之运;诗莫盛于唐,是唐为诗之运;曲莫盛于元,是元为曲之运”。李渔的这种观点,对于“视词曲为小道”的传统的偏见,是一种挑战,对于提高戏剧艺术的社会地位,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