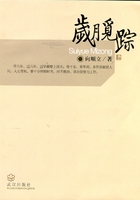我在海上拉响了汽笛
我上到拖肖5高层的右边,趴在栏杆上看海。栏杆宽宽的,我完全可以从栏杆里钻出来蹦极。突然,船左右摇晃起来,好像想把人从左边抛向右边,再从右边抛向左边。有人拨拉了我一下,于是我不知怎么的就在左左右右的晃荡中,被人轻轻拨拉进了驾驶室。他用一个最简明的动作示意我呆在室内。那动作简明到我都没有看到,只是感觉到了。我跌向椅子,又跌向墙边。他还站在驾驶室门口。如果我从室内跌出去,他也会拨拉把我再拨拉进室内。
我们一队北京人,一起在山东省日照市上了这艘船。我和很多同行还不怎么认识。醤如把着门口的这位大汉。我扶着什么物件站稳后,我对他玩笑:你不会掉下海吧?
我笑笑地望着他。但我吃惊了他为什么脸红?哦,他不是我们北京人?他就是上的?我居然还问他会不会掉下海,这叫人怎么回答?他不知怎么回答,就脸红了。后来我看到,他不脸红的时候也是红脸大汉。
我再不敢说什么,只是看着船长刑。我只看到船长的背,他那穿着灰上衣的高高大大的背。他正在把自己的拖舟?去顶住一艘巴拿马船,让那肖整到和航道一个方向。我好像觉得他是用自己的灰色大背在顶住巴拿马船,好有力量。
灰色大背身后,有一把高高的木椅,好像饭店里为幼儿准备的高椅。红脸大汉或灰色大背都不理会我,干站着又有点乏味,我于是干脆坐上了这把高椅。坐在驾驶室里唯一的这把椅子上,可以看得很远。我双臂往椅子扶手一搁,顿时产生一种伟大感一有一次在颐和园,我往慈禧太后坐过的椅子上一坐,双臂往椅子背一搁,在照相机镜头前做出了太后状。可是那天我穿一件绿底白块的恤,照片出来一看,整个儿一蛙太后。
无论如何,坐在灰色大背身后的高椅上,有一种安全自得的快乐。这时就见灰色大背用右手拽住屋顶上的木把,拉了两下,拖船响起了两下汽笛声。那么响,那么远远地铺开在海面上。我跳下木椅,走到灰色大背身旁,看着屋顶上那个奇妙的木把。我多想多想拉一下。我用手指头轻轻碰一下木把。我用手又摸一下木把。你拉一下吧。红脸大汉开口了,每个字都说得硬硬实实的,叫我想起山东的煎饼。吃煎饼长大的人,人也瓷实,心也瓷实。
我怯怯地看一眼灰色大背。他没说话。我也没看见他的脸。只是感觉到,他用沉默的背,表示我可以拉一次。我伸出右手拉了一下,不响。再拉,还是拉不动。我使劲使劲拉,我整个人我全身就吊在右手上,吊在那个木把上了。我的身体晃来荡去的。
不不,这只是我的感觉,我想象中夸大了的感觉。我第三下拉响了汽笛。我把很大的声音放在很大的海上。我在很大的海上放上很大的声音。哦!我一職老高。
我忽然想,我的伤怎么好了?来日照前还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今天上船的时候就觉得行走自如了,而且禁不住地老想笑,找茬大笑。要是在房子里,这样的旁人是一种騷扰。但是在海上,面对这么大的大海,还有什么可称大的?如何地笑,也被一阵海赌走了。海风卷去的,连同我的病痛。
我多想说,给我一片海。我想,红脸大汉会硬实而简明地说,拿去吧。或许,我已经拿了一片海了,在我拉响汽笛的时候。
迪斯尼的鞋兄鞋弟
让我想想,我是在洛杉矶,在迪斯尼。然而怎么一眼望去,白晃晃的阳光下,一地白晃晃的白网球鞋?与我脚上的鞋一模一样,只是大些或小些。我的鞋,是在国内买的,我从小穿到现在。这些年,女鞋年年有时尚。总有人相劝,你怎么还穿这种鞋?你也可以换成旅游鞋,好看的旅游鞋多的是!
是的,很多,太多,多到人皆有之,人皆穿之,我就不大想穿。当然,严冬天寒地冻,两只脚穿上旅游鞋,如同住进两幢保温的房子。但寒风一过,我的脚就从旅游鞋里探头探脑地伸出来,看看外边还冻不冻?可以出来了吗?可以了,可以了!两只脚从旅游鞋里一跃而出,跳将起来,搬回心爱的老巢一一白网球鞋。啊!这样地鞭、白洁、简练,每走一步就传递着白网球鞋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走路有弹性,心與也年轻,行动更简明。
这样健身健心的鞋,为什么叫我不要穿?因为大家都不穿?大家都穿的鞋我也穿,我不就成了大家了?
我的鞋,也习惯了在多种公众场合的形单影只。在迪斯尼突然面对着一地的白网球鞋一地的同类,反而蒙了。不明白自己这是在北京还是在洛杉矶?在北京,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女性穿一样的网球鞋;在迪斯尼,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第二天去好莱坞,又见一地的鞋兄鞋弟,好像四海之内皆兄弟。后来才知道,美国女性这两年时兴穿白网球鞋。哈,我生出来就穿这鞋了,我的鞋率先时奪了,原舰以为我的鞋自甘落后呢。
我得意地在洛杉矶走来走去,就像一导女鞋新潮流的胃大王。
女人怎样爱自己
7尺,冲下来,前后左右。每到午夜,我把自己交付给那个几十元钱的国产喷头。
7欠们快活地鲜活地扑腾过来,争先恐后,在淋滴尽致的服务中,把我的疲劳带走。我想起《飘》的原名随风而去,我这是随水而去。
这是我告别每一天的最后一个乐章。朋友问我女人怎样爱自己,我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我一点说不出女人怎样爱自己。使劲儿一憋,想到了午夜的淋浴。还有些什么呢?给自己买小玩具。还有呢?
也许,也许我需要爱的人,需要我爱的人,实在叫我不太有工夫再去爱自己了。这个还需要什么,那个又需要什么。爱需要力量,去奔波,去投入,去付出。爱是生命的支点,是生存的实感,是心灵的阳光,是青春的歌唱,是无边大海的汹涌,是山间濮的流淌,是田野小兔的奔跳,是草原驶马的长啸。
爱使人生辛劳又甜蜜,丰厚又滋润。就像李玟唱的《好心情》:有你就有好心情,好像夏天吃冰淇淋。
如果说,青年是一个年龄段,更是一种心态;那么女性是一个性别,更是一种心性。女人是善良,是爱情,是快活,是天真,是宽谅,是柔韧。女人怎样爱自己?
人生没有下脚料
我没有想过要当作家。我没有想过要做文为生。我是说我海读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第一想当的是篮球运动员。酷夏的星期天,我常常一个人翻进一楼的体育教研室,抱起篮球,又从窗口翻出来。然后奔向操场。操场好像被烈日晒化了,晒得什么都化掉了。只剩下一个我。
还有天上的一只火球,和地上的一只篮球。
那时的女生都梳两根辦。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地把我校的辫子篮球队带到我家,用我家的一把剪刀,我们互相剪去了二十多根力辦。妈妈下班回家,迎接她的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头发。和一个叫她目瞪口呆的短发女儿。
妈妈立即展开了与满屋头发的大战。她顾不上说我一句一不不,不是顾不上,是她本来就不射兑我。我喜欢麟,那就姆吧,那籠发吧。我为篮球狂,一直狂到病倒休学。
妈妈天天照料我,还是没说我一句。或许我不过是充满激情地投入一项热爱的运动,虽然有点奋不顾身。激清是不需要被指责的。
篮球打不成了,我开始移情别恋,爱上了英语。到高三,我一心想当的是英语笔译。我给同学们起了很多可笑的英语绰号,我填写的高考志愿一律地是英语。那时可以填14个志愿。我只填6个。
因为,那还用说吗,考英语我是稳拿,填那么多干吗?但是,没等高考,上海戏剧学院派人到各中学来物色新生,用现在的话,叫做星探,叫我去上戏。我做着我的英语梦,自然不去。直到中学团支部找我谈话,直到我在上戏报考单上绕开表演系写上了戏文系。
没有想到我被录取了。更没想到,莎士比亚的诗意和激情,是这样地震撼了我这17岁的心灵。我读译本,读朱生豪读方平。我要读原文,抱着字典一点一点啃。大二开始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大三跑上海图书馆,抄录全部英文的有关莎士比亚评论的题目。我想全部读完!
事实上,我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老跑上海图书馆去读资料,只是我以为我能做到。我至今保留着爸爸给我的两本字典一英汉和汉英。已经给翻得书页都脱落了,好像老人松动的一口牙。我为英语狂,我为莎士比亚狂的时候,爸爸妈妈一直支持我。倒好像我的每一,-是对的。
我出生以来一直体弱多病,但是爸爸妈妈的呵护,使我的好奇心、我的想象力一直不弱。大学时我的好奇心驱使我要去读完关于莎翁的英文评论。中学时候我的想象力使我毫不怀疑我会成为上海女篮的中锋,我也已经走进上海市队打过中锋,只是在市队要给我发球衣那天我已病倒在家了。我想到的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做到。但是,有想象力有好奇心,就有动力就有激情。
我的想象力够不着的,是后来我的工作是专职作家。所以突出工作两字,因为我没有想过要当作家,如同我没有想过要进戏剧学院。1980年底,我奉命写一出大戏。我用7天写了一个五幕轻喜剧。在北京的西单剧场演出时观众从头笑到尾。当时的北京人艺和中国儿艺来抢我,相持不下,有关领导干脆把我调进北京作家协会。
这么多年我写的一直是散文和报告文学,直到21世纪才突发奇想地要写小说。一写,竟是像一个剧本。有人称之为视听小说,有人称之为跨文体小说。我心窃喜,我想我的舞台剧本行还没拿出来呢。
一到足球世界杯或奥运会,总有些人约我写稿,总觉得我爱运动爱写运动。我想诸位不知道我可真的有一-球史,至今想到上海体育馆篮球场那锃亮的糊板,看到我自己雕投篮的背影,心痒呢。
我很痛惜的是我的英语,六七十年代的横扫一切把我的英语也扫掉了。本世纪初我运动过激眼睛动手术,闭着眼睛涂写一些人生快乐之事,没多少文字,交给了当时在华艺出版社的金丽红。有天晚上10点半了,金丽红不期而至,要我槪抵本小书的中英文。面我不行的。她说你行的,明天中午12点后交稿。说完她就走了。
好像灰姑娘害怕午夜12点15,我一想起明天中午12点,觉得那么恐惧!她怎么会说我行?我怎么能行?我在灯下摊开那中英文,摆上英汉和汉英字典,校对起来。我怎么会校对了?到第二天中午12点,我好像刚刚上完英语补习班处了考卷。
过去的人生经验,都是今后人生的原材料,或者是能源。没有下脚料。
尤其是,在上海图书馆抄录英文目录的贪婪时刻。尤其是,天上一只火球地下一只篮球的激情时刻。
我说的话我自己都不信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我说的话我自己都不信了。我说,我亲近的人都不信了,然后,我自己也不怎么信了。我再说这话的时候,那口气,就犹豫起来,游弋起来,站也站不稳,靠也没处靠了。
即使这样,我说的时候还是真心的。我是说,这一段忙完后,我可以休息-下了。
这句话,现在说来有些删改。原先是说一定可以休息一段了。语气就尤其给删改了。原先是丰厚而响亮而多声部合唱似的。现在,高音部删去了,中音部删去了,只剩下一个低音。单单地,弱弱地,或如无奈的萨克斯。去年我辛苦。去年底宣布今年要休息一段了。然后,这个宣布挪到了今年5月后。再然后,又挪后3个月。
然后。又挪-。终于,我再宣布的时候,还要加上一句:不过没有人相信我了。再终于,再再加上一句:我自己也不知道做得到做不到了。说起来,我今年忙的书之一,是一本我做的洋娃娃的服装书,96款服装的闪亮登场。而这闪亮背后,是暗无天日的制作,好像所有的黑夜都变成了涅瓦河畔的白夜,一天24小时都供我设计供我制作。也供我娱乐。
今冬服装的时尚是,大一号,这实在是个很可爱的概念。工作这个概念,也很可以大一号。又想到和谐这个词,有时候没完没了地黑白颠倒,也是一种和谐。因为这是一种生命的需要,一种生存的符号。
这一年就要过去了。没有人翻信我的。不过,我觉得这其实是我的和谙生活。
我没有从独木桥掉进岷江
此刻拿起这支笔,我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可就是想拿起笔,就是想写什么。
刚才从《羊城晚报》上读到一则腿: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索欄垮,全国生物教师夏令营四人死亡一人失踪。他们是前往卧龙山五一棚时经过岷江支流的。我的心,像索桥那样颤悠着,嘣地断裂了。我想我应该走过这座桥的。只不过他们是一个团队,我是个人采访一实地采访卧龙保护区的看林人。我自己得有个五一棚。记得快近原始森林时看到一堆野猪屎,或是一堆野牛屎。如果野猪来了怎么办?我问看林人。他说他在山林30年,他从不伤害动物,动物也就不伤害他。我记得过独木桥时他拉着我,那实在不能箅桥,那只是一棵树随意地搭在河两岸,树下是湍急的河流和直冲而下的如房子那么大的巨石。
我没有从索桥上掉下去,我尤其居然来回走树而没有从独木桥掉进岷江去。或许终是我们人少,并不会惊动这无人之境。
或许,这样的自然保护区,本不该有很多的人去惊扰。自然保护区,其实也几近是无人区。这里只保护自然,不保护人。自然本来是最美丽丰厚的。但是如果人类非要按自己的意志改变它,人要是激怒了它,那么大自然的脾气也餓灭性的。
就想起大约十来天前从报上看到,在四川窦圇山双峰间的铁索上做高空表演的勇士不幸跌落。天!我的心一下随他跌入山谷。我曾经像小孩子崇拜战斗英雄和他攀谈过。我在窦圃山顶看他表演,用双手捂住脸,从指缝里看的。看完他的表演后大家看我我满脸是泪。我不忍看,不愿他天天用生命去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他站在山顶间的铁索上,他比山还高。现在,山还是证明了山比他高。
人类和自然的相处,也要睦邻。大自然这位芳邻,为人、空气和千姿百态的美丽。可是人类呢?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姑娘
我生出来的时候,很瘦,妈妈不敢碰我的手指头。要是一碰就断了呢?我一直生病:这天医生又来了,说不用给这孩子看病了,救不活了。我是喝药长大的。一两岁时要喝水就喊药,药。妈妈喜欢看电影,她抱我去电影院,就怕电影中有人喝水。人家喝水我也要喝,我就指着银幕喊:药!药!
上孝后,常常生病。我一人躺在床上,看石灰剥落的天花板。我从那斑斑驳驳中,看到童诗中的宫殿、王子、公主,看到窈窕的身材、撑开的大裙,看到王子和公主的美丽的故事。每次生病,都有王子公主陪我。
假期里,爸爸天天早上教我和两个弟弟背古诗。我家住在三楼。夏天打开门,坐在楼道口很凉快。我和弟弟都坐在那里,扯开嗓子读诗。任何人只要一进我们这幢楼,就会听见我们三个6岁上下的孩子,用老辈人的拿腔拿调背祖先的祖先的诗文。
白天功课多,玩的时间少。我和弟弟相约,等爸爸妈妈睡着了,我们再爬起来玩,把白天拉长。爸爸妈妈是中学教师,没钱给我们买玩具。我们的玩具是自己攒的,醤如各种纸盒,最多的是装一块上海药皂的纸盒。夏天的夜晚,有月光,有星光。我们毋她上,用纸盒搭汽车。其实不是汽车,是连接起来的一幢幢奇特的房子,不过可以开动。我们用想象把这串房子开得呼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