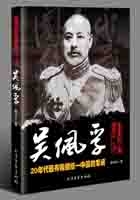别父老,入梨园,生命中的风景
听过《前门情思大碗茶》的听众都有相同的感觉,那旋律那韵味,似歌似戏,非歌非戏,戏中有歌,歌中有戏。熔歌曲和戏曲于一炉,这正是“大碗茶”的妙处,郭公芳的成功得益于她数年来的梨园耕耘。
1973年夏天,一场海风刮来一个喜庆的信息:山东省戏曲学校来青岛招生,招生的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跃跃欲试者纷至沓来,报名地点就设在郭公芳就读的上清路小学。近水楼台先得月,学校的音乐老师把郭公芳推进了考场。初生牛犊不怕虎,她大大方方地站在考官面前,唱了一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嗓子条件不错,心理素质很好,这是考官给她的印象分。就在那个夏天,她中榜了,入学通知书给她带来了一个莫大的惊喜,那年,她十岁。
“她还是一个孩子,从小娇生惯养,一个人出远门行吗?”父母亲为她担心,可并没有擅自做主,认真地征求她的意见。
“公芳,你愿意一个人到外地去上学吗?”
“愿意。”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会照顾自己吗?”
“会。”
“你会洗衣服?”
“不会就学。”
“你想不想家?”
“不想。”
“你不想妈妈?”
“想啊,放假了回家看你们。”
妈妈流泪了,郭公芳却没有哭,她生性刚毅,很少流眼泪。妈妈一边流泪一边给她准备行李,她知道妈妈不想让她离开,可不安分的她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济南是省城,省城是什么模样?那里有大明湖、千佛山,那山那水令人神往。对她来说,更具有吸引力的是那所在梦里也不曾出现过的戏校。那是一个样板戏风靡的年代,文艺园地一枝独秀,京剧舞台遍及城乡,当一名京剧演员多荣耀。郭公芳感谢命运的安排,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一颗希望的种子。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接下来的日子,细心的母亲给她缝制衣被,哥哥姐姐们为她准备日常用品。临走那天,全家人一起把她送到火车站。火车开动的瞬问,透过车窗看着母亲那张流泪的脸,郭公芳再也忍不住了,不听话的泪水流过脸颊,流进嘴里,那滋味有酸有咸。身后是一个温馨的家,前方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看着亲人那渐渐模糊的身影,一种从没有体验过的离愁爬上心头。
新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开始,环境变了,条件变了,生活节奏变了,面对全新的一切,郭公芳才觉得自己难以适应。过去在家里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现在所有的事都要靠自己做。过去在家里可以“倚小卖小”,可在学校里却没有人买账。最难熬的是到了晚上,她想家,那是刻骨铭心地想。一闭上眼睛,爸爸妈妈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闪动,老师同学的影子就不时地在眼前出现,还有家乡的大海,大海边的童趣,这一切都那么遥远。一想到这些,她就想哭。白天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她不敢哭,只有到了晚上蒙上被子才能偷偷摸摸地哭一场,常常是哭着入梦,又从梦中哭醒。
每逢周末,班里的同学回家的回家,投亲的投亲,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只孤雁就有她一只。无事生非,为了排解孤独,不安分的她常带着那些“无家可归”的同学去“闯”外面的世界:到学校后面的坟地里拆花圈,到老百姓的包谷地里掰玉米,到池塘河边捉青蛙……“祸”闯得多了,麻烦也跟着来了。那天,她们从包谷地里掰来嫩玉米,捡来废报纸,兴致勃勃地在宿舍烤了起来。烤熟的玉米没吃到嘴里,却引发了一场火灾,幸而抢救及时,没有酿成大祸。“烧烤事件”轰动校园,她因此差点儿丢了学籍。
被窝里的梦做得正香,起床哨却催着人起床。早操、晨练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冬天夜长,黑咕隆咚起床,迷迷瞪瞪出操,出完早操还没有睡醒。能睡个懒觉该有多好,在当时那是最大的享受。睡懒觉的“享受”只有值日生才有,每个月才能轮到一次。郭公芳总是争着抢着当值日生,培养劳动观念是假,多睡一会儿懒觉是真。她年龄小,大家总是让着她。
把“寒窗”喻为学校是再贴切不过的了。那个年代,学校环境条件差,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电扇。每逢夏天,身上长满了痱子,到了冬天,手脚生满了冻疮。最累最难的是基本功课,练形体,练嗓子,练下腰,练劈叉,练倒立,一天下来,浑身疼痛难忍。炎炎的烈日下练倒立,汗水和泪水一起往下流。冬天迎着西北风喊嗓子,喊着喊着哭了起来。那段日子的确很苦,苦了整整六年。
郭公芳属于“两头冒尖”的那一种,“调皮捣蛋”她是挂了号的,可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用老师的话说“她是那块料”。在那个倡导“又红又专”的年代,郭公芳成了“只专不红”的典型。班里的同学全都入团了,她成了“重点帮教”对象。辅导员老师找她谈话,鼓励她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她心领神会,立马写信搬来援兵,求哥哥帮她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后来她如愿以偿地入了团,那份光荣里有一半是哥哥的功劳。
毕业汇报演出是对六年来学习成绩的最后检阅。郭公芳汇报演出的曲目是《白蛇传》,她担纲主角许仙。
《白蛇传》是古装戏的经典之作,演和唱都有较高的难度。六年寒窗,如何交一张合格的答卷?面对评委们审视的目光,郭公芳胸有成竹地走上舞台。手眼身法步,步步到位;道白演唱,字正腔圆;一场踢花枪的武戏,居然踢出了一个满堂彩。演出结束了,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省京剧团,成为该团最年轻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