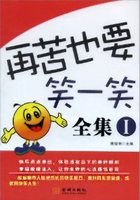有一种意见,我是不能苟同的。这种意见认为,报告文学似乎只应具备批判性功能,而只有批判才能最充分地发挥报告文学的效用。这看法显然是一偏颇,它既简单地对待了生活,也简单地对待了报告文学。只从作品的褒贬态度难以评判它的价值,当然也不能纳括一种文学形式的丰富特性与功能。报告文学面对的是全面纷繁的生活现实,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只用一种眼光和面孔来对待生活现实。重要的在于作家是否真诚地面对了真实,并且在这真实面前有一个适当准确的态度。对假的褒奖与对真的批判,其效果是一样的难以令人接受。
孟可的《希望之海》(见《当代》1989年第5期八罗盘的《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见《中国作家》1991年第5期久不约而同地报告和描写了奋战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石油地质工作者的生活情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被人称为“死亡之海”,有多少先行者在她面前却步或葬身沙海。可是,夕天,一批批的石油地质工作者要向这“死亡之海”挑战了。他们尽管有现代化装备,可要征服这不驯的大沙漠,却毕竟是一场异常艰巨且充满风险的战斗。这是人与自然的搏斗;这是生命与死亡的较量;这是精神意志与物质的决战。两位年轻的作者,深入前线,为我们带来的前方战事情景令人感慨晞嘘又惊心动魄。这里看似没有枪炮声,可狂风卷起的沙暴,超常酷热造成的干渴,迷幻一般变化的地形地貌等等,时时都在对石油地质工作者的生存及工作构成巨大的威胁,使之稍有不慎,就会有丧命的危险。然而,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石油地质工作者以自己的智慧和意志,虽然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不光以自己的生还打破了“死亡之海”不可战胜的看法,并且用自己出色的工作效果,为人们认识、开发这里时石油资源作出了空前的贡献。对于这样一些近似神话传说可又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和人物,孟可、罗盘的选择与报告适时而又生动形像。他们一致地对这些步入“死亡之海”,创造了人类辉煌业绩的人们,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与称颂之情。这是对生命的礼赞;这是对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的礼赞;是对人类在征服大自然的征途上迈出的重大步伐的礼赞。它对于认识人类自身和认识自然对象两方面都是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对于这样热情洋溢的赞美诗般的报告文学作品,我们没有理由忽略它的价值和创造。
同样,象王宗仁的《青藏高原之脊)系列报告文学(见《十月)1991年1期),《当代)1991年第4期,《长城”991年第5期)、王戈的《通向世界屋脊之路》(见《西北军事文学)1991年第1期入徐志耕的《莽昆仑》(见《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7期)、文乐然的(高原》(见《当代》1991年第3期》、燕燕、张卫明的《雪域战神汽见什月》1991年第5期)、江宛柳、王鹏的《高原之子》(见(昆仑》1991年第3期)等报告文学作品,又都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多少年活动于青藏高原的人们,以对这里不同人等接受高原的冲击、考验,在巨大的付出之后的收获情形的描绘,为读者打开了一道不易接近的大门,使其生动形象地领略这大门内许多难忘的人与事。氧气对生命来说,是一种随时都不能缺少的东西,可在广阔的青藏高原,独独欠缺的就是这种东西。由于氧气的欠缺,随之而来,人一切本来正常的活动都变得难以正常起来了。诸如吃饭,睡觉,行走这样近乎本能的行动,都变得殊异反常。正是生命对于高原的这种强烈的不适应,才使我们的战士,科技工作者,各样的工人,在他们的岗位职业活动中要经受许多非正常的困苦,付出更多的牺牲。他们守卫和建设高原,在这里探矿,筑路,从事各样的工作,他们投入的是生命和热情,奉献的是血肉和青春,得到的是一种无私圣洁的忘我精神。他们身居高原,恰似站在人生的制高点,把他们生命的颜色和辉煌的劳动成果,都书写在这不灭的高原之上,完成了它的永存。燕燕、张卫明在他们的《雪域战神》前面写道:“生存因死亡而益加珍贵;因险恶而越发坚韧。人与自然的永恒母题,也因地势凌空而高拔雄奇,接近太阳而灿烂辉煌:这是诗一般的颂词。然而,对于千百万生活与奋斗在青藏高原上的人们来说,它确系真诚情感的流露,是一种心的接近和血一样的热情表现。对于崇高的赞颂,多么炽热也不会过分。最令人无法接受和头疼的是那种虚情的矫饰与廉价的奉承。前者是对美的趋附,后者是对丑的贴近。报告文学的品格,也时常在这种对崇高的赞颂与虚情矫饰及廉价奉承的表现中反映出来。
其实,无论是布社会生活的实际存在中还是在报告文学作品中,是很难把赞颂与批判清楚地区分开来的。对某一个人、某一种行为的激赏,同时即是对其背面的批判。水落石出,扬正抑邪,从来都是辩证地统一,它并不是行政命令和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虽然人们总渴望通过主观的倡导能对生活,对文学产生重要影响,使生活同文学适应自己的愿望,可结果似乎多不能令人满意3不是效果甚微,即是南辕北辙,留下历史的尴尬。对于作家,对于报告文学来讲,它遵循的应该是时代的脚步,是不断发展的美的精神、美的行为和美的存在。作家作品应该在这样的原则下作出取进行判断,而不是为了一个什么具体的、近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轻易地校正思维方式和创作行为。若是代表了时代精神和进潮流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它自然会同作家作品的追求吻合,作家作品亦就无从谈及脤务与背离的话题了。事实上,不少优秀的报告文学,正是在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活密切联系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读者所看重和喜爱的。像贾宏图的《大森林的回声》(见《人民文学)1990年第9期),其主要目标是报告新上任的伊春市委书记杨光洪,写他如何“求真务实”,以一种新的行为准则和工怍作风改变伊春市的社会风气及生活面貌的情景。然而,这一目标的确立和杨光洪引起作家赞扬的根由却在于这里存在着群众极为反感的“五种流行病”,即“牢骚病、推诿病、扯皮病、妒贤病、护短病”。还有“三种人”,即“那些坐而论道的‘说客’,指手划脚的‘看客’,拨弄是非的‘政客’。”这“五种病”和“三种人”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情绪和领导的威信,是阻碍振兴当地生活难以逾越的恶疾。亦是像杨光洪这样把“合民心,顺民意,平民愤,察民情”作为为政之道的人无法容忍的。所以,作者在具体地报告了杨光洪果断扫除这“五病”“三种人”的动作之后,把来自群众内心深处的,对于杨光洪的赞誉称之为“大森林的回声”,使人感到一种打破沉闷的动响;感到一种大山林海的新的浦动,对生活生发出新的希望。但是,十分有趣的是,这篇主旨充满热情的作品,在其不少的篇幅里,却是以写主人公对丑陋,对恶习进行严厉地批判与革除为内容的。作品把赞赏置于对丑恶的鞭笞之上,结果在分明的对比中找到了一种强烈的效果。王中和、李恒茂的《鲍江兮》(见《满族文学)1991年第3期),也是对一位县农业银行行长的赞羡。说来令人遗憾,这位行长固然在合理利用农行资金,最大效用地开发农业经济方面有不少贡献,可最能动人的地方却是他不为歪风邪气所干扰,没有在受了多年的打击、委屈,再次掌权之后,利用这权力为自己谋取丝毫的利益。在正常环境卞,这种行为本属应当的基本行为。然而,在不正之风甚烈,以权谋私的行为颇多的现实环境中,这本属应当的行为作风却显得难能可贵了。生活的真实存在,也许造成了作者的窘态。可作者正是在这种生活的反常中认识了鲍江兮这个人物,看到了一种生活与时代的不邊应和浅显又深刻的现象。相似的作品还有关仁山的《播火者》(见《人民文学》1991年第3期刘志良的《魂兮归来》(见《北京文学)1991年第8期),贾宏图的《人格的力量》(见《人民文学》1991年第6期广王立新的《珍贵的遗产》(见《河北日报》1991年1月21日邓加荣的(一部打乱的日记(见《中国作家》1990年第5期),王德恒、程远的《水之魂)(见(青年文学》1991年第11期)等。怀着忆旧情绪的歌赞与批判,或许引不起人们强烈的兴奋,可是生活中并不乏在怀旧情绪里寻求新境的范例。特别是人们感到烦躁和茫然的时期,就更容易产生这样的怀旧情绪。这并不能说明报告文学作家游离于时代生活的前沿,或许这正是从生活最需要的地方投来的目光,发出的呼吁。
批判的态度并不一定就是消极的态度,更不能把批判性简单地视为破坏性。在许多时候,批判正是一种进取,是一种建设,是勇敢的探求。对于枇判的惧怕与推拒,有时实际上正是一种固守与乏力的表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进坟墓。”历史正是在一种不断的批判淘汰中得到进步与发展,得到变革与更新的。人们没有理由拒绝批判的存在。在报告文学的历史传统中,批判性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许多作家曾利用这种武器猛烈地对旧世界,对假恶丑的对象实施了攻击;也对自己队伍中的污垢行为及各种陋习弊端进行了有力的枇判,从而使报告文学的战斗力和影响作用大大加强。读者也许记得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在这部描写当年中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基希叙述纱厂童工的苦难悲惨生活;描写日本人统治下的上海“吴淞废墟”情景等,在一神深情的痛苦中对剥削制度和侵略者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时人称基希为“怒吼的新闻记者”,就是因为他面对***给人类造成的灾难,面对剥削制度的冷酷无情,面对种族歧视的不公等现象,不断地发出大声的“怒吼”,这“怒吼”是战斗的号角,也是批判的武器。在我国报告文学的历史上,批判性也多为作家所运用。前面提到过的《包身工)、(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之外,还有像叶圣陶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等大量作品,无不都以其鲜明的枇判精神使人们难于忘却。自然,对敌人的批判与揭露,同对我们自身问题的认识与批判是有根本性区别的。每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应当认知并把握好这种区别,从而使批判具备更灵活的方式,更加富有效果。前些年,人们受茅盾先生“‘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这种见解的启发,把那些反映了社会生活中这样那样矛盾、困惑、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称之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因为这类作品,极大限度地参与了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密切了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立即就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浓厚兴趣。在这样的作品中,作家们继承和革新了报告文学的批判精神,以严肃负责的态度面对社会现实,用报告文学的方式承担社会的责任。对于现实生活采取毫不回避的态度,把对于现实生活的描绘与审视判断结合到一起给予多角度的报告,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在那些优秀的作品中,过去较少为人们注意的生活面得以提出和表现;那些人们习以为常但却不应忽略的问题得以重视;那些过去人们自以为认知其实是一种误解的社会现象得以纠正。总之,在报告文学全方位地走向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的时候,报告文学与社会生活现实的瑯汇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肯定与否定,明辨与误识,开拓与守旧,升华与沉落等理性的,精神情感的,行为方式的判断交织在一起因与实际生活现象结合而起作用,构成了一个斑斓纷纭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已成为往事,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来冷静地认识和总结它,但就其阵势及广泛持久的影响作用,任何轻率的判断和结论都会冒一种历史的风险。在运用批判性武器的时候,“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作品不是全都得心应手,行动自如,其间的失误,笨拙情形也不在少数。例如,对某些社会问题描写与认的片面性;在某些判断中严重的主观性;在表现方式方法中存在的贪大求全及不计精简等。但在掌握并运用批判性的过程中,它为报告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