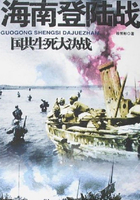悲壮的行为掩盖着军人们痛苦的心灵;进取奉献的精神表现着军人无私的品格。读《瘦虎雄风),这样的情形到处可见。看看描写守备团长躲在零下二十度的兵器室连撒尿时也不敢出来面对一帮讨债人的文字;扫视一下为了每天十五元的报酬被雇用为人看守仓库的战士的身影;揣摸一下怀着不安心情坐在工程投标席下的军长的心情;看到那位为了承包到工程陪人喝酒竟喝到被抬上手术台上的师长和那位战勤科长去大兴安岭发运木材时因无钱送礼几乎变成流浪汉和乞丐的情形;还有更多活动在施工第一线的干部战士们的艰苦状况,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固然困难未能阻止住军人的攻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也出现了像徐恩来、牟玉清等这些似乎具有奇才奇智的人物。可这一切并不能消解这种行动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冲突,使人的不安与困惑得到解脱。
李荃的《中华之门》和王友齐的《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是在另一种形式下反映着军队生活的矛盾现实的作品。当随着国门的洞开而一批批走上边防口岸岗位上的武警战士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威严之气,他们的品格举动时时令人心动。然而,有多少人了解他们所面对的矛盾现实呢!资金设备的匮乏;匆忙的筹建过程;必然碰到的与检查对象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人身后的家庭婚姻子女大事都未能因为国门之洞开而相应得到妥善解决,矛盾不穷,困苦常有。
然而,作为共和国的“门神”,这些战士们尽职尽责,把青春和人生书写在共和国的门楣上。作为测绘兵,自然亲知我们国土的辽阔。然而,他们更是亲身体验着踏尽这辽阔国土时的艰辛和疲惫。他们表现的是种种吃苦牺牲,的精神和品质,但告诉读者的却还有那些本应消除的矛盾和困难。作为人与人来说,边防武警和测绘兵的众多成员,他们是那般的相亲相爱,可一接觖到他们与社会的其它生活,涉及到他们与生活工作环境等内容来,矛盾却是非常尖锐地存在着。对于这些矛盾,有些或许无法逾越,然而,长期地忽略那些努力一下就可得到解决的矛盾,就令人痛心了。
军队生活的现实面貌,在一家刊物中这样集中多样的得到反映,无论如何都是有益的事情。更不必说,编者、作者在反映这些纷宏矛盾的生活状况时排拒了单纯揭露、过分渲染的作法,而是把深切的优患和负责的探求精神结合到一起,进而表现了积极的态度和昂奋的情怀。矛盾冲突;严峻的困难,许多令人不安的现状,都因作家们的这种态度而不再给人以压抑,反而陚予作品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感召力量,并由之透露着推动生活前进的现实动力与转机。失去的已经开始用新的更加有价值的内容偿还了。
谁也不应否认,报告文学创作在这些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样,谁也不必讳言,伴随着报告文学这种巨大变化而出瑰的一些弊端和偏颇。早些年间,报告文学患有软骨之疾,使其中不少作品软弱而带有媚态,这是让许多人不以为然的事实。然而,当报告文学敢于正视社会生活,可以不再气馁地表示自己的性格时,某种强烈的个性化作法又使不少报告文学作家作品流向主观性一方,变得过于专断和固执起来了。自然还有更多地假报告文学之名以营私、追求功名、追求利禄的低级行为了。这-切是令人不安和头疼的。我们不乐意再看到这种失之平衡公正的现象了,可走出一条顺畅的路又是多么的不易!
也许,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种种弊病,最终还是一个如何准确生动地报告社会生活的问题。在我看来,不管是有软骨之疾的作品,还是过分理性主观的作品及那种追求荣禄的玩艺。究其根本,不过是作者如何地把握反映生活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明彻的:在报告文学中,作家理应服从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和本质趋向,而不是简单草率地把社会生活“拉郎配”,借以完成某种失之主观片面的意志。我们完全不必在歌颂和批判之间进行褒贬,因为,失去了真实准确认识和报告生活对象的所有作品都可能是虚浮的,不会使人接受的。窃以为,一篇报告文奈作品的成功,其最主要之点,就在于作家在自己和对象之间找到了一种真诚的,合谐的沟通契机,并有效的把这种真诚,合谐的沟通描写出来。
在我肯定《大势》、《瘦虎雄风》等这儿篇报告文学的时候,并不是以为它们走向了超众绝伦的地步,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我认为这些作品在打通作家与生活对象,生活现实与报告文学作品及读者的联系方面是有一些长处的。可以说,(大势)对于过去的否定是果断而巨大的,它是如此明确地指出过去某种国土防御观念的消极和局限性;那种带有凝固的治军方法的不现实性等重大问题。这种否定何其气魄,何其深重。但是,我们并未因作家的这种否定而感到突兀,并随之产生某种惊诧。原因就在于,作者中夙和作品中写到的不少将军,是站在更高的基点,更加科学进步的地方对其进行了利弊分析之后提出来的。作家作品在这里让读者接受的不光是自己的否定,而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是让你在接受了新的建树之后感到这否定的合理和必要。《瘦虎雄风》几乎是含着泪水书写将士们因为经费短缺而去进行生产经营情形的,作者似乎也并未把这种举动视为正常而根本合理的现象。
但是,对今天的国情和环境能够理解,对军队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作法可以接受并理解,从而就悄悄地使自己的真诚和情感与军队生活的现状汇于一流。因此,杜守林不管多么充分地描绘军队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艰辛乃至血泪情形,可他流露的却不是怨愤,不是屈辱的情绪;而是对战友们的理解,崇敬与激情。虎瘦雄风在,处贫威严存。作品中许多流溢着悲壮色彩的描写,非旦无损于经费拮据环境中军人的形象和品格,反而使这种困窘的现实生活成为陪衬军人强盛生存能力,应对非战争生活困难的机会和背景。虎瘦本当惜,雄风自可嘉。因为作者的智慧,使背负艰难的军队现实图景其冷峻而不失之悲怆,昂扬而不致于轻松。至于(星辉》的作者张嵩山,《脚踏着祖国的大地》的作者王友齐及《中华之门》的作者李荃等,他们或歌或愤,但都把一汪深情,一片爱心献给了我们的军队,献给了千千万万个前线官兵。
虽然多有痛苦和惆怅,但终不过是爱之愈深,望之愈切,带着内在的温情和急迫的心绪罢了。我不想肯定这些作品中,那一位作家所采取的表现方法更好,尽管它们确有差异。报告文学是一种需要作者不断调节自己而适于客观事实、题材对象的一种文学形式。决定其成败的不应完全是作家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可以去肯定某一篇具体的作品,却不必在整个创作中树立一种典范,因为让他人放弃自己的优势而趋向典范,这对选材,对写作都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报告文学的真实对象只有一个。这种极端的限定性决定作家不能超过对象?依归任何一种典型。
在当前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我把自己的热情和爱意投向这几位作家作品,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依归了那些成功的范例,而是在于它们所报告描写的军队生活强烈地触动了我。除去这主要的一点外,在表现的方式方法上,我更重视的地方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编者和作家们的坚定的从具体题材内容出发选择道路方法的志趣和行动。他们不去到众多的人群中找寻自身,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因把自身汇聚于人群之中而淡化,而模糊,反倒是因为孤独而突出了。
生活的舞台五彩缤纷,文学的剧场也不会永远演出一个剧目。报告文学创作在得到过读者的击掌之后,走向清寂的趋向从八九年就已显示出来了。活跃时的击掌固然不是多余,可清寂时为其再度的出台献策就更是需要了,尽管这十分不容易。
在读过《昆仑》一年的报告文学作品之后,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这些作品是在报告文学创作露出退势时出现的,难道它们的存在和实践,不能给我们思考报告文学创作的今后道路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吗?当然,报告文学的退势已非作家们的一时努力可扭转,可对以往的鉴戒终归不是多余。那么,我以为可作为鉴戒的至少有下面几点:
首先,真诚地从社会生活现实宁发现题材,把对于事实的尊崇置于最高的地位,在真实中求发展,在事实中找寻理性和情感的升华。
对于社会生活的真诚,这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作家作品都应,持有的根本态度。也许可以说,失去了这种真诚,无论是褒是贬,都不可能产生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报告文学是最直接坦率地面对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装假的行为对它来说是致命性伤害。几年来,在数以千万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真诚有力之作不在少数,但缺乏真诚,矫造之作也并非少见。当反映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受到大家重视的时候,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就出现了一些为问题而问题,为理性而理性的作品。在这类作品中,自然不能指责作者完全的无依据,但不应掩饰地是,有些问题确实被作者夸大了,把局部性的扩展成全局性的现象了。
或者说,把偶然性的东西视为必然,看成是普遍的现象了。这种一窝蜂式的创作现象,既掩埋了那些真正反映了实质性社会向题的力作,也同时在创作,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了某些馄乱。这种创作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毫无疑问,问题出在作者对生活缺乏全面准确认识一环。生活中虽然会有许多相似的现象,但即是这些相似的现象也包含着相异的成份。因之,如果作家们在这些相似的社会现象面前稍有忽略,看不到那些相异的部分,甚至主观地使之适应某些既成的观念,那么要求得对生活的准确认识就十分困难了。这种建立在不确切生活现象基础上的作品,自然也就失去了对生活的真诚而流向矫造,不管其作者是怎样的修饰,也无法弥补其致命的弊病。在对生活的真诚态度上,(瘦虎雄风)、《大势》等作品,显然是无可指责的。
杜守林在面对军队生产经营这种行为时所真有的不安情绪;中夙在发现旧的国防观念,战略构想及治军方策在众多将军们共同的冲击修正下有可能成为一种历史现象时的窃喜心态,还有张嵩山、王友齐、李荃他们在那些具体鲜活的军队生活,军人心灵情感面前所流露出的情绪,都会让人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交流情状。这相较于那些缺乏深厚生活基础,而依赖也许是机智的手段去反映问题,人为地升华理性的作品,或许还有迟暮笨拙之嫌,但它毕竟是易为人接受得多了。在我看来,一块真正的石料比起以代用材料制作的工艺品、更富有价值。虽然后者也不妨作为观赏的对象而存在。
其次,树立良好的文风;去掉浮华之气;朴素地报告生活的真面貌。消除形式主义的牵扯,在追求确切描写中创造独特的个性。
报告文学旨在准确地报告和传递社会生活真实对象的状貌和所包含的各种内容。所以,尽管作者可以在这种报告的过程中努力创造某种更富于个性化方式,但这种创造最终不能越过生活对象本身,而变成一种天马行空式的杜撰。在近些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文风恶劣,失于浮华冗长之态的作品日渐增多,读来使人不免厌烦。不适当的运用全景描写手段;片面的追求宏阔厚重的格局;游离报告对象之外故作高深的思考和罗嗦劳叨地卖弄才华,等等现象,都在不同程度地袭扰败坏着报告文学的朴素文风,影响了对生活对象作更加坦诚率真的描写。本文涉及到的几篇作品,甚至也未能完全地排除掉某些冲击波,使自己变得更加个性化一些。
不必讳言,《大势》所采取的广视角与全局鸟瞰的结构是一种适当的选择,作品有宏阔似海浩荡如潮之态。但其中也不乏虚弱铺排的毛病,对少数几位将军的报告就明显的内容苍白而成多余之笔了。《星辉》是以不少精彩片段连缀而成,作为短章不失为佳作;但从整体角度视之,就不免有松散牵强之弊了。因为它缺乏像《大势》、《瘦虎雄风》那样有一个可以连起各面的内核。抓住内核,辐辏八方,互为效应。《中华之门》的内容真是厚重丰富得很,可惜作家的报告似乎过于铺排平实,以致使人有冗长杂乱之感。我之所以这样直言这些作品之疾,当然知道它无损于作品的整体风貌。自然,一篇作品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远不能说明它的文风如何!但这些缺点若是对别的作品同样缺点的重复,那就不妨从文风面分析一下了。
报告文学的个性风格是自作家的选材开始就发生作用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单从形式上看问题,简单地去模仿别人,硬要把一个池塘扯成一个深沉宽阔的湖泊;强行地让一位本可能单纯地人变得复杂起来。认为作家的主观可以左右对象,形式可以改变对象那么就只有深陷到形式主义中去,而难求个性特色了。我们的报告文学看似眼花缭乱,细分不过几类。
为什么各不相同的社会生活对象在作家的笔下竟变得类型化了呢?原因或许就在于作家写作时无意中抹煞了对象的特点而使其服从了作家自己对某种类型作品的爱好了。多年前,笔者访问小说家陆文夫,谈起他作品的风格。他说:别人说我的小说有别致的风格,问我是何以造求的。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知道,我忠实地描写了生活人物。是这些相对稳走范围中的人物的生活及行为,促成了我小说的持点。风格不是追求来的。而是在忠实于生活的描写中自然形成的。这些见识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或许更有启发。不必对某种成功的形式表示过多的热情,还是更加深入地去认识、表现你所要报告的对象吧!
再者,放弃世俗的兴趣,高扬文学的纯洁品性,使报告文学脱离庸俗的泥沼,展露其庄重的容貌。
不知由什么时候开始,报告文学这种原本严肃庄重的文学形式,竟被少数人用于满足自己和他人世格兴趣的浊流中去了。写一点名角的寓言轶事;描绘一些带色的性爱情节;说说玄妙的人情世态或为人鲜知鲜见的畸型人与事。大有搜尽神州,为求一异的状况。在此种风潮来临的日子里,报告文学创作被污染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被少数人当成了钩起读者兴趣的诱饵。真令人为之痛心,为之叹息。更有甚者,报告文学被有的人视为树立功名、追求利禄的工具。商业性的交流冲撞着报告文学纯净的面容,有时竟把它涂抹得十分丑陋,搔首弄姿,媚态可掏,令人无法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