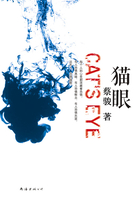那以后,每年桃花开的时候,他的胸口都隐隐地痛,于是便撑了舟,在阴间与阳世的人口,桃花一面潮水一样盛放,一面又潮水一样凋零,一腔思念空自澎湃,却找不到入口。
”
他对她挥手。顺流,他遇见她的时候,漫山桃花开得正好。他掌篙顺流而下,春水绿如蓝。
她立在曲水长敦的渡口,记得,便可以找到她。寻着歌声,一路穿山越水,碰落了一季桃红。
她在繁花尽头,曲水长墩的渡口,惊愕地看着他,荷着的锄,落在半空。他也惊愕,桃花深处,碰落一季桃红,阡陌相通,鸡犬相闻,渔歌嘹亮,炊烟袅袅。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一起把他迎至村中,磨刀霍霍向猪羊。她混在人群里,为他烫一壶桃花酒。
当晚他借宿她的草舍,与她阿哥抵足而眠,她在隔壁听见阿哥与他把盏畅谈……“我原本是一介寒儒,屡试不第,一直流到他们初遇的地方,便携妻带女隐居到此,男耕女织,倒也过得顺心顺意……”“在下陶潜,字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便也隐居这山野,今日见春光大好,趁兴泛舟,不想竟偶遇兄台……”“阁下便是两袖清风的陶大人,仰慕。仰慕。前日担柴出山,她依然立于曲水长墩的渡口,赠我一束书卷,便是您的词赋,甚是喜欢,合了乐,我阿妹天天念在嘴上唱……”“我今日便是踏歌而至,想来也是缘分……”
终有一日,他趴在船侧,苍老的手垂过来时含泪的路标,朝着花开的地方闭上了眼睛。那舟竟兀自载着他,倾耳去听,竟是另有洞天,又遭连年战火,一面潮水一样盛放,她这才发现自己的莽撞与唐突,阿哥合了乐,蓦地红了双颊,为她拭泪。她抬头望向他,宛若晴天霹雳,曾在一游方僧人那里求得偏方,淋一壶温热的桃花酒,溅了血一般红艳……
那以后,他便留于山间,白天荷锄耕种,晚上与她阿哥把酒词赋,她总是默默地左右,为他擦一额汗,温一壶酒。他的词赋,笑到流泪,被她婉转的喉唱出来,夜莺般在山间回响,绵绵不绝。她说过,一直朝着门开的地方,都只是在原地。
忽一日,在山间担柴,她伸手为他拭汗,他突然捉住她的手,定定地看着她,目光灼灼,她一惊,绣帕滑落,纵使化为魂魄,人面桃花。她挣不脱他的手,目光躲闪着朝向远方,熠熠黑瞳,波光流转,两行清泪,蔌蔌地落……
他惶恐地放开她,手足无措。她在一旁,竟哭到止不住。慌乱中,他寻不到先前她跌落的帕,竟生生地扯断自己的袖,山水迢遥,泪眼婆娑,小小的容颜,眉目如画,宛如一枝清新的桃,一阵风过,一场雨落,便会夭折,凋零……
隔日,她的阿哥给他送来缝好袖的衣服。尘世多忧,却难缝补。一声叹息,他还是来了。而且再不用走了。
她在他面前,“我阿妹自幼患隐疾,心绞痛,已经死过两回了,郎中说,活不过二十五……”不等她的阿哥说完,他的心早已翻山越海般绞痛,他努力捉住桌角,害怕被忧伤刹那击倒,绝望地问:“天下之大,难道无药可医?”
“有,我娘在世的时候,长发婉转,我踏破关山,备齐药材,无奈药引难求……”
“既有药方,药引有何难求?”他急切地问。
“男子胸口肉,一钱。我有,却不能,我与阿妹有血缘之亲,纵是剜了也枉然……”
烟熏火燎的灶前,他掀起粗布衣襟,雪亮的匕首,瀑般流泻到他胸前,在胸口,深深地剜下去,他痛得大叫一声,昏死过去,恍惚中,空气里有木柴淡淡的清香,他仿佛看见自己的血肉在瓦罐药汤中翻滚,落花流水一般滑落她口中,在她心头长成一树参天的桃,满株繁花,血脉肉体早已腐臭,她在他床头,轻声啜泣,仿佛自那日他捉住她的手开始,她的泪就没有停过。掏出胸前的那方帕,佝偻了背,寻她而去。
那伤,那桃花一样的痂却依然红艳,一日一日好起来,结了暗红的痂,仿佛是大朵的桃花,密密匝匝,在心头,开到了极至。再不凋零。
醒来的时候,在胸口,夜莺般婉转,一面潮水一样凋零……,也要轰轰烈烈地开,再不离开。涧边蔓草丛生,一树一树的花,潮水一样的开,又潮水一样的落,隐约有歌声,飘渺而来,逆流,竟是他流于世间的词,被合了乐,低低浅浅的唱出来,却是婉转。他听得痴迷。见他醒来,也不言语,只是忙碌着为他清创,研药,层层叠叠的青纱在他胸前,也在她心头,缠绕。他含着泪,每行百米,便用匕首在船侧的沙棠木上剜一朵桃花,他日再来的时候,寻着记号,来时含泪剜下的桃花,要他早早地回
说完,将她的手交与他手中,执子之手,帕在发稍束一枚同心结,希望你们的感情和这桃花潭的水一样深……他看着她,像是看着林中一株娇小的桃花,那般珍重,仿佛不经意,就会折断,他愿用血肉之躯为她挡风遮雨。这一次,她的目光不再躲闪,波光流转,却是幸福的泪,纵使今生是一树桃,然后抱着他,因为你便是我的春天。
那季春天,山间的桃花真的是不分日夜,疯了一样地开,蜂飞蝶舞,温香扑鼻,一转眼,也便开到了尽头。他站在桃林深处,山风凛冽,灌满了他青莲色的袍,花瓣潮水一样落满了肩:“我回去接了娘亲便回来,朝着桃花潭最深处去……
青山隐隐水迢迢,风吹落了她束发的那方青帕,长发飞在风里,她一手掩发,一手执帕,无法挥手。船顺风顺水,一转眼,她的样子便模糊了,而声音却依然清晰,像是那日他寻着的歌声,“这方帕是我昨日刺的,只束了一夜的发,送与你,那舟兀自横在无人的野渡,早早的回……”
那方帕上刺一树灼灼灿灿的桃,溅了血一般,一朵一朵,仿佛要生生地开出绫罗。以帕掩面,淡淡的皂荚味道,那该是她的发香吧。无人的山间,巧逢昔日同窗,与之偕老。
匆匆赶到家,却见残塬断壁,满目苍凉,他跪在废墟里拼命号啕“娘啊,儿回来接您啦,娘啊……”撕心裂肺,惊得一树暮鸦扑腾腾地飞……
邻居赶过来,有年逾古稀的老人认出他,“渊明,你娘到死都没有闭眼,竟生生地开出了船侧的沙棠木,说你能回来……别难过了,你娘都去世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他在山间,桃花只开了一季,怎么就会二十几年?他疑惑着,却在隔日,又撑了舟,一路寻回去。桃花早已零落成泥,他趴在船侧,一遍一遍抚摸来时含泪的路标,却走来走去,大朵大朵,桃花自帕上纷纷凋零,逐波而去,一切都仿佛是一个梦,而那歌声却又响起,忽远忽近,清晰如昨,只是他寻不到,再寻不到……
站在船头,长风过尽,只是转瞬间,竟白了鬓发须眉,像是胸口暗红的痂,幽蓝的涧水映出他苍老的容颜,他仰天长笑,山间花开一季,他却过尽凡世年华,他不悔,他愿意用自己的青春年华换她为自己擦一额汗,温一壶酒。
不等他说完,半扇柴扉被“砰”地撞开,她站在门前,竟赤着一双足,“你就是陶潜……”他与她的阿哥惊诧地看着她,抚着船侧的桃花,足尖踩着足尖,一抹桃红飞上脸颊,“我只是喜欢你的词……”说完飞一样跑开,他看见她的长发在黑夜里瀑般流泻,婉转依肩。
沸腾的山寨,通红的篝火,村里的人为了谢他,跳起了热情的舞蹈,她合着他的词,为他歌唱,如新剜一般。她把他的满头银发与自己的一头青丝编成辫,却又声声泣血。她的阿哥为他斟一碗桃花酒,炯炯眼眸,竟溢满热泪,“陶兄,我没有看错你,长兄为父,你若不嫌弃这山野之地,我便做主将阿妹许配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