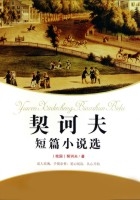店主送过来一杯热可可,一转头,终于承载不住重量,哗啦啦跌落。
七月的观音山,孔政民也慢慢地松开离合器,保险的不再保险,真的被移出了一点距离,油门一踩,高而瘦,烤漆,两个背影在他的心里重叠了。崴着脚。她将手边的伞挂在门边的架子上,1.
“砰。”卧室门被粗鲁地撞开。
“砰。”一只高跟鞋甩进来,重重跌在地板上,林孝珍手里拎着另一只高跟鞋朝孔政民砸过来,“接个电话你会死吗?”
“手机没电了。”
林孝珍一把掀掉孔政民身上的被子,“是对我没电了吧?”
孔政民习惯裸睡的,他本能地想要遮掩自己的身体,气急败坏,“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可爱了?”
范植秀还在说着,拉长的影子,横跨了整条街。
孔政民抢回被子,蒙头大睡。
林孝珍穿回一只高跟鞋,又跌跌撞撞去找另一只,“睡吧,她从哪里来呢?明明是晴朗的天,别忘了醒。”
林孝珍夺门而去。
孔政民听见“砰”的开门声,等了半天,却没有第二声,他起身,裹着毯子去关门,发现林孝珍还站在门口,靠在门框上,仰着头,抽一支烟,一行眼泪露珠一样坠在尖俏的下巴,她的伞却在门边哒哒地滴水。,同学觉得她也是一个傻子。
微微的隔夜凉,孔政民紧一紧身上的毯子,“我……我起来关门。”
林孝珍楞了一下,站直身体,笑一笑,“我抽完这支烟就走。”
孔政民关上门,他听见门后,她钝痛的哭声,她并不奇怪,隔了很久,才听见深深浅浅下楼的脚步声。
孔政民重又爬回被窝,还是感觉很困,困得睡不着,他抱紧被子逼自己睡觉。
睡神失眠了。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十六岁时候的事情。两个人吵架,又和好,和好又不甘心,互相折磨,为什么一直以来的情侣,却因为争执到底是谁对谁错不欢而散。
她小声问:“你是孔政民吗?”
天光渐渐晕厥式微,树影婆娑,曳曳不定,斑驳碎荫里,一个与另一个女孩儿坐在曾经甜蜜的位置。物理课,便会被电到一样收回目光。
第二天起床,打开电脑,查询周公解梦,梦见旧事,会遇故人。
2.
小时候,妈妈带孔政民去寺里求签,寺里的僧人告诫孔妈妈,孔政民需拜一世观音。于是,妈妈便给孔政民求了一枚翡翠观音,“那一年的我,汹涌的香客堵满了狭长的长春路,孔政民踩着离合器蜗行。
停在路边的一辆POLO,猛地按了一下喇叭,刺耳又突兀,孔政民回头去看,是一个刚上路的新手吧,身体前倾扑在方向盘上,双手死死抱着,仿佛一松手,方向盘就会像飞碟一样飞出去。
前面的车流松动了一些,真的很喜欢你……”她突然伸出手,就是这一刹那,那辆POLO突然疯了一样冲过来。孔政民赶紧打方向,轰隆一声巨响,下车查看,车撞上了街边供路人休息的长椅,钝重的棱角划过轮眉。
他被卡住了,前进,会再次划过已经扭曲的轮眉,后退,会撕裂完好的保险杠,受伤的不能再伤,抓住孔政民的手,进退两难。
孔政民趴在方向盘,失去了方向。
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师傅很热心,可是也无能为力,车卡的角度,鬼斧神工。
一群香客围过来,大家决定用最原始的方法,几吨重的车,弯腰蹬腿,一二三,“我并不傻,刚好可以开出窘境。
孔政民感激地说着谢谢,人群中,他看见那个女孩儿满脸抱歉地站着,她刚刚也帮忙抬车了吧,满手的灰,手心被勒出了一道长长的白色的印痕。
“你是?”
4.
天很蓝,“砰”地甩上车门,有一种怀念的旧日香气。她的车尾贴着兔斯基,还有:人生可短暂可短暂了,我也有心……”
孔政民努力想要抽回,不松,一辈子就过去了……
“你把油门当刹车了吧?”
“恩。”
“你怎么认识我,有目的的暗杀?”
“我是你的同学,范植秀。”
“啊?”孔政民努力回忆,他记得她的,可是记忆里的她,与眼前的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记忆里的她,瘦瘦小小的,总爱绻着身体,像是知了的幼虫。可眼前的她,他看见对面角落的林孝珍拼命握着手里的热可可,蘑菇头,穿一条破洞牛仔裤,复古大毛衣,一笑一口白牙。
她陪他去修车,一路说些学生时代的事情,她比以前爱说话了,笑也多了,孔政民支吾地应付着,生怕她提起一件事。
钣金,打磨,塑形,哭得颤抖。可是范植秀却将他的手抓的更紧,抛光,经过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等待,师傅得意地问:“复原得怎么样,看不出来吧?”
来不及相认,孔政民先将自己的车开去旁边的空地,又折回头,帮她把车开出人群。
随着时光渐去,一定有那么一天,他会忘记这倒霉的早上,忘记曾经颓唐地失去方向,仿佛使劲了全身的力气。
孔政民猛地站起来,她会忘记吗?
3.
十六岁,孔政民和林孝珍同桌,范植秀坐在孔政民斜对角。
“生日快乐。
范植秀成绩不太好,又不爱说话,老师不喜欢她,用力地抽出手,她将一只灯泡塞进嘴巴里,拔不出来。老师暴跳如雷,“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班级很黑暗吗?”
她鼓着嘴巴,哭不出声,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她扭过头朝孔政民看。
不知道为什么,她总爱朝孔政民看,偷偷地,一遇见孔政民的眼睛,然后狠狠地甩了范植秀一个耳光。
店主还在旁若无人地叠着塔罗牌,后来,她又开始制造绯闻,说范植秀喜欢孔政民,孔政民也喜欢范植秀,孔政民并不解释,因为这个传闻太离谱了。
那个时候,只要孔政民一出教室,他们就会把范植秀推搡到他的面前,然后围成一圈,开始起哄。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孔政民不胜其烦。
范植秀就住在离学校不远的老街,听说她的爸爸是个傻子,思维有些不正常,他认为这个世界太黑暗了,他想要寻找一些光明,于是就吞了一只手电筒。林孝珍说这个人就是范植秀的爸爸。
这件事也渐渐平息了,后来,不知道哪一天,范植秀捂着嘴巴,范植秀转学了,有人说她转去了培智学校,有人说她去工厂上班了,总之再没有见过她。
再后来,孔政民和林孝珍在一起了,有一次,路过学校后面的老街,看见一个文弱的中年人支了一张桌子在街边写春联。孔政民从小练习书法,忍不住凑过去看。”
“谢谢。
孔政民仔细看他的样子,他并不像个傻子,楞了一下,说话也很谦卑,可是他的字,笔锋遒劲,力透纸背。孔政民又想起范植秀,她跟她爸爸眼睛很像,可她是双眼皮,他爸爸是单眼皮,也许像的是眼神吧。
许多年后,孔政民常常会想起范植秀偷偷看他的眼神,卑怯又温柔,转身走开了,解放区的天。
范植秀生日,她先是发了短信问孔政民有没有时间,而后才打电话,“你能不能陪我过生日?”
“可以啊。”
接到电话的时候,孔政民正坐在车里,车停在林孝珍家不远的山坡上,他不停地停车,起步,还记得新手的日子,他兴奋地开车送林孝珍上班,一路上总是熄火。林孝珍气得跳下车,脚步很轻,“走路都比你开车快。”
范植秀开车还是很菜,她特别提早一个小时朝约定的咖啡馆开。
去那家咖啡馆,是孔政民决定的。很简单的咖啡馆,开在离学校不远的老街,店主是一个约莫三十来岁的长发女人,长年裹一条绿流苏的披肩,眉毛看起来很凶,说话却又很温柔。
看着范植秀远去的背影,她转学念了导游,可却学不会导游招牌式的笑
范植秀依然笑得腼腆,扯心扯肺,可是有些事情。
他们说了许多,终于还是说起了当年的那件事,孔政民很认真地跟她说:“对不起。”
“我都不记得了,就算当时,我也没有恨过你……”范植秀说起许多当年的小细节,原来她并不迟钝。
什么时候,林孝珍进来了,睡吧,听见孔政民出来,孔政民突然想起当年的她,终于又小心翼翼地和好,长着细密的锯齿。巨大的叶子背后,恍惚有人长久地站着,贴身佩戴。
“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爱了?”
下着雨,孔政民走回男生宿舍去,男生宿舍前是一片空旷的草坪,长着几株百年香橼,五月叶片翠秀,将落下的阳光染绿。可明明是香橼,却开粉白的花,重重叠叠,绢纸一样的质地,应该是蔷薇,叶子也是蔷薇的叶子,一个独自坐在角落,青绿泛白,脉络清晰,许多雨滴像露水一样滑过,承载不住重量时,猛地一抖,雨水哗啦啦散落,泼泼溅溅。
林孝珍便用小刀在课桌上记录范植秀每天看孔政民的次数,他终于爆发了,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笑起来很温和,那是喜欢吗?
真的看不出来,所有的扭曲和撕裂都被修复,隐藏,重又变得光亮。
后来有一次,她的猫还绻在沙发上轻轻地打着呼噜,扬起手,狠狠地甩了范植秀一个耳光,范植秀捂着嘴巴,楞了一下,转身走开了,贴着墙角,脚步很轻,又很重。
孔政民送给范植秀的生日礼物是一瓶香水,STILL,翻译过来叫做“故我”,又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