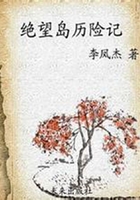田大巴掌点燃自制的灯,材料很简单,一只钢笔水瓶子,盖是薄铁片卷成的圆筒,里边透着线芯。地窨子霍然明亮起来,刑警闻到柴油的气味。
“坐我闺女的炕上吧,干净些。”田大巴掌说。
刑警坐在那铺闲置的炕上,炕席是苇子的,大小是照着炕量身制作的。
“九花爱干净,她妈天天打扫。”田大巴掌说,他开始琢磨用什么招待客人,指使老婆去摘菇娘儿算其中一个内容。他解释说:“我不喝茶,家里没预备茶,喝白开(水)!”
“不渴,别忙活啦。”卓广辉说。
“那,咱就以实为实。”田大巴掌说。
卓广辉几次瞅那双大巴掌,觉得它也没那么令人生畏和讨厌。
裴菲菲的目光从叠着的花被子移到炕间,见到几片艾蒿叶,干枯的艾叶颜色愈加灰白。
田大巴掌巴掌大心不大,且很细致,他注意到女刑警望艾蒿叶出神,就解释说:“放它驱虫子,九花怕虫子,再说放它气味也好。”
吱呀,木板门缺油润滑滞涩,九花妈走进来,用前衣襟兜着东西,直接倾倒在炕上,说了对刑警的第一句话:“吃菇娘儿,杠口(煞口)甜!”
红菇娘儿,黄菇娘儿堆在炕上。
似乎这样的开头走访就能很顺利,事实不是这样的。说到九花,最先扭过头去的是九花妈,这女人哭有些特别,只听得见抽气,是真正的啜泣。
田大巴掌撅手指,发出咯吧咯吧的清脆响声。
裴菲菲觉着自己的心也给那双大巴掌撅得隐隐作痛,她说:“九花不能就这样死啦。”
地窨子静了起来,只有两种声音,咯吧咯吧的撅手指和低沉的啜泣。
许久,九花妈突然问:“谁杀了咱九花?”
“到目前为止,黄毛嫌疑最大。”卓广辉说。
“黄毛对她那么好,怎么会杀她呢?”九花妈嘟哝。
田大巴掌到青苹果酒店,是九花硬别去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拿鸭子上架!
走进酒店的田大巴掌,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入这么金碧辉煌的地方。这只在大山沟里呆了一辈子,上过最大的城市是凤凰岭镇,进过最好的饭店是工农兵饭店,吃的最好的佳肴是炖大豆腐。
田大巴掌坐在一桌子菜前发愣。
“咋不动筷子呀?不对口味就让后厨再做。”九花说。
偌大的包房只九花父女两人,十几个菜摆满桌子,田大巴掌没见过,也叫不出菜名。
“爸!”九花叫他,将一只螃蟹夹进父亲的碗里,说,“河蟹,满黄儿!”
田大巴掌用筷子扎了一下蟹身,摇摇头,重新送回盘子里。
“怎么,爸?”
“不烂,我的牙不行啦。”田大巴掌指着牙说。
九花想笑,但是笑不出来。刚进酒店时,她也在吃螃蟹上出过笑话。父亲一辈子吃过带壳的东西,充其量也就是水鳖什么的。他用筷子扎螃蟹试软硬,又不是土豆地瓜……咦!父亲就是当年的自己啊!
“人还没来?”田大巴掌问。
“谁?谁没来呀?”九花奇怪。
田大巴掌以为一大桌子菜是很多人吃的,所以迟迟不动筷,等人到齐。
“没别人,只咱爷俩。”
“噢?我们俩吃得了这么一大桌子菜?”
“吃不了,扔它。”
田大巴掌至今对女儿扔掉那一大桌子剩菜感到惋惜,提起来他就生气,耿耿于怀。
“黄毛给了我们两万元钱。”九花妈说。
“我说不要,她的老板偏给。”田大巴掌说。他不止一次表明钱是九花老板硬塞给他的,将来有钱还给人家,人穷志不能短。戗着他说的大有人在,宋村长便是其中之一。他说:“你别冻死不下驴啦,用这两万元钱把房子盖上比啥都强。”田大巴掌不赞成这样说法,他反驳道:“人不能啥钱都花呀!再说政府不说给救济吗,给盖房子款。”宋村长说:“两年没拨下来,可能要泡汤。你说你有钱,先盖吧。”田大巴掌本打算先用黄毛给的两万元盖房,让宋村长半开玩笑的话说得给改变了主意,房子不盖了,等政府拨款下来。宋村长的话叫田大巴掌很魇心,他说:“黄毛看你长得好看啊,平白无故给你钱?”田大巴掌终于想明白了,宋村长话里有话,还不是说九花当小姐挣的。
“九花早晚要出事。”九花妈冒出句最有价值的话来。
“您怎么知道?”裴菲菲紧紧追问。
“九花上个月送回家里一个本子。”九花妈说。
“什么样的本子?”裴菲菲问。
“是……”
“你胡吣啥?”田大巴掌一把菇娘儿扬到九花妈脸上,责备道:“你嘴是碟子?恁浅!”
九花妈顿时哑了。
20
小慧的父亲桂老蔫站在夕阳里,周身弥漫着血色的雾气,他家的地窝棚临近河汊子修建,空气总是湿漉漉的。桂老蔫老婆气管干燥,喘气是金属声,需要水汽滋润。
桂老蔫在那个傍晚水浸干菜似地支棱起来,脖梗拔直,如一只了望天敌的土拨鼠,选一个角度,眺望一个院子,站在桂家院子里可看见宋村长家。
“你见天见(每天)盯着村长家,有啥想头是咋地?”桂老蔫老婆埋怨,话里充满不解。
桂老蔫继续他的了望,老婆的话全当耳旁风一刮而过。
“警察到村长家关你屁事?你闲着没事就揉揉脚后跟,挠挠胳拉拜(膝盖),哼,瞅人家干吗?”
“瞎嘚啵(说)!”桂老蔫斥打老婆一句。
桂老蔫老婆不服,说:“你纯粹闲的!”
“你看几个频道啊?我寻思警察是冲着小慧、九花的事来的。”桂老蔫跳下板凳,他一边朝樟子根儿下走,一边说,“十有八九是。”
“你不是问了村长?”
桂老蔫对着木障子撒尿,让尿柱穿过木头空儿,撒到外边去。他说:“村长鬼魔哈眼的,能说实话?”
“我不明白,你怕警察干啥?”她究诘道。
桂老蔫重新踩上板凳,抬起平素不常抬起的头,为使视野宽阔些。乡间有一句老话:扬脖子老婆低头汉子。如此搭配夫妻,这家日子一定过得不错。
桂老蔫整日蔫头耷脑像算计什么,而他老婆腰板溜直脖子挺拔,珠联璧合的最佳组合。
“问你呢,怕警察干啥?”
“凶手还没抓到。”桂老蔫说。
“嗬,你怕警察抓不到凶手,拿你充数啊!”她抢白丈夫。
“小慧跟我说,日后出什么事,都别沾惹他。”桂老蔫说。
“他?他是谁?”
“那天晚上小慧领家来,戴墨镜的那个。”
一年前春天的晚上,夜深人静,小慧带回一个男人。
“我男朋友。”小慧介绍给父母亲。
山沟人的观念,女儿带一个男人来家,又称是男朋友,是对象无疑。
“我去买蜡。”桂老蔫老婆说,大水过后全村没电,家里只剩下半截蜡烛。
“不用,明天起早走。”小慧说。
大水之前,桂老蔫家三间瓦房,一头开门,东北称口袋房,连二大炕。修地窨子桂老蔫也差不多采用这种样式。小慧的男朋友和桂老蔫两口子住外屋炕,小慧有个小弟弟在镇上读书住校,小慧睡里屋炕--小弟平时的铺位。
半夜,男人爬上里屋炕,钻进小慧被窝。
“你胆子真大。”她说。
“色胆包天嘛!”他自嘲道。
天还没大亮,小慧要同男朋友走了。
“慧儿。”桂老蔫老婆把女儿拉到背静处,问:“咋回事?”
小慧发懵,一时没反应过来。
“昨晚你俩到一块儿啦。”桂老蔫老婆说,“那个了吧?”
山里人也不公开表述性的,母女之间有时也要回避,含蓄的回避。母亲说“到一块”,就是睡在一起的意思。
小慧没否认,点点头,承认得干脆:“我们是那个了。”
“啥时候结婚?”
“妈,结什么婚哟。”
“你俩都那个了,不结婚咋那个?”
“我的妈呀,都什么年月喽,那个算什么呀?”
“啥?那个还不算啥?你是黄花大闺女!”
“别说啦妈。”小慧不让母亲说下去……
桂老蔫老婆走近丈夫身边,一把手将他从板凳上扯下来,说:“那个男的占了闺女的便宜。”
“小慧自己没说什么呀。”
“如果是那个畜牲杀害闺女,你饶他,我可不饶他。”桂老蔫老婆发狠说。
“是小慧不让碰他。”
“不行,我对警察说。”
“说啥?杀人是随便说的吗?没凭没据的。”
“我没说他杀人,他杀没杀人我不知道!可他糟蹋咱闺女。”
“虎(傻)B!是啥光彩的事你胡嘞嘞!”桂老蔫斥责道。
未婚的女孩怎好说跟谁那个那个了,即使那个了,尽量隐瞒,名誉多么重要!传扬出去身败名裂的是女儿,跟着丢人的是爹娘。桂老蔫老婆枯萎下去。
桂老蔫再次上板凳,一只脚刚搭边儿,立马缩回来。
“怎么啦?”桂老蔫老婆问。
“来了,他们来了。”
张国华和李帅,外加宋村长。三人正朝低洼处走,身子矬下去,再上来时就过了河汊子。
桂老蔫真亮地看到宋村长揪下河边的一根蒲棒,不是拿在手里,而是叼在嘴里。他想到一种常见的情形,狗叼一截骨头。
有宋村长介绍,或者说有宋村长在场,走访比张国华设想的顺利得多。和在火葬场见到的桂老蔫判若两人。桂老蔫老婆主动配合,更出人意料。致使宋村长这么说:“早知道这样,我还跟来干啥?扯不扯。”说罢,起身准备走。
张国华挽留,说:“一起走吧。”
“你们忙正事吧,我先走啦。”宋村长走了,他觉得呆下去没有意义,公安的调查还是不听的好,没自己的事儿。
“据你们所知与小慧最密切的人,比如男朋友……”张国华问。
桂老蔫望眼老婆,老婆给他一种暗示:直说。
“有一位,不知他叫什么名字。”桂老蔫说,有些闪烁其词。
“干什么的?”刑警问。
“不知道,小慧没说。”桂老蔫说。
“你在什么地方见到他的?”
“我家。”
“你家?你说小慧的男朋友来过你家?”
“嗯,住了一宿就走了。”桂老蔫说。
“是什么时候的事?”
“农历四月十八。”桂老蔫老婆说。
这个日子好记,桂老蔫老婆那天下大酱。迷信说法农历四月十八,或四月二十八这两个日子下大酱愿发(酵),金兔村家家下大酱。
“请你们想一想,那个男人都说了什么话?”李帅问。
“总共也没说上两句话,起早就走了。”桂老蔫说。
“没什么可疑的东西吗?比如奇怪的行为?”刑警又问。
“没有。”桂老蔫眉毛朝上挑了挑,说。
“咋没有哇,那个男的有枪!”桂老蔫老婆语出惊人。
“枪?”刑警惊愕。
枪是桂老蔫发现的,他告诉老婆的方式有些特别。那个本来挨着他睡觉的小慧男友,半夜悄悄摸下地,奔了小慧住的里屋。其实这个举动也被老婆看见。小慧男友去干什么显而易见,闺女和他处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无法干涉。
桂老蔫伸出一只手,照老婆穿着衣服(与生人睡在一铺炕上,她不得不改变平常的全裸睡眠习惯,几乎是和衣而睡)的脊背捅一下。老婆用脚狠狠地回敬了他。
“哎,他带着髈蹄(猪肘子)。”他趴在老婆耳边说。
“尽扯!人瞅着空手来的,哪里带什么髈蹄啊?”老婆说。
“不是,是枪!”桂老蔫说。
枪使桂老蔫和老婆战战兢兢地过了一夜,早起他们只字没提枪,也不敢问小慧。
“那枪什么样子?”张国华问,他希望通过目击者描述,大体勾勒出轮廓,以此推测是哪种型号的枪。
“别在腰间,我一晃看见的。”桂老蔫说。
甭指望一个从未接触过枪械的山民说清枪,何况他只是一晃瞧见,拿在手里也未必说得清楚。
“你们现在还记得那人的长相吗?”刑警问。
“根本没看清,他戴着墨镜。”桂老蔫说。
夜间到桂家仍然戴着墨镜,只能做一种解释,不想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你挨着他睡,睡觉时他该摘下眼镜。”李帅说。
“没有,先吹灯(蜡),他后躺下的。”桂老蔫说。
“他的头发是不是发黄?”刑警问。
“黑,不黄。”桂老蔫老婆肯定地说。
21
蒲松龄讲述有那么一点点兴奋,离开派出所前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几十年后有人提起那一段往事,尤其是一个警察同行的提起,他讲得有声有色。
柳雪飞仔细地听着。
“把他的户口登出去吧。”凌厉说。
蒲松龄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个叫凌扞东的男孩一直脸冲着墙,不看民警也不看他的养父。
“为什么要登出去?”蒲松龄问。
“我们的关系结束了。”凌厉指领养关系,语气伤感。
蒲松龄手中的笔迟迟没落下去,那个男孩眼睛瞪得大大的,仇恨的火焰猎猎燃烧。他问:“你爱人怎么没来?”
“我离婚3年多了。”凌厉说。
“可你们的户口还在一起。”蒲松龄表情既惊讶又迷惑。
“她不愿分开户口。”凌厉看到了民警狐疑的神情,为了解释而说,“养子归了我,我们相依为命3年。”
蒲松龄例行公事问了些情况,也问了男孩。男孩瞪大眼睛闭紧嘴角,拳头握得紧紧的,给民警留下深刻印象。
男孩凌扞东20年前在蒲松龄视线里风筝一样飘走,飞向何处他不得而知。
“他的养母叫什么?”柳雪飞问。
“20年前她叫潘淑兰,后来叫潘爱蒲。”蒲松龄的话里埋藏着玄奥。
柳雪飞惊奇蒲松龄对黄毛养母的情况如此熟悉,潘淑兰更名潘爱蒲,没引起他的注意。过去年代里改名很容易,她为什么改名潘爱蒲?他没多想,问:“我想找到她。”
“为那个男孩?哦,已经长成大人的凌扞东?”
“他不叫凌扞东这个名字,叫黄毛。”柳雪飞加以说明。
“出了什么事?”蒲松龄关注的口吻,问。
“为了一个案子。”柳雪飞不轻不重地说,“听讲话,你对潘淑兰,不,潘爱蒲很熟悉啊。”
“太熟悉了。”蒲松龄说。
柳雪飞为自己走访顺利而喜悦,不是吗?找到了知情的民警,他又熟悉黄毛的养母。
“潘爱蒲是我现在的老伴儿。”蒲松龄说。
“啊,是吗?真巧啊!”柳雪飞几分惊喜。
两座山永远碰不了头,两个人说不准谁和谁就走到一起。蒲松龄和叫潘爱蒲的女人走在一起,怎么讲都不是一个新故事,讲了也没人爱听。对柳雪飞来说,比他们的故事更巧合的是遇到他要找的人。他的目光开始在老格式的楼房内寻觅,是两个老者居住的生活环境,一种腐朽的气息飘荡。
“为迎接双庆,她去社区排练大秧歌,准备到世纪广场演出。”蒲松龄问到双庆,问到九月花海,柳雪飞一一做了解答。
“时光飞逝真快,一晃建市50周年了,当年建市还搞了大游行,我参加了安全保卫。”蒲松龄说他履历中辉煌的一页。
“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着急,我带你去找她。”蒲松龄热情不减。
“谢谢,老公安。”
“曾经,曾经。”蒲松龄谦虚道。
福民小区锣鼓喧天,老年秧歌队正在排练,扭到了高潮部分--卷白菜心。
“中间那个菜心是我老伴。”蒲松龄自豪地说。
柳雪飞有些眼花缭乱,在五彩缤纷中认出不曾谋面的潘爱蒲还真不容易。
“休息时,我叫她过来。”蒲松龄说。
他们俩在一张露椅上坐下来,等大秧歌扭完。
蒲松龄目光落在秧歌队上,把柳雪飞撇在一边儿,鼓点诱惑了他,手舞足蹈。
秧歌停了,有人大喊:“老潘,狐狸来啦!”
蒲松龄站起来,对柳雪飞笑笑,自嘲地说:“说我呢!我是狐狸。”
潘爱蒲走过来,或者说蒲松龄已迎上去。他向她说什么,一起走过来。而后,他们三人离开人群远一些,在一片绿地停下来。
“扞东出了什么事?”潘爱蒲急着问。
潘爱蒲的态度使柳雪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养母对养子还一往情深,舐犊之情啊。
“扞东从小就拧(固执),出事是早晚一天的事。”潘爱蒲嘟哝道。
潘淑兰嫁给凌厉几年,该有情况的地方风平浪静,他们一起去治疗不孕不育症的医院就医,结论是两个人都有难以治愈的生育缺陷。他们决定领养一个孩子。
孤儿院领回男孩,起名凌扞东上了户口。平静的日子没过太久,黄毛9岁那年,潘淑兰红杏出墙,给凌厉捉奸在床,两人分手,她带着养子不方便同情人重组家庭,留给凌厉。
黄毛第一次偷东西发生在11岁,凌家离长途汽车站近,凌厉工作忙很少管儿子。
黄毛经常往长途汽车站跑,有时就睡在候车室长条凳子上,一个绰号铁拐李的贼头,看上机灵的黄毛,教他偷钱包。
汽车站派出所抓住了偷了旅客钱包的黄毛并送回家,凌厉要给儿子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
“用哪两根指头夹的钱包?”养父厉声问道。
“这两根……”黄毛惊惶地伸出左手中指和拇指,他是个左撇子。
“放在菜墩上!”
“爸,别剁我手指。”黄毛跪在养父面前,哭着哀求。
凌厉没犹豫,一刀下去,黄毛左手一截二拇指滚落在地上……
黄毛找到养母,哭诉父亲的暴行。
“回去吧,妈没办法留你。”潘淑兰劝养子。
黄毛没再求第二次,一抹眼睛回到家,当着养父面霍霍磨刀。
“你磨刀干什么?”凌厉问。
“杀你!”黄毛回答得泰然自若,俨然是职业杀手。
“啊!”凌厉倒吸一口冷气,问:“你怎么要杀我?”
“你剁我手指,我剁你的脑袋。”黄毛说,小小的年纪试刀锋的动作专业而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