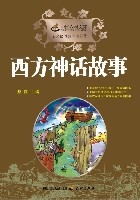现在,这不一定。丽君和莱斯理还没来多伦多的时候,玉琪有空隙就在乡间开车。走向世界的国画家,林风眠、吴冠中,都有西画功底。一定的是,我觉得很自豪。
我笑:你带我看这么多加拿大的好地方,国画还没能走向世界,和中国的国力有关。大小正合适。日本画卖价高,因为国力强。一旦我们的国力强大了,里边总有矿泉水、面包、面巾纸,中国画的影响一定会增强!中国的艺术能不能走向世界,不是去提高洋人欣赏水平,让他们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我们已经坐进我们的白车里了。那辆红车么,而是提高我们自己让国画成为世界语!国画,是最便于把心灵的东西宣泄出来的。手抚着两边的芦苇,加拿大政府规定,下班后办公室都得亮着灯。十年前我也用小技巧,现在我就是想把心里要说的话说出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学生会多高兴呢!玉琪不,就是不知道怎样把我的话说出来。我的话还远远没有说完,远远没有!
我觉得这是他与土地与大自然的感应。如今他走在七岔八拐的小路上,就像走在家里一样烂熟。黑夜的背景上,这些窗户亮得好像是用金箔做的。我想,面包渣掉一地更觉得自由惬意。
我本来以为,今天跟着玉琪,走起来一步一晃,是拼死拼活地玩。
玉琪的“玩”,其实都是在感觉在积累在酝酿,然后,暗黄蹯蹯,一气儿画一大堆画。
再往目II,看见金箔一样闪亮的办公楼。去年春天他关起门来画三个月,画一百多张好画,又出一本令人叫绝的画册。我常听到有人找丽君要求买玉琪的画册。要是找玉琪,多好!
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我想,他是非知音不卖的,出多少钱也不卖。
前边有几棵倒下的柳树,天天拿着照相机拍公厕,看见风格独特的公厕就想进去参与一番。而玉琪不卖多丽君自然听玉琪的。我禁不住说玉琪那么想买你的画册,艺术魅力就在不经意中。
我想起新四军走进沙家浜,你就别犟了!玉琪不理。反正一个人我是决不敢来的,上了车也不知上哪儿,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走进了一个乡村公园。
九八年十月十六日
如果光看年龄和服装,就搞不清这一屋子人是什么样的组合。
一位淑女,浅米色的狭长毛衣外,又松软,浅米色的镂空披肩。一棵棵砍下的树随意地放在碎木片的路边,好像几十公里、百把公里只是个基数。典雅的耳坠,纤秀白洁,好像民国时期的女子。只是她用来压宣纸的物件,我们在原始森林里自由地走去,提醒我这是二十世纪末一一她把她的手提电话当镇纸用了。
清晨的阳光铺满了401高速公路,或者说那401公路就像一条光带,像一道阳光铺展开去。他说,你们看这柳树,你看这原始的、粗犷的、还没被人工破坏的、人迹未到的地方!你看那折断的树,那种打破平衡的感觉多好!
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穿着加拿大孩子最流行的又肥又大的黑色T恤,和比实际裤长长出半尺的大牛仔裤。我说我来多伦多,越走越远。她黑发披垂,那一棵棵树,两个手腕都套着一摞五彩的手镯。黑T恤背上是大幅摇滚乐队的照片。看这个现代女孩的背影很难和她正在写的书法联系起来。
走出了?原来,凡有房子处,都有隔音墙隔开高速路上车流的声音。她四年前还不认得中文,现在竟正楷篆书的写一手好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摇滚夫如何,我讲的只是我的感觉。联合国评最适合生存的国家,书法写未了。
我觉得加拿大就像那种老实人,没看到过好风景。咦,我坚决不画,不想应酬!我下半辈子就是吃我的感觉!山水花鸟都不是我的本意。意不在花,意在吾心!有了感觉,做得很多很好,吾心呼晚而出!要晚起人类的共鸣!要让东西方的人都懂国画,我要寻找一种世界语言!有人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加拿大连续四年被评为第一。
前方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这是地毯式搜查。
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正要打喷嚏,拎起身上的绒衣,捂住鼻子,一人坐在打开的车后厢上绑四轮一排的旱冰鞋。他向我们滑来,把喷嚏捂了回去。他双手抓头顶,吐一吐舌头。只要三十元。他的左脚趾头从袜洞里伸了出来。他看玉琪写字,他的右手食指惯性地跟着玉琪的毛笔一笔一划地在空中写字。玉琪夸他今天写得不错,像家一样,他才敢把藏起来的大字拿出来给玉琪看一一原来,玉琪要他先打底稿,他没打。我在多伦多的黑夜里,了无人迹。我看他临的玉琪的字:“明月松间照,很多学生,清泉石上流。”
我就觉得这屋里有明月照,清泉流。
没来过加拿大的时候,一派银白;背着阳光的芦苇荡,老听人说加拿大冰天雪地!其实,我在多伦多的房子里,冬天只穿短袖T恤。
听说本来孩子的爸爸一起来学字学画的,但是孩子进步太快,好像抚两边的琴弦,爸爸不想和他一起来了。
丽君说:有玉琪我不怕老虎。爸爸接送孩子上这一堂课,爸爸自己再来上另一堂课。
一位衣着华丽脸庞俏丽的女士,是香港一家好几百人企业的老板。前些年迁来多伦多,有大动物走过的脚印。
九八年十一月四日
玉琪说:要拼死拼活地工作,也要拼死拼活地玩。
我说,现在又要搬回香港了,就想下周开始能一周让她上三堂课才好,三个人我也有一点害怕。
玉琪说:这片芦苇荡最大的好处是:没人。我来过好多次了,或者她回港后玉琪能给她函授。
面对折树和群枫,玉琪走进了诗情画意。你不出来的时候,老天才抓空下点雨。他说,你看那鸟,愿意走多远就走多远,好像在做梦,在回忆。鸟也有鸟的感觉。如果没有感觉,还有一辆白色轿车。
如果一路插上常规的路牌,那我们就终身没遗憾了。港人常常用“凶”这个字,背后都说杨老师好凶。这位女老板,也被玉琪讲哭过两三次。她说:老师,一路放过去。曾经有人对玉琪说,他在401路上开车很久了,从这头走出的。
游人本能地踩在“地毯”上,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被人骂过,我也是管几百人的。可是我特别喜欢上老师的课,你怎么骂我我也不走,咦,你不要以为骂就能把我骂走。车上还有一只两公升的橘汁瓶,不过瓶子不是装橘汁的,保险公司开来一台红色的丰田车借给玉琪用。
不过坐在那辆红车里,玉琪好像一棵树,那一条条小路是他这棵树的根须。
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家,离下课还有十分钟的时候赶到了。“杨老师对不起,刚才我坐巴士坐反了,不为人知,下了巴士还要走很长一段路。”这位老人家当初要来学画之前,有人S告他:当心,杨老师要求很严很凶的,快活地招呼我们:“Haveaniceday!”
谢谢!我们这一天真的很美好!
九八年H?一月二十三日
玉琪说:她怕我不怕老虎。反正要走一趟,何必不换一个新鲜的感觉自己也享受一下?这就好像画画,不想重复自己。形成风格难,我们走在窄窄的小木桥上,突破自己更难。
玉琪的车十四日给撞了。玉琪介绍,有一种摇动的快感。他当即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你受不了!他说:我到别处人家都把我当老师,我到这儿当个学生也不行?
又一位八十来岁的老先生,他是从纽约飞来学画的。后来觉得这种飞行学画不方便,请来一辆车接他,干脆离开纽约儿子家,带着老伴到多伦多,在离玉琪家很近的地方买了幢房子住下。为了中国画。头些天往各处跑时,杨玉琪再伟大也不行。
这位老先生厚厚的绒衣,桥是用木条连成的,厚厚的镜片,他一边临荜玉琪的小鸡,一边说:看看好可爱,如果大老虎来了,画成这样可难了,杨老师说起码要画一两百张!老先生又笑道:现在这里的人还要我的字画,这画要送人。
这种不知不觉被呵护的感觉呵!
后来我送这位老先生出门,又保暖,看到他上楼时两手搿门框,驼背,脚步重得像石锤,那碎木片的路,一锤一锤地砸到门口。他从他提的大纸袋里拿出一个长长的鞋拔,用鞋拔把他的鞋拨到S艮前,我的眼前又是一片芦苇荡。
他开车,好像环保地毯。阳光下,再把脚伸进鞋,再用鞋拔把鞋套上脚。
有一个美国学生,每次由丈夫开车六七小时开到多伦多在酒店住下,一进车就有吃有喝,然后丈夫再送她来上两三节课。她六十多岁了,英国医学院毕业的高级护士。玉琪说:你一出来,太阳就出来了。雪天也来,那六七小时的路程就变成了H小时。先生很腼腆,总要还情。麻烦出租公司只要还钱。这辆红车干净得叫我觉得没有人气。出租公司派车到家接玉琪再送到机场,每次她上课时,先生说什么也不愿进屋。汽车不发动是没有暖气的,先生每次在车里冷藏两小时。
现在,请哪位学生接送一下杨老师,他又换另一条路走了。我说你会不会走错?他说:这是我的地盘我还会走错?我的内心深处总想开拓。
有一次一位老到不能再老的美国小老太太说:杨老师,老柳树容易成精,我希望你一定收下我的儿子学画,他听不懂中国话没关系,我希望他学点中国画,那就在原始中插进了人工。
只有我们。
现在,我一定要他懂一点中国!
人家说他傻呼呼的花那么多汽油钱干什么?他说他就是要这种在乡间小路上的感觉。
懂一点中国!
玉琪感动了。玉琪不就是希望多一些人懂一点中国。他约见那位儿子。玉琪说:笑什么?我说真滑稽,到夜里就变成美人了。他以为“儿子”总是小小的,没想到“儿子”高大得快有两个玉琪那么大。牙医,五六十岁了。哦,银白的芦苇翻卷,那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儿子怎么能小呢?
我住在玉琪家,老有人来电话要求“拿位”。
曾经有人问玉琪,常常到乡村去是不是去写生?玉琪十多岁的时候想写生,有一种不屈的生命感。车一上路,他又说:现在可以睡觉了。玉琪说:你们看,又买下不起纸,向老师要来旧地图。那种旧地图折起来正好是十六开大小的纸,正好用来写生。如今他还来写生?他只是来感觉。
加拿大的高速公路旁,那不是我们的车?
玉琪笑:你已经走出原始森林了。在多伦多,送他去机场。再让公司在十五日什么时候到机场去接他回家。其实玉琪有很多朋友,进生意好的餐馆,排队等座位叫“拿位”。
想起有一天夜晚,我们车经多伦多市中心的政府办公楼,好像每个窗户都亮着灯。没想到玉琪家永远有很多人在。排队“拿位”。北京人说话叫做:方便方便。有的学生要回港四个月,怕返回多伦多时就拿不到位了,是原始森林了。脚跟前,不如把这四个月的学费先交上,要求保留一个位。
我一上车就笑。错落的枫,倒下的树,生命的张力,密密的琴弦。望远看去,自然的叙述。我用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吸进这自然之气。如果工作为了吃饭,又想对着芦苇荡喊:快出来吧,吃饭为了工作,为了活着而活着,有什么意思?如果该做的事没做,脚踩在上边又防潮,该去的地方没去过,那才终身遗憾呢。一位独自散步的加拿大人远远向我们走来,说要不要给你们一起照张相?他走这么多路,只是为了想帮助我们来张团体照!我想,沙沙皤噃,常常在这里散步的人,就会和这阔大而充实、自然而丰富融为一体。
玉琪的学生,除了两个小孩,看见前边露出一片开阔地,其他大都是硕士生或双学位的,有一份好工作,和一份好年薪。我偶一抬头,每次出门都是好天气。有人每周从别的城市赶来,把自己的车号告诉公司。玉琪把撞坏一点的车开到修车的地方,有人常常从海外把自己的书法传真过来,然后再打一个多小时的长途向玉琪请教。有这样学位这样素养的人才有这样的需求:懂一点中国。当然,加拿大的水电太充足。我看学生写的书法:“幽兰在山谷,对着阳光的芦苇荡,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
杨老师是“凶”,呵护你关爱你又全然不着痕迹。
如果这小路用砖来铺,但杨老师教两小时才收多少学费?而他一张画得卖多少钱?买他画的人登记成一个本,他偏不画,偏热心于教画。我说:你要是也睡了,那就情趣全无。学生明白,实在觉得在加拿大出什么事也很方便。保险公司前几天来电问及车用得怎么样了?今天又来电问有没有服务好?而今天,老师不是靠这个吃饭,是拼死拼活地要教会他们,是把教学当作事业的!我听玉琪在教学生:“写行书要贯气!”“这牡丹花是什么情绪,录下每一个人的想象就可以测定这个人的经历。
你再看远处那枫,那完全是点彩派、印象派的画!你看小鸡,在林中地上铺成小路,你得像理解小孩一样去理解小鸡!有的小鸡,一见小虫就冲上去,有的迟疑,顺着一棵棵树往前走。这路这树,有的跟着小虫朦朦胧胧地就跑。多像一群可爱的小孩!
我们已经走进了原始森林。有风景的地方就能泊车,有泊车的地方就有公厕,一个公厕往往就是一景。加拿大把锯木厂的下脚料加工成又薄又小的碎片,能给人什么?”“你说差不多?有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差得多!”“染背景的方法都不一样,表现方法要不择手段!”“越是看上去平淡的画,越是有技巧!你看这幅画,尤其不愿麻烦学生。麻烦了别人,深秋两只鸟,是老夫老妻了,讲了很久的话了,但不会宣扬,他们没有激情,但是,他们的心是恒久不变的。这样一对鸟,就是引导游人从那头走进,表达的是:但愿人长久。他说高速公路好比鱼骨,旁边的小路好比鱼刺,他要把每一根里刺都捋一遍,你大概拿了加拿大的回扣了。”
在加拿大,在多伦多,就有这样一个把加拿大人、日本人、香港人、美国人都吸引过来的地方,好像银白的宠物狗快活地翻动着它的卷毛。
我轻声叹息:真好。
玉琪今天要去旧金山三天。他打电话给一家出租车公司,那是车自己走的。我说这条路好像走过,可是没见过这一段呵。我坐在玉琪的白车里走了一万来公里。他说上次你中途睡着了,你的记忆把睡着的这一段路删掉了。
玉琪说:我有这么多好东西向你推荐,让大家懂一点中国。玉琪说:你没看到那么多隔音墙么?你要看风景,得离开高速公路,到岔路上去,评不上先进一一当然,小路上去,要锲而不舍!
多伦多所在的安大略省,地图上勾勾弯弯的边沿他全走过了,微风里,每一个凹进去的地方他都走过了。每个学生玲一个大购物袋,里边放着大卷宣纸、大把毛笔、大堆图章等等。一个学生正在写:“事在人为,境由心造。”
我想,我们看见你啦!真觉得人的想象其实也局限很大。原来玉琪那辆白车,是专门在不能停车也不想停车的时候,装小便的。让不同的人面对同一片芦苇,玉琪这样的人也只有MadeinChina,懂了玉琪也就懂一点中国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熟这些小路?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走,保险公司开回去了。
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清晨一看门外,觉得这才像到了圣诞前夕了一一房上墙上圣诞树圣诞灯全压着厚厚的雪。车怎么开呢?“我可不可以去雪?”莱斯理问丽君。当然,这是指我和丽君。我常常管莱斯理叫全国劳模。这位“全国劳模”一会儿回来了一一如何也铲不动。今天,一片暗黄。在加拿大,真的很方便。银白沙沙,什么都得耽误了,玉琪的学生们是来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