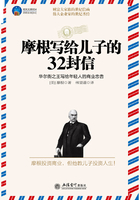因蝗虫谷的住宅靠海,每逢秋冬,寒气逼人,交通又不便,如遇大雪,顿成与世隔绝之孤岛。1995年,宋美龄索性把它卖掉,搬到纽约曼哈顿一栋15层高的普通公寓,从此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每日作画,概不见客。2000年农历春节前夕,曾有一位贴身随从提着两罐乌龙茶(这是宋美龄最爱喝的一种茶)去探望她,却未被允许进门。独居期间,孔令侃、孔令伟和孔令杰三个晚辈相继辞世,张学良也在几年后作古,仅留下她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代表着那个年代与过去的延续。但令人遗憾的是,宋美龄始终拒绝作口述历史和撰写回忆录,她声称一切都留给了历史,而时间会让历史还原。
宋美龄106岁生日之前,由于她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所以当时即有宋美龄身后事的种种传闻向外发散。这些传闻都没能得到证实,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她希望自己死后不回台湾安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外界有诸多的揣测。
一种说法是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以前曾经表示,一切都将交给上帝,身后不会随同蒋介石合葬在台湾。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执意不回台湾,但有分析人士称,蒋介石和蒋经国逝后一直没有下葬,这可能跟蒋介石一直想叶落归根回大陆有关。蒋纬国指出,蒋介石生前选定在南京紫金山、枋山、四明山三个地点,蒋经国则希望归葬浙江奉化母亲的墓旁。当时作为蒋家第三代唯一合法代言人的蒋孝勇,则坦白称移灵是家务事,蒋家有蒋家的处理方式。
另一种说法是宋美龄希望叶落归根。因为位于上海的宋氏墓园,除了有宋氏三姐妹的二姐宋庆龄的墓地,宋氏三姐妹的父母也都是安葬在这里。因为受限于两岸的政治因素,宋美龄一直无法亲自到墓园祭拜父母,所以几年前她特别委托别人代她献花致意。因此有人推测,宋美龄可能在身后选择和父母一起长眠在上海的宋氏墓园。
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性格中强势的一面得到了充分展示,从她的这篇回忆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她性格中强势的一面,回忆文字原文如下:
西安事变的经过、状况之复杂,决非中国过去的“兵变”可以比拟。
12日:噩耗传来晴天霹雳。1936年12月12日,我在上海。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忽然跑到我的寓所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闻此噩耗,不啻晴天霹雳。当时上海与西安的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以及陆地、空中交通,皆告断绝,过了好几个小时,仍不能得准确消息。而各种流言已传播全球,英文报纸,竟根据流言作了头版的大字标题。13日早晨,我和孔部长及端纳仓促赶往南京。无奈,南京虽为首都,同样没有确切消息。(国民党)中常会已于12日深夜开会,决定:免去叛变首领张学良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之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这天早晨,南京还接到了西安方面发来的“全国通电”,署名的人除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西北重要将领外,还有陪同委员长前往西安的南京高官多人。通电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蒋介石)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蒋介石)做最后之诤谏”。通电中,他们还提出了“救国主张”的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
这八项要求是: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停止剿共;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实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张、杨的电文也指出:他们将确保我丈夫的安全。兵变发生,我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是女人,世上之人,必定以为我是女人,遇到突然的兵变,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所以,我必须抑制个人的感情,从全局考量对策。看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如果处理得好,这次兵变必能得到合乎常理的解决。于是,当天晨8时,我即给张学良发去专电,告诉他:我们共同的朋友端纳,准备立即飞往西安。端纳也给张学良发了电报,盼其立即复电,看西安是否愿意接待。
13日:友人端纳直飞洛阳。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我一开始并没有给予重视。当时南京的一般人,在推测张学良发动兵变的原因时,亦大多认为,西北地瘠民贫,张学良率部驻军西北,或许早有不满,因此推断:张学良这样做,实际只是为了要求将东北军调防到丰腴省份的一种“借口”。不过,南京主张讨伐张学良的人,因此更加主张:对此种不听中央号令者,必须予以严惩,否则就是开了坏的先例。我则推测说:“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或许确实有不平之情绪,而且他们也认为自己具有相当的理由。如果一部分国人真的对中央怀抱不平,那么中央就应该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原因,并尽力纠正之。同为中国人,假如有其他途径可以解决此次兵变,又何必一定要用军事方法呢?”13日上午,接到了张学良的两封电报:一致孔祥熙部长,一是给我的。为节省时间,我和端纳决定:烦请端纳于13日午后,先直飞洛阳。另外,我请端纳携两函,一函致委员长,一函给张学良。在给张学良的长函中,我告诉他:他的这一举动,将使国家前途受到严重打击。我并表示,他的举动虽然十分卤莽,但我敢断定,他发动兵变的本意,并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的恶意,因此,他必须及时自拔,切勿贻误时机,以致后悔不及。端纳乘坐的飞机,13日下午起飞。还好,到了晚上,端纳就从洛阳打来长途电话,称他已于傍晚抵达洛阳。端纳告我:13日白天,中央军的30多架飞机,已在西安上空做了示威飞行,目的就是要告诉西北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军之手。端纳在电话中还说:他不管张学良是否有回电,定于明晨直飞西安。幸好,当天夜里,我忽然接到张学良致端纳的电报,说他欢迎端纳入陕。于是我放心了:端纳所乘飞机,应该不会在前往西安的途中,被人击落。
14日上午:中常会上舌战高官。南京政府当时已经决定:委员长回京之前,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遣全国军队,空军亦归其统辖。而委员长已经遇难的消息,也忽然流传开来了。局势虽然黑暗且危险,但我仍然有个直觉:事变可以稳妥解决。于是,这一天的我,就是要让国民党中央的诸位高官们相信,其一,只要多做忍耐,和平就不会绝望;其二,在军事讨伐西安之前,务必先尽力解救委员长脱离险境。因为攻打西安的战事一旦开始,委员长即使不被南京陆军、空军的轰炸所误中,也必然被怨恨的叛军所杀害。谁知道,中常会上,我陷入了“立即攻打西安”的主战派的重重包围之中。
中央常委会上,有人说:“为维持国民政府的威信,应当立即进兵,剿灭西安叛兵。”我当即反驳说:“今日之中国,假如没有委员长,就不会有任何统一的政府。今天我们舍弃委员长,不去救他,请问:还有哪个人能够立即担负起领导全国的重任?”我刚刚说到这里,会场里立即群情激昂,主张纷杂:有人说,委员长或许已经遇难;有人说,国家利益,应当重于委员长的个人生命;更有人辞色之间似乎在说:“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其丈夫而已。”我立即大声说:“我虽是一名女性,但我今日在此发言,绝非仅仅为营救我的丈夫。如果委员长一死,真的能够为国家造福,那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但处理西安叛变,如立即挞伐,直接轰炸,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立即陷入兵燹之灾……不仅如此,还将使我们为抵御日本入侵所做的诸多努力,白白浪费。因此,为了救中国,我不得不吁请诸位,妥善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看到各位都在倾听,我接着说:“希望各位相信,我决非每天早晚惦记丈夫安全的一般女性。今天,我在这里发言,是以公民资格,要求以最少的牺牲,为国家和民众,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因为委员长今天的安危,是和国家的安危密不可分的。如果你们主张向西安方向增派军力,我赞成,但请一定下达命令,嘱其切勿随意开枪,更不能立即轰炸西安、发起挑衅。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如果和平绝望,到了那时再开战,应该也不算晚。我深信,在座各位虽然与我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的诚挚态度、希望国家好、希望委员长好——应该是相同的;我坚信自己的主张不错,因此我必然全力以赴,确保我的建议能够得到实现。”听我一口气镇定地说完这些,会场里很安静。于是我又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决定:“我决定明天亲自飞往西安。”此言既出,会场哗然。在座高官,皆曰“不可”。众人皆曰“不可”,主要是因为当时盛传谣言,说:血与火充塞西安,西安城内,已成赤色恐怖世界。对局势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就算今天没死,日后也难免一死。大家对我的劝说,归纳起来就是:此时我赴西安,等于给叛变者又送去一个要挟我丈夫的凭借,因为我是自投罗网去给叛军作人质的……悲戚、失望、无奈,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原来的信仰,更难!至散会,中央的诸位高官终于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我飞西安的设想,仍遭到极力反对。晚上回家,不禁黯淡凄怆。只有暗自祷告,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的信仰耳。
14日下午:黄埔学生手足亲情。从中常会出来,各机关首脑也纷纷打电话给我,向我询问:目前情况下,应当如何应对。这中间,尤以黄埔同学的电话,最为迫切,他们要求我“立即发表讲话”。我知道,黄埔军校毕业生,都是我丈夫昔日亲自教育、培养的军队骨干,现在又担任着各部队的重要指挥员。既然他们坚持要我讲话,我就不能推却,于是,我索性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做了公开的演讲。我除了转述自己在中常会上的观点,同时也指出:在尚未搞清事变真相之前,期望各位同学切勿妄加断定。遇事一定要镇定,切勿感情用事。委员长平常对待各位同学,一如对待自己的子弟。目前遭遇事变,正是各位谨遵师训,报答校长的时候。我也说明,西安叛变者,已经有电报给我,我也回了电报给他们。委员长和张学良的共同朋友——端纳,正在前往西安的途中,我深信,这些叛变者看到全国民众的反应,必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因此,只要他们有悔悟之意,我们就应该打开谈判的大门;假如他们有悔罪的诚意,黄埔学生就应该以宽大为怀,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既往不咎。当我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压迫之时,我的大姐姐孔夫人(孔祥熙夫人宋蔼龄)、我的二姐姐孙夫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以及我的其他亲戚、朋友,也都过来全力慰藉我,他们的爱护之情,让我永远铭记在心。还有我的大姐夫孔部长,他兼任“代理行政院长”之职,虽然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但他始终充分同情、支持我的主张。
12月14日(星期一)晚,西安事变终于露出了希望的第一缕曙光,并且确切地证明了我此前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端纳从西安发来电报,报告了委员长的平安,而且说,委员长现在的住处,十分舒适,他正在旁边照顾呢!这封电报同时表示:张学良亟盼孔祥熙代院长赴西安,也非常盼望我能一起前往西安。过了不久,我又接到张学良直接发给我的电报,电文中不仅对我发出邀请,而且首次做出保证,说他虽然发动兵变,但绝对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意思……可惜,对这份电报,南京有些人认为:不可信!这些人认为:叛变部队的计划,往往异常险恶。端纳的电报,很可能是叛军故意假借端纳的名义发出,实际是为了诱使孔部长和我,一起进入陕西,以便他们能够再多扣押几名重要人质,增加其日后的谈判筹码。对于此种推测,我表示“根本不信”。因为我知道,要想避免丈夫死于兵变,避免内战大规模发生,避免其他不怀好意的邻国看笑话,我就必须前往西安,力求事件和平解决。所幸者,孔部长与我的两位姐姐,全都表示:愿意陪同我一起飞往西安!姐姐、姐夫的态度,真的让我很感动。
15日:汉卿来电邀我入陕。15日(星期二)下午,突然接到端纳从洛阳打来第二通长途电话,这个电话,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原来,十五日早晨,端纳冒着恶劣的天气,从西安乘飞机返回洛阳,就是为了从洛阳机场,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他去西安的真相。他用简短的英语,概述了全局。他说,委员长并未受到苛刻待遇;端纳到达西安后,委员长已被允许迁入较舒适的房屋。委员长也开始与张学良直接谈话,只是他的怒气仍未平息。不过,张学良已经当着端纳的面,郑重表示:他决心随同委员长一起回南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发动兵变的动机虽然绝对纯洁,但这一兵变,确有错误。与此同时,端纳也告诉我:张学良盼望我能去西安,因为他和他的部下,对我非常推崇云云。当然,端纳也坦率告我:委员长嘱咐说,我一定不能去西安。我丈夫的理由,和南京高官的说法差不多。当晚,我和大姐夫联系,不料,孔部长的医生说,他的身体不好,不能飞陕;而且孔部长兼任代理行政院长,此时此刻,势必难以离开南京。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告诉端纳,请他转告张学良,可否以宋子文代替我的大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