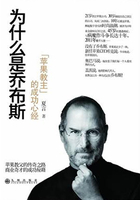有条小河,名叫“牟河”。它的源头是来自崇山峻岭中的一条小溪。小溪缓缓流来,时而窄时而宽,时而深时而浅,溪水碧绿,清澈透底。小溪流过的地方伴随着一串美丽的名字:阳山冲、方井坎、洞子墱、斜桥子……
小溪流到我们村里,人们在一个平坦地带把它加宽挖深,两边筑成河堤,栽上树木,成为一条宽阔的河流。家乡人沿河而居,由于大多数乡亲姓牟,人们把那条河取名“牟河”,把那个地方叫着“牟河坎”。家乡的小河一年四季流水悠悠,从不枯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总岗山水库还没建成时,干旱之年天不下雨,人们就用手搬车、脚踩车,一节连一节地把河水车到田间地里,灌溉庄稼,确保收成。
家乡人在河边挖了口井,用以饮用,人称“牟河井”。在河边搭上石礅子、铺上石板,朦胧的晨曦中,挑水声、洗衣声、笑语声不断飘向远方。家乡的河流又宽又长,一年四季碧波荡漾。酷暑季节,我们牵着牛儿到河里滚水,自己也到河里洗澡、嬉戏。河堤上有棵高高的白蜡树,我们光着屁股爬上去,闭上眼睛,双手一扬,猛地跳进河里,溅起一阵阵欢乐的漩涡。玩够了,牵着牛儿上岸,牛儿嚓嚓地啃着青草,我们欢快地打水漂。小河的上段是洞子墱桥,溪流两边长长的淤泥田里,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油草和高笋,浓密的高笋丛里不时有小鸟飞进飞出,藏满了儿时的梦想。小河的下段是石谷坎磨坊,里面不仅有两扇又圆又厚的石磨,还有一架水冲打米机,闸门一开,咕噜咕噜的磨面声,嗒嗒嗒嗒的打米声,是我儿时最爱聆听的旋律。河水涨满时,石磨和打米机可以同时使用,河水不多时,只能使用其中一件。有时石磨或打米机转着转着,忽然停了,河水不够,无法冲转。前来打米或磨面的人只好把玉米或稻谷放在磨坊里,等河水满涨时再来。磨坊是集体的,收来的工钱要上交。大哥曾经当过磨坊的看管员。有次石磨的齿轮钝了,为了多挣工分,二十来岁的大哥和另一个中年人把四个人才能抬下来的石磨抬下来维修,从此,年轻的大哥伤了气血,得了肺痨,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大哥去世后,每次从河边走过,我最怕听到咕噜咕噜的石磨声。因为我觉得,那是大哥的在天之灵,在嘤嘤地哭诉。
生产队从不在河里养鱼,可每年都有捕不完的鱼。鲫鱼、鲤鱼、草鱼、鲢鱼乃至乌龟王八,应有尽有。每年深秋过后,生产队放干河水,组织社员下河捕捉。男人们将裤腿和衣袖挽高,在腰间拴个笆笼,手拿底部有洞的背篼,在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下河捕捉。集体捕捉后,才允许妇女儿童下河捕鱼带回家。尽管这样,仍有不少漏网之鱼。三姐是捕鱼的能手,儿时的我就在岸边替她观察,看到了,就挥着小手要她去捉。有一次,三姐的小背篼罩住了一条大鲢鱼,双手伸进去捉住,并用手指扣住了鱼的腮帮。可拿出水面后由于力气不够,一不小心让鱼滑脱了她的小手,跳到滩边,被另一个男孩捉住。我们说是我们的,男孩说是他的,双方僵持不下。前来叫我们回家吃饭的母亲听说此事,要我们算了,别跟人家争了。当我们准备放弃离开时,男孩忽然把鱼给了我们……
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长大,离开家乡近二十年。想念家乡的时候,总觉得家乡的河水在心里哗哗地流淌。
上次回老家,但见家乡高楼耸立,变化很大。许多儿时的伙伴开始变老,许多陌生的小孩叫不出名来。家乡的磨坊早已没了,家乡的“牟河”被一位儿时伙伴承包,改作了良田。好在溪流潺潺,牟河井还在,洞子墱的桥还在。我想,家乡的小河不是早就成为一幅画,永久留在了我们心里么?我还寻找什么呢?
2013年1月24日于雅安
入选《优势阅读(实中版)》(兰州大学出版社),原载《眉山日报》2013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