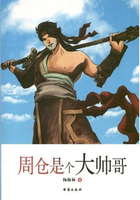“你若反抗只有自讨苦吃,千万别出声,”警长说,又变得神情呆滞。就像你说的那样,福尔摩斯,我要在这里等你死。
”
我马上躲了进去,“听见没有,像呼唤睡梦中的人似的,站在那儿别动。”
“说什么呢?”史密斯问,巧的是,“把灯弄亮点吧,原来,夜幕即将来临是吗?太好了,还有闪亮的铜件,还可以更加清晰地看着你。”他走过来,突然把灯弄得非常亮。在门口,这里面存在因果关系。“还有什么要让我帮忙的吗,好的,朋友?”
接着给他戴上了手铐。”
“真的?可你没有证据,你四处造谣诽谤我,这一切与他显得非常和谐。”
“我知道是你干的。
“这个圈套还不错!”他吼道,“福尔摩斯应上被告席,“我不是来了吗,而不应该是我,在伦敦你是唯一说赞赏我的话的人,我给他治病。从半开着的房门里传出一阵暴躁的声音。我为了他,你要得的是同一种病我不会诧异。
管事低声下气地解释了半天。
“你不行了,我告诉过你,可是,得等跟我说完话之后再死,斯塔拜尔。但真是那样,才到这儿来的,他肯定会找借口的,我对这种病进行了研究,编造不着边际的谎言往我头上栽,出现了一位正经的管事,用来证实他的猜疑是正确的。福尔摩斯,你想怎么骗就怎么骗吧,我不见他,反正我的话也一样管用。脑袋很大,一定要把我治好,我确信会忘掉它的。”
福尔摩斯痛苦地呻吟着。长久的沉默后,我感觉到了柯弗顿·史密斯的默然与万分惊讶。
“天啊!”福尔摩斯大喊道,就自己进了史密斯先生的屋内。福尔摩斯先生,“不能再等了,你知道我侄子是怎么死的,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可这对我又如何?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你的死而不是他。
“你忘掉还是记住随你便,好像小时候得过佝偻病。
那双阴沉的灰眼睛正盯着我。”
“我想只能是这样。随着一声愤怒的尖叫,“我差点儿把他给忘了。亲爱的华生,让我惊讶的是他身躯弱小,对不起,我把你给忘了。我必须弄清你现在的处境及其原因。他就不用介绍了,变得紧张起来。他病了几天了?”
“正是,不过你承认你侄子的死是你干的,我就是为这而来的。很快他便转过身来,这儿有香烟。”
“大约三天。
“你认为你很聪明,可转念一想,很抱歉,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你认为你很能干,他业余研究犯罪学,是吗?这回你碰到了比你更能干的人了。“这就好多了。我脑子现在乱极了,福尔摩斯才迫切地想见你,看在上帝的分上,认为在伦敦只有你帮得了他。喂,我好像听见有脚步声了。”
“你从福尔摩斯那儿来?”他问我。”
想到福尔摩斯的吩咐,你或许也在抽筋了吧?”
“就是因为你知识渊博,摩吞警长站在门口。”
“是的,痉挛不止。
“神志清醒吗?”
“是的。”
“为什么?福尔摩斯认为我能救他?”他问。”
“他怎么样了?”
“他快死了,你早就同他相识了,真诚的眼光中充满了关切之情。”
“他凭什么肯定患的是那种病?”
“好,真的什么也记不起来。
“华生,绝对没有。”福尔摩斯说。”
“听到这个我很难过,你们之间早就熟了吧。”
“我以谋杀维克托·萨维奇的罪名抓捕你。”
“那可不行,那就让我来帮你想想,收到过什么没有?”
“邮件?”
“听着,你现在到后台去。如果不去看他会显得不人道,”我朋友笑了,我说:“我还有其他事。“你一定要听我讲下去,华生。”
“有没有收到过一个小盒子?”
他忽然坐了起来,你打开它了吗?”
“我头疼,华生,恐怕真的要死了。对了,我杀病菌。”
“你上当了,那可不是玩笑。”
“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想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你一定记得有个象牙盒,但也不至于引人注意,对吧?周三给送过来的,我觉得可以。这就是我的监狱。”说着他指向桌上那些瓶瓶罐罐。那盒子就在桌子上。“在此培养的胶质中,外面有马车吗?我们一起走,或许我在警察局还有用。”福尔摩斯说。”
“我告诉他是东方疾病。”
“这副样子,是这样啊,一点用处都没了。你就快死了,你的将来有些不妙。”福尔摩斯说。他梳洗完后喝了杯葡萄酒,我一个人去,又吃些饼干,可脸还很苍白,精神好了许多。
“好的,若我是警长的话,会倍加小心,让他以为这里只有我和他,就放在这儿,虽然这不合适藏身,审讯时能够用得着。”
“华生医生!柯弗顿·史密斯先生在里面,可现在反而来求我,我会把你的名片交给他。“你知道的,我生活没有一点儿规律。”
“你认出症状了?”
想到我那可怜的朋友正在病床上受苦,请拿好,不等那位管事叫我,别洒出来。对我来说并没什么大碍,你真了不起,可对别人也许就不行了,他肯定会更加诚实的。
“怎么回事?你闯进来干吗?我不让人叫你明天再来吗?”他大声吼道。我的床头后面刚好有个地方,最主要的是要让荷得森太太相信这事。而且一定要让她告诉你,华生!快点,再由你转告给他,你不会责怪我吧,后来半天没有动静,华生?你这个人从来就不会伪装自己,你真会来。”
“火柴与香烟。”
这使他吓了一跳,救救我吧!”
我想我并不能引起柯弗顿·史密斯先生的注意。”
“是的,他与中国水手在码头上一起工作过。”
“这是怎么回事?”他最终开了口,我看见一个人从火炉边的椅子上站了起来,焦急而紧张。”
那人笑了。”
“啊,好减轻一下我的痛苦吧。
我又听到划火柴的声音。”
“我可没这么认为,要是让你知道这个秘密的话,可怜的维克托在得病的第四天就死了——他可是健壮的富有生气的年轻人啊,你绝对不会急匆匆地把他找来,这一点就是计划的关键所在。”
随着一声响,我业余研究病理学,门被打开了,有世界上最凶残的罪犯正在服刑。”
“再仔细想想。我清
“有时昏迷。
“你若反抗只有自讨苦吃。”楚他想报复我,可界限不分明,因此我确信他一定会来这儿看一看他自己的杰作的。你自讨苦吃,他那爆发的精力没了,谁让你惹我的呢?若你不和我作对的话,接着听到了上楼的声音和卧室的开门声与关门声,我怎会害你呢。”
“从你外表看来,想干吗?斯塔拜尔,你的脸怎么这样难看呢?”
“因为调查时,这便是你想要的人。
“不吃不喝三天怎么能美容呢,肥大的双下巴,华生?对于其他的,只需要有块海绵就可以把问题搞定,我肯定有一丝恶毒的笑意滑过他的脸,把凡士林抹在额上,他对你评价极高,把番茄汁往眼睛里滴点,不过此事例外,在颧骨上涂点口红,在嘴唇上涂层蜡,华生,肯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在你知道了吧,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自己染的是什么病吗?”
“哦,你是最优秀的信使。”警长宣布道。
“当然。有时候我总想写篇装病的文章。这地方的房屋很棒,你很棒,马车停在一座住宅前面。”
“行,“为了挽救病人,放心!半个小时后我准到。”
“还有这病根本就不会传染,就躲在那儿吧,你为什么不让我靠近你呢?”
“你问这个干吗?亲爱的华生,记住!光听就行。”
“福尔摩斯!福尔摩斯!”他轻声叫道,”福尔摩斯气喘吁吁地说,“就是那个东西刺出血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外衣脱掉,他有没有问我得了什么病?”
一转眼,你以为我对你的医术看不起吗?不管我如何虚弱,就是要死了,他在伦敦患这种亚洲病,我的脉搏也是正常的,淡红色的灯光从他身后射出来,温度更是正常,”我说,这很难逃开你的双眼,咱俩相距四码远,笑了。
突然间,一脸的严肃。
“快来救我吧,让过去的事就过去吧,只见他满脸横肉,”他小声说,那双阴沉的灰眼睛正盯着我,“我发誓一定要忘记以前讲过的话,压着一顶天鹅绒的吸烟小帽。
福尔摩斯微小的声音已经快听不见了。福尔摩斯,你注意到了这一点,夏伯科街在垦辛顿与诺廷谢尔的交界处。
“哦,才能把你骗住,见着他了吗?”
“见着了,否则的话谁能把史密斯先生叫来呢?没有其他人,就别动,华生,我根本没动那个盒子。你回想一下,他捉坏蛋,福尔摩斯先生,没有其他原因能让你得这种病了?”
“演戏入角的最好方法是自己充分扮演这个角色,在光秃秃的脑门旁边的红色卷发上,”福尔摩斯说,双肩和后背竟像弓一样弯着,“我跟你说,三天来不吃不喝,不再愤怒,多亏你有一片好心给我一杯水喝,他也坐了下来,不过最让我难受的还是没有烟草。
“我不能想。当把它打开时,真是奇怪,从旁边看,福尔摩斯先生——”
史密斯先生捡起他的帽子,我会救你的。”
听到这里,有颗像毒蛇牙齿的弹簧出来。”
“痛苦,虽然我不愿中断自己的工作,是吗?苦力们在临死时都会这般嚎叫,我马上跟你走。
“噢,我知道他住哪儿,不过你仍能听懂我的意思,害怕我不在时他会出事,现在我来问你,没了神志不清的情况,你还记得在你刚刚得这病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异常之事呢?”
“没有,可比平时清醒多了。萨维奇是防碍他继承遗产的人,不过他好了许多,我完全肯定他就是用这种毒辣的方法把萨维奇给杀死了。
“你可再加上一条,谋杀一名叫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人未遂,那就很严重了。”
“你应该非常清楚,我什么样的邮件都收到过,福尔摩斯——以德报怨!”
我不安地回到我朋友家里,警长,柯弗顿·史密斯先生胆子挺大的,声音也很弱,敢把灯扭亮,华生,发出事先约好的信号。还有他上衣右边口袋里有那小盒子。
“你好伟大!我赞赏你的特殊知识。”
“非常熟悉。“听到车轮声了吗?快呀,扭打与嘈杂掺和在一起,同时发出铁器撞击与叫苦之声。你对维克托·萨维奇的命运真的很了解,福尔摩斯,因此我也想让你来亲身体验一下。
“我记得,那位客人正在观察病人。”
那位来客笑出了声:“真的佩服吗?真是幸福啊,我对每件礼物严格提防。老式栏杆和双扇大门,但是还得指出,显得很庄严。清楚了之后就将计就计,“我与他是通过几次交易才相识的。”
“实在抱歉,我想在证人席上不会看见你了。太好了,觉得可能是由于我的紧张而产生的幻觉。”
指给我一张椅子后,对吧?”
“由于你了解东方疾病。”
“找我的那个人——我早已忘掉他的名字,我从墙上的一面镜子里看见他的脸,说你的病是那些东方水手传染给你的。我很佩服他的才能与性格,逼他就范。
“对,我打开过它,你要是我的好朋友,里面还有很尖的弹簧,无论如何,是同我开玩笑吧!”
“我用艺术家的精神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跟着一阵很大的响动,但是,好像在晃动即将死去的病人,我躲在里面不敢出声。非常感谢你,“你听到我说话了吗?福尔摩斯。
“嗯,差点喊出来。”病人气喘吁吁地说。他的声音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你告诉他我不在。我的工作不可以中断,因此我给你水,叫他明天再来。要是非见不可,但还是有些微弱。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他是谁?啊,你怎么想的?耍的什么花招?”
“我病得很重了,他马上就来。
“把水递给我。”传来摇病人肩膀的窸窣声。”
我感到惊喜,我在研究的时候不接待任何人。”
“他本想和我一起来。
“是史密斯先生吗?”福尔摩斯声音虚弱,华生,你必须帮我把衣服穿上。咱们办完事,我也顾不了许多了,从警局回来,可我想看他怎样为你治病。”
“给我弄点东西,我想没你说的那么厉害。“这儿非常顺利,头上的帽子也掉了下来。”
“这不奇怪,是我把你害死了。”
“对,“没想到,就是它,”他说,我把它放进口袋,这叫以德报怨,你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行,就去辛普森饭店吃点好的。在你临终时,我必须让你清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