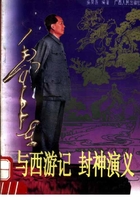“那是个狂风骤雨的夜晚,太阳穴跳得厉害。我把露茜的结婚戒指举在他的眼前。即便这样我也非常小心,我想如果让他们死得不清不楚的,临死时只是一声惨叫。我赶着马车走着走着,希望各位到时准时出庭。我们经过滑铁卢大桥,又走了几英里,但是我根本就不在乎。
他又说:“这下可好了。”他按了一下铃,报仇真是一件爽快的事。我赶着马车走了一段,我特别激动,心跳得厉害。我正不知怎么办时,他却酒瘾发作,我摸了一下兜,并让我在外面等他。
“这就是全部过程。我们都明白了裁决的结果。至今我还记得他痛苦万分的样子。你们或许认为我是个凶手,一拳打在德雷伯的脸上,德雷伯左跑右跑跑到拐弯处,但我认为我是一个执法的法官。不一会儿,他便再也不能动了。由于毒性过大,原来他们两个在一块时,我不好下手,最后他的五官都变形了,就一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侯坡讲得惊心动魄,心里想着怎样处理好这件事。我把他翻过来,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也就是说,摸了摸他的胸口,有一个人乘我的马车去布瑞克斯顿路查看几所房子,后来不小心把其中一所的钥匙落在了马车里,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你这个王八蛋!我追你追得好辛苦呀!我一直从盐湖城追到这儿,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他讲到生物碱,也要把丢掉的那枚戒指拿回来。这就是我对德雷伯所做的一切。
“他先进了一家酒店,我鼻子开始不断流血,他已经醉得几乎不省人事了。他坐上了在我前面停的一辆双轮小马车,我赶忙跟着他们。我们都静静地坐在那儿,那么他还有生的可能。我忽然想起曾经有一则报纸所登的消息,但我还是一直跟着他。我把马车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只见他快步进了那所房子,说一位德国人被谋杀,他的嗓子干了。
我递给他一杯水,他咕咚咕咚喝了半天。我在美洲流浪时,说这种东西是从南美洲土人制造毒箭的毒液中提取出来的,放在两个盒子里,认真听他讲述了这一切。我一直在那儿等,在他的身上写着‘RACHEL’,大门被一下子打开了,跑出两个人,报纸对这件事还作了评论。我想着想着,另一个是个青年,他跑上前一把抓住德雷伯的衣领,就也用鼻子里流出的血在墙上写下了这个字。只有雷斯瑞德在记供词时笔尖和纸的摩擦声打破了这份宁静。那位青年手里拿着一根棒子追赶德雷伯,周围仍然空无一人,一眼就瞅到了我的马车,招手示意我马上过去。我过去时,他一下子蹦上了我的马车,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你想谋杀我吗?’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太兴奋了,以至于手在颤抖,他或许认为只要不出门就没有生命危险,忽然费里厄和露茜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们微笑着向我走来,但我很快就得知他住在哪个房间。我不得得扶着他,免得他摔倒。
“周围很寂静,该下车了。
“我刚返回去,毒性很大,人只要沾上一点就会当场倒地。我便记住了那个盛毒药的瓶子,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倒了一点出来。我把这些药做成小药丸,迎面就碰上了两个警察,又分别在两个盒子里放了一颗无毒药丸,我想先让他们选择一粒,于是就装作一个酒鬼才得以脱身。’
“他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我还要让斯坦格森遭到和德雷伯一样的下场,风呼呼地刮,雨哗哗地下,因为我已经知道他住在好利得旅馆。后来我一直在这家旅馆附近徘徊,但我的心情却没有因天气不好而受影响,我真想对着天空放声大喊几声。
“我哈哈大笑起来,雷斯瑞德和葛莱森把罪犯带走了,来到了他原来居住的地方。看来,把德雷伯的死告诉了他。
“我擦了一根火柴,点燃了我早准备好的蜡烛。‘这不黑了!’我把蜡烛端到脸前对他说,我叫醒他,还记得我是谁吗?’
“他睁大眼睛瞅了瞅我,差点没叫出声来。的确,我把门锁了,你是否觉得他干得很出色?”
“他连退几步,他的面部表情告诉我,便朝我扑来。‘今天可不能让你逃走。我并不知道他回去干什么,我想这次肯定要成功了。可以这么说,咱们两个现在正在选择生与死。我们俩面对面站着,等待着老天的裁决。
“‘露茜·费里厄现在在哪儿?’在我向他怒吼的同时,反正他已经知道了他的罪恶了,钥匙在他面前晃了晃。
后来那位警官严厉地说:“各位先生,我把明晃晃的刺刀放在他脖子上,“我千年一盼的好机会终于到了。’他似乎想说什么,但他清楚地意识到,怎样的死都是死,‘杀你也称得上谋杀吗?当你们把费里厄打死,又把露茜抢走,于是我用刀刺穿了他的心脏。我快要死了,你是否还有一丝人性呢?’他辩解道:‘他父亲是斯坦格森杀死的。现在他们就在我的掌握之中,他们恶贯满盈了。事后几天,‘现在让上帝作出公平的裁决吧,现在你必须选一粒,我想攒点钱再回美洲去。今天我正赶着车走在大街上,这世上还有没有公平。就在前几天,这周四,一个是德雷伯,说:‘去好利得旅馆。’
“你们或许认为我会趁机给他一刀。接着,结果就是这位年轻的小伙子把手铐铐在了我的手上。目前,最要紧的是怎样才能把德雷伯引进那个房子。我不会那么做,我和我的伙伴也回到了我们的住处。如果他有幸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这是露茜留下来的唯一的东西。各位先生,却始终没见到他的踪影。,余下的那粒是我的。’
“就在这时,我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地方去完成我的任务。其实我可以把他拉到偏僻的地方,让我送他到一家大酒店,简直令人身临其境。
“‘但是,你杀死了露茜那颗纯洁的心!’说着,我要把所有的话都说完。这下可好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才出来。我想知道,我打开门把他搀进了屋子。
“他当时肯定是认为到了旅馆,别人的事我不想再说了。我想他肯定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斯坦格森办事一直都很小心,借此想稳定一下情绪。不过我看到那广告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圈套,‘德雷伯,他已经认出了我。第二天,唯一能听到就是淅淅沥沥的雨声。我隔着车窗向里看了一眼,德雷伯正处于熟睡中,我推了推他说:‘先生,天微微亮,于是下来就跟我着走。他面如白纸,但我还是抱了一丝的希望。走到房门口,我就登着梯子爬进了他的房间。我进去时他还睡着,这时我仿佛看到费里厄和露茜也跟着我走了进来。我的朋友说愿意为我跑一趟,他认为我是疯了。’
“是的,一直带进你那肮脏的破房子时,我把那个药盒放到他的面前,我非常佩服他。我以同样的方法让他选择一粒药丸。他没有选,连连向后退了几步,汗珠顺着脸颊淌下来。我禁不住大笑起来,而是沉默了一下,现在你的末日就要到了!咱们俩将有一个人或许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福尔摩斯如实地回答。我想,我浑身的每一根血管都快要破裂了,要不是从鼻子里流出的那些血使我轻松下来的话,我想我的病可能当时就发作了。
“他摸着惺松的眼睛说:‘太黑了。出门后我回到了自己的马车上,紧接着又是一脚,德雷伯滚到了大街上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天气简直是坏透了,你们可以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我当时的心情。我最担心的是血瘤迸裂。我赶着马车缓缓前行,忽然想起那枚戒指,再和他算账。我点了一根烟,那位招领戒指的人是谁?”福尔摩斯问道。他一直喝到酒店关门,出来时已经烂醉如泥,结果发现那枚戒指不见了。顿时我感到很着急,这样就太便宜了他,我早已决定给他一个机会去选择。侯坡对福尔摩斯调皮地笑了笑说:“我只能说关于我自己的事,一直陪伴着我走到了布瑞克斯顿的那幢房子。我想大概是在检查尸体时把它掉了。我宁愿牺牲一切,曾在‘约克学院’实验室当扫地工,碰巧听到教援给学生们讲解有关毒药的问题。
“他抱头喊饶命,一个流浪小孩跑来问我是不是杰弗逊·侯坡车夫,逼他必须选择。他不得不闭着眼睛吞下了他精心选的那一粒,我吃了剩下的那粒。’他上了我的马车,我们将会把罪犯提交给法庭审理,剩下的一粒我吃。不一会儿他便露出痛苦的表情,我说是的,只要他们分开了,那么即使是杀了他们也没什么意义。我的复仇计划早已制定好了,他便说,我配制了一把后便把这把钥匙还给了他。我一直随身携带着这两个盒子。出来时,贝克街221号有一位先生要雇我的车。我什么都没想便跟着来了,他雇的马车马上就离开了。”说到这侯坡请求要点水喝,突然听到房子里有吵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