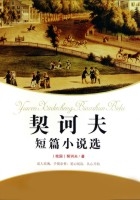1
他太太讨厌见到巴比特笨手笨脚的样子,听到他要死不活的打鼾声;这鼾声,他太太可怜兮兮地说,她已经听惯了,变得麻木,再怎样讨厌也不会表示出来;但不多久,她把他们的卧房弄得一点没有人味。
于是,才有了那睡廊。平常他们拿它作化妆室;酷寒的晚上,巴比特忍痛放弃了他的男子气概,溜入卧房内床上来,一面蜷缩着脚趾呵暖,一面嘲笑那正月的鬼冷风。
卧房似一张又朴淡又明亮的色纸。这是一位第一流的装潢师设计的,这位“专攻内部”的人,替天顶市许多投机建筑商搞室内设计。灰墙,白色木造门窗,天蓝色地毯,家具看来似乎是桃花心木做的——五斗柜,嵌着大而亮的镜子,是巴比特太太的化妆桌,摆放着几乎是纯银的梳妆用具,两张一模一样素色单人床,中间夹一张小几,放着一座其他人家都用的那种床头灯,一个开水杯子,以及一本其他人家也都看的彩色插图床头书——这是本怎样的书,谁也不敢确定,因为从来没有人翻过它。床垫坚实而不硬,这是一张值得炫耀的时髦的床垫,可值不少钱;热水暖气管子让整个房间有一种科学味道的外表。窗子颇大且容易开关,上好的锁环,荷兰制的卷帘窗罩,保证窗子不会龟裂。这窗子在整个房间中尤为一杰作,它可是从为中产阶级开的“摩登快乐之屋”买来的。然则,这房间的一切跟巴比特了无关系,也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假加某个人住过这里或喜欢这里,半夜里读一些热闹的小道消息,星期天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他一点也不会注意到这房间有啥不同。这里有着上好的旅馆内上好的房间的那种气氛:期待服务生进来收拾干净,好让某人只作一个晚上的停留,头也不回地离开,而且永远不会再想到它。
花岗住宅区每一家,都有一间煞像这般的卧房。
巴比特的房子已建了五年。整栋房子就似这卧房一般,既头头是道又似是而非。它有最高级的品味,最好的廉价地毯,简单而值得赞美的架构,最新奇的设备。到处,电取代了蜡烛和易弄脏的炉火。卧房地板缘有三个电灯插头,隐藏在黄铜小门后。走廊上有真空吸尘器用的插头,起居室内有钢琴灯和电扇用的插头。干净的餐室(内里有张令人称羡的橡木餐具橱,上铅釉玻璃的碗橱,乳酪色灰泥墙壁,一张朴素的风景画,一只鲑鱼在大堆牡蛎上喘着气),有供电咖啡壶和电烤面包机用的插头。
其实,巴比特的房子并无一样东西出了什么毛病,但它不像一个家。
平常早晨,巴比特是活泼蹦跳的,一路打趣着去吃早饭。但今天,有什么事搞砸了。他像个教皇地走过走廊,顺道查看威珞娜的卧房。他嚷着:“给这家一个这么高级的房子有什么用?他们不感激,不好好干活,也不晓得什么才是最要紧的事。”
2
他挺向着他们:威珞娜,一个棕发矮胖的二十二岁的女孩,刚从贝林摩勒学校出来,关心责任、性、上帝,为现在穿在她身上的灰色运动服无法克服的宽松而烦恼。泰德——狄奥多·罗斯福·巴比特——十七岁腼腆的男孩。妲卡——凯瑟琳——还是个十岁的小鬼,红发发亮,皮肤细嫩,这暗示着她吃了太多糖果和冰淇淋苏打。巴比特放重脚步进入房间,但他没有显露他含混的忿怒;他真的不喜欢在家里做个暴君,他常唠叨不休,但无什么意义。他朝妲卡吼说,“喝,猫丫头!”除了“亲爱的”“甜心”用来唤他太太外,这是他语汇里仅有的昵语,他每天早上拿它来吓妲卡。
他灌下一杯咖啡,希望能使他的胃和心平静下来。但胃一无感觉,似乎胃也不属于他了,而威珞娜又露出那一副多么有良心责任的讨厌相;突然,一种对生命、家、事业的怀疑,又来搔撕着巴比特的心。那怀疑,从大清早他的梦境与那纤柔的小仙女消失后,就一直搔撕着他。
威珞娜在鲁昂斯勃皮革公司当了六个月档案管理员,她希望成为鲁昂斯勃先生的秘书,对这事巴比特也曾凑说,“你昂贵的大学教育,也该得些好处啰,到你准备嫁了安顿下来为止。”
然则,现在,威珞娜说,“爸!我跟一位同学谈过,她在联合慈善机关工作——喔,爹地,有好多甜得紧的小婴孩到牛奶供应站来!——我觉得,好像我该做些像那样有价值的事。”
“你说这‘有价值’是啥意思?如果,你当上鲁昂斯勃先生的秘书——也许你可以的,只要你保持你的速记水准,别老是每晚偷溜出去听音乐会或闲聊——我猜,你一星期可以发现三十五或四十件有价值的事哩!”
“这我晓得啦,不过——喔,我要——贡献——我多希望我在社会福利工作处工作。我想,假使有一家百货公司,让我设一个福利部门,有一间精致的招待室,一些印花棉布和柳条椅子,等等等等的。或是,我能够——”
“现在,可给我注意听着!首先,你得了解,所有这些向上发扬道德啦,或向后翻筋斗、社会福利工作啦,或什么改革改革的,在上帝的世界中,除了是踏入社会主义的阶梯外,什么也不是。一个人愈早学懂:他不要被娇生惯养着,也不要期望什么免费的食物和——哎,所有这些免费的东西,翻筋斗,给他小孩玩的小玩意,除非这些全是他自己赚来的,那么,他就会愈快愈努力工作去生产——生产——生产!那才是国家需要的啰,而不是所有这些虚幻愚蠢的鬼主意,只会腐蚀工作者的意志力,带给他的小孩许多超过他们本分的怪念头。至于你——如果你肯用心干活,不这样无所事事拿些劳什子来烦自己——老是这样!当我年轻时,我就下定决心,做我想做的,酸甜苦辣始终坚持下去,而这就是为啥我能有今天这个样子,而——蜜拉!你怎么让这些鬼丫头把好好的面包切成这些碎块?你不能自个动手吗?总归,扫兴透了!”
泰德·巴比特,一间很棒的东区中学校的三年级生,一直发着似打嗝的声音来打岔他们。现在,他冲口喊,“说呀,珞妮,说你要——”
威珞娜转过来:“泰德,小心点,别打岔,我们正说着严肃的事呢!”
“噢,废话,”泰德公道地说,“自从某人犯了错让你从大学滚出来后,狗屎的,你就一直扯这些关于什么等等啦,等等啦,等等的傻话。你是不是要去——今晚我要用车子。”
巴比特嗤鼻了:“噢,别想!我自己要用!”威珞娜抗议说,“噢,甭想,你这又骄傲又讨厌的家伙!我自己要用!”妲卡低泣了,“噢,爸爸,你说过你也许开车载我们去玫瑰谷玩!”而巴比特太太说,“小心,妲卡,袖子沾到奶油啦。”大家彼此怒目着。威珞娜忿恨地说:“泰德,说起用车,你真是猪!”
“当然你不是了!没鸟的货!”泰德定是气疯了。“你只要一吃完饭,就急着把车抢走,整个晚上就让它停在某个婆娘的屋前,你待在室内,胡扯些文学啦,有教养又博学的男人啦,你就要嫁人啦——只要他们肯求婚!”
“哼,爸本就不该让你开车!你跟附近那些恶心的野男孩开起车来像疯子一样。你们搞的鬼主意,就是打算在夏令营中轮流以每小时四十哩的速度开车!”
“噢,你从哪儿听到这些蠢话!你是被车子吓怕啦,所以上坡路时你也紧张兮兮地拼命刹车!”
“我才没有!而你——老是吹牛说你多懂汽车,优妮斯·小野告诉我,你说电池供发电机的电!”
“你——怎么啦,我的好姑娘,你根本不懂发电机是从一个差动齿轮来发电的。”泰德对她这般傲慢不是没有理由的。他是一个天生玩机械的人,一个机器制造者和万能的修理人,他懂的东西他自己说不清楚罢了。
“够啰!”巴比特面无表情地截断二人的话头,他点起了一天里的第一支令人神清气爽的雪茄,瞥了一下《拥护者时报》的标题,似尝了一口令人振奋的麻醉品一般。
泰德用磋商的语气说,“噫,坦白说,珞妮,我并不想用那破车,不过我答允我班上几个女孩,载她们去学校参加合唱团预演会,所以,噫,我并不想开车,不过一个绅士得遵守他社交上的承诺。”
“哼,都是你的话!你跟你的社交承诺!在那个鬼中学里!”
“喔,我们到过你那母鸡大学,我们以后才不选它呢!我可告诉你,在这个州内,没有一家私立学校有像今年我们这样棒的一群聚到一块。有两个家伙,他们老爸是百万富翁。说真的,噫,我该有一辆自己的车子,像那些家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