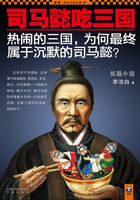秋声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①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②,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③,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④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⑤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⑥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⑦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⑧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之馀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⑨,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⑩声主西方之音,夷则{11}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12},黟然黑者为星星{13}。奈何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注】
①悚:恐惧。②淅沥:形容雨、雪、风等的声音。萧飒:风声。③(cōng匆)铮铮:金属相击发出的声音。④衔枚:古代行军常令士兵口中横衔着一种形状像筷子的器具,防止喧哗,以免被敌人发觉。⑤明河:天河,银河。⑥霏:飘扬。⑦砭(biān边):刺。⑧缛:繁多,繁茂。⑨义气:刚正之气。⑩商:古乐五声之一。{11}夷则:古乐十二调之一。{12}渥(wò握):浓郁,湿润。丹:红色。{13}黟(yī衣):黑色。
《秋声赋》作于嘉佑四年(1059),欧阳修时年53岁。这篇文章是他继《醉翁亭记》后的又一名篇,骈散结合,铺陈渲染,词采讲究,是宋代文赋的典范之作。
《秋声赋》写秋以立意新颖著称,从题材上讲,虽然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题材,但欧阳修选择了新的角度入手,虽然承袭了写秋天肃杀萧条的传统,却以秋景烘托出人事忧劳更甚于秋的肃杀这一主题,使得文章在立意上有所创新。
文章第一段写作者夜读时听到秋声,从而展开了对秋声的描绘。文章开头,作者简捷直入地描画了一幅生动的图景:欧阳修晚上正在读书,被一种奇特的声音所搅动。这简捷的开头,实际上并不简单,灯下夜读,是一幅静态的图画,也可以说,作者正处于一处凝神的状态中。
之后,作者对秋声作了一连串的比喻,把难以捉摸的东西变得具体可感。作者用风声、波涛、金铁、行军四个比喻,从多方面和不同角度,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地形象地描绘了秋声的状态。秋风呼号,秋声凄切,长夜漫漫,虫声唧唧,悲愤郁结,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叹息。用形象化的比喻,生动鲜明地写出了作者听觉中的秋声的个性特点,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感。
紧接着是与童子对话,从浮想联翩回到现实,增强了艺术真实感。作者对童子说:“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回答:“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童子的回答,质朴简明,意境优美。于是,作者的“悚然”与童子的若无其事,作者的悲凉之感与童子的朴拙稚幼形成鲜明对比,两人对秋声的感受截然不同。在这种对比和反复描绘之下,“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一句,将悲秋之情由自然转喻至人。作者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心情自然溢出,而后引入一个豁然开朗的新境界,实际上是实现了对“悲秋”主题的超越。
第三段是全文的题旨所在,作者由感慨自然而叹人生,百感交集,黯然神伤。这一段,作者在极力渲染秋气对自然界植物摧残的基础上,着力指出,对于人来说,人事忧劳的伤害,比秋气对植物的摧残更为严重。
最后一段,作者从这些沉思冥想中清醒过来,重新面对静夜,作者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和悲凉没有人能理解。“童子莫对,垂头而睡。”唯有四壁的虫鸣,与“我”一同叹息。此情此景是何等悲凉:秋风呼号,秋声凄切,长夜漫漫,虫声唧唧,悲愤郁结,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叹息。
统观全文,叙事简括有法,议论有理有据,章法曲折迂回,语句圆融轻快;可以说是节奏有张有弛,语言清丽而富于韵律,写景、抒情、记事、议论熔为一炉,浑然天成。
此外,《秋声赋》在文体上也有所创新。欧阳高举文体改革的旗帜,以身作则,在抨击古文的烦琐空洞之后,又回过头来为“赋”体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赋的散文化: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使赋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加了其抒情意味。这些特点在《秋声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后人评论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赋史大要》:“诚文赋开山之作。”
朋党论
臣闻朋党①之说,自古有之,惟幸②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③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④,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⑤。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⑥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冶。《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⑦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⑧。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⑨。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⑩。”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11}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
①朋党:人们因政治目的、主张相同而结合的派别或集团。宋仁宗时,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被诬为朋党,遭贬谪。数年后,范仲淹再次执政,欧阳修因作此文。②幸:希望。③党引:结为私党,互相援引。④共工:旧传共(gōng恭)工、(huān欢)兜、三苗和鲧(gǔn)为尧时的四凶。⑤八元、八恺:据《左传》,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称八凯。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称八元。此处元、恺皆和善之意。⑥皋(gāo高)陶:掌管刑法。夔:掌管音乐。稷:掌管农事。契(xiè泻):掌管教育。⑦用:因此。⑧目为党人:东汉桓帝、灵帝时,两次兴起党狱,株连正人君子多达四千余人。此言汉献帝时,有误。⑨“唐之晚年”句:指唐穆宗、宣宗年间的牛僧孺与李德裕的党争,史称“牛李党争”。⑩“及昭宗时”句:唐昭宗在位十五年,904年被朱温杀害。次年,朱温又杀朝官三十余人,投之黄河,但当时仍用唐昭宗的“天佑”年号。{11}诮:责备。
本文是欧阳修于庆历四年(1044)写给仁宗皇帝的一封奏章。当时革新派范仲淹、杜衍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以夏竦、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被弹劾罢职后,不甘心其政治上的失败,广造舆论,竭力攻击、诽谤范仲淹等引用朋党。其陷害忠贤的险恶用心,深为欧阳修所洞察。于是欧阳修向宋仁宗上了这一篇奏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本文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
文章先从社会发展的事实落笔,“朋党之说,自古有之”,证明朋党的存在有其历史的依据,并为下文征引历史事实埋下伏笔,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那么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作者用“同道”“同利”鲜明地概括出两者的不同,使自己的观点十分鲜明。接着,在前一段基础上的深入剖析,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君子是真朋,小人是伪朋。这是由于,小人之朋是从利出发的,所以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假的;而君子之朋出于对道的共同追求,所以必然能“终始如一”,所以是真的。
同时,欧阳修指出“道”和“利”,是区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关键所在。小人是以利,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利益相同则相结为党,见“利”则相互反目,“利”尽则分道扬镳;而君子是以“道”相互联结,同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道永远不变,则君子之党永远同心。第三段主要是广泛列举史实,证明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结尾处大量引用事实的基础上,着重阐述迫害君子之朋则国亡,信用君子之朋则国兴的道理。
本文是一篇富有战斗性的政论,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历来享有盛名,为人称道。本文在写作方法上,有如下两大特色。
一是全文自始至终运用了对比论证的艺术手法,逐层深入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在开篇定下基调以后,就紧紧围绕着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步步展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无朋”是因其“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君子有朋’是由于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小人以利害相交,必然见利忘义,利尽残害。最后,文章还列举了从上古尧、舜之时直至唐末各个朝代盛衰的大量历史事例,围绕国家兴亡治乱与朋党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反复的对比分析。事与理的结合,对比手法的反复运用,起到了化深奥为浅显,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艺术效果。
二是文章转折句和排比句的交相运用,既纡徐有致,又富有感染力。本文气势磅礴,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富有忧患意识的政治家刚正不阿的战斗精神。但从其时徐时疾,张弛有度的说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欧阳修沉着冷静的大将风度,表现在其语言的运用、句式的选择上。在对比论证中,作者多处运用了转折句式,如第四段,连用五个“莫如”。这一系列转折句式的运用,不仅突出了对比的效果,而且使论述的笔调趋于舒缓,使文章既明白晓畅,又委婉而耐人寻味。这正是作者所推崇的所谓“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的政论的艺术风格。
后人评论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反反复复,说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末归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见人君能辨,但问君子小人,不问其党不党也。”
纵囚论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①,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馀人②,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③: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④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⑤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⑥,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⑦以干誉⑧。
【注】
①刑入于死者:指刑法定罪达到死刑者。入,指定以罪名,使受刑罚。②录大辟囚三百馀人:选取死囚三百余人。录,收集、汇集之意。大辟,古代五刑之最,死刑。{3}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死囚)到了期限而最终自己归宋,没有误期迟到的。{4}移人:改变人(的品性)。{5}纵:放纵。此指假释性地放出囚犯。⑥三王之治: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理民。⑦逆情:违背人情法理。⑧干誉:谋求名誉。
据《旧唐书·太宗纪》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将待执行的三百余死囚假释归家,并约定他们返回监狱受死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皆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死罪。这件被后世传为美谈的太宗“德政”,与唐太宗主张刑法宽简、死刑要严、赦令勿滥的一贯态度不合。为此,欧阳修也对太宗“纵囚”赦死的不合人情法理提出质疑,认为是矫枉过正了。
本文作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按照提出质疑、论述说明、提出自己的观点的顺序进行。体现了欧阳修论理文一向逻辑性强、结构严密的特点。
文章开始并不直设论点,而是先放开一笔,泛论君子小人之别,为全文的议论树立了一个参照标准;同时也藏下暗笔,以“罪大恶极”反照太宗释囚不通情理,以“视死如归”反照死囚自归不合情理。做到泛论不泛,紧扣论题。接着简叙纵囚之事,断以评议,又紧扣君子小人之别。
然后,欧阳修先肯定太宗“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的论述,提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的主张和措施。认为信义只能用于君子,对小人则要用刑法。因此,唐太宗纵囚使归的事是不合乎常情的,是现实中不大可能存在的事情,即使发生过,也只能是上下互相欺骗沽名钓誉之举,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定法。还特别指出,刑罚达到死刑者,那又是“罪大恶极”的“小人之尤甚者”,不可轻易宽赦。段尾以一句反诘句“此岂近于人情哉”,表达作者的不解和质疑,引发读者思考,同时总结上文,开启下文。
在其后的论证中,作者对太宗“纵囚”赦死之壮举进一步分析、批驳,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事是沽名钓誉,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
统治者违背情理以邀取名声,是否利于治国呢?这是末段议论的重点,也即本文的论题。文章同样没有直涉论题,而是先宕开一问,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与近情理之间的矛盾:归而诛之,如再纵又归,显然不近情理;如再纵不归,无从体现恩德,故以否定收断。最后,顺理成章地指出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