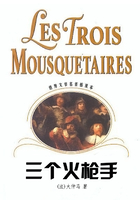“喜欢独处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说这话的人是想在寥寥数语之中,把真理和邪说放在一处,这是很难的。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心里有了一种天生的、隐秘的对社会的憎恨与嫌弃,则那个人不免带点野兽的性质,这是极其真实的。然而要说这样的一个人居然有任何神灵的性质,则是极不真实的。只有一点可作为例外,那就是这种憎恨社会的心理不是出于对孤独的爱好,而是出于一种想让自己退出社会以求更崇高的生活,这样的人在异教徒中我们曾经有所发现,如克瑞蒂人埃辟曼尼的斯、罗马人努马、西西里人安辟道克利斯和蒂安那人阿波郎尼亚斯,而基督教会中许多的隐者和长老则确也曾如此。但是一般人并不大明白何为孤独以及孤独的范围。因为在没有“仁爱”的地方,一群的人并不能算作一个团体,许多的面目也仅仅是一幅图画,而交谈则不过是铙钹丁零作声而已。有句拉丁成语略能形容这种情形:“一座大城市就是一片大荒野。”因为在一座大城市里朋友们是散居各处的,所以就其大概而言,不像在小一点的城镇里有那样的交情。但是我们不妨更进一步并且很真实地断言说,缺乏真正的朋友乃是最纯粹最可怜的孤独,没有友谊则此世不过是一片荒野。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意义来论“孤独”说,凡是天性不配交友的人其性情可说是来自禽兽而不是来自人类的。
友谊的主要效用之一就在使人心中的愤懑抑郁之气得以宣泄释放,这些不平之气是各种情感都可以引起的。闭塞之症于人的身体最为凶险,这是我们知道的,在人的精神方面亦复如此。你可以服萨尔沙以通肝,服钢以通脾,服硫华以通肺,服海狸胶以通脑,然而除了一个真心的朋友之外没有一样药剂是可以通心的。对一个真心的朋友你可以传达你的忧愁、欢悦、恐惧、希望、疑忌、谏诤,以及任何压在你心上的事情,有如一种教堂以外的忏悔一样。
许多伟大的君主帝王对于我们所说的友谊的效用之重视,在我们看起来实为可异。他们重视友谊,甚至往往不顾自己的安全与尊荣以求之。因为作为君主,由于他们与臣民之间地位上的距离的缘故,是不能享受友谊的——除非他们(为使自己能享受友谊起见)把某人擢升到他们的伴侣或同辈的地位,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有不便的。现代语中把这样的人叫做“宠臣”或“私人”,好像他们之所以能到这种地位,仅仅是由于主上的恩惠或君臣之间的亲近似的。然而罗马语中的字眼才能算是把这种人的真正用途及其擢升之由表达出来了,罗马语把这种人叫做“分忧者”,因为真能使君臣之间结成友谊的,正是做这样的事情的。我们又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事情并不限于懦弱易感的君主,即从来最有智有谋的君主,亦往往有与臣下中某人结交,呼之为友,并使旁人亦以君王之友人称之者;君臣之间所用的这种称谓就和普通私人之间所用的一样。
苏拉,当他为罗马的独裁者的时候,把庞培(即后来被人称为“伟大的”庞培者)擢升到很高的地位以致庞培自诩为苏拉所不及。因为有一次庞培为他的一位朋友争执政官之职,与苏拉所推举之人竞选,进而获胜。在苏拉对此表示不满而开始争吵的时候,庞培反唇相向,叫他不要多言,“因为拜朝阳的人多过拜夕阳的人”。在恺撒则有代西玛斯·布鲁塔斯,其影响之大,竟使恺撒在遗嘱中立他为次承继人,仅次于恺撒的孙外甥。而这人也就是有能力诱致恺撒于死地的人。因为在恺撒为了一些不祥的预兆,尤其是克尔波尼亚的一场噩梦的缘故而想使参议院先行散会、改期再开的时候,布鲁塔斯拉着他的胳膊,轻轻地把他从椅子上拉了起来,并告诉他说,他希望恺撒不要叫参议院散会,等恺撒的夫人做一场好一点的梦之后再行开会。安东尼在一封信(这封信在西塞罗的攻击演说之中曾经一字不移地引用过)里曾呼代西玛斯·布鲁塔斯为“妖人”,好像他用邪术迷惑了恺撒似的,他的得宠之深可见矣。阿葛瑞帕虽然出身微贱,但是奥古斯塔斯却把他升到很高的地位,以致后来当奥古斯都以他的女儿朱利亚的婚事问麦西那斯的时候,麦西那斯竟敢说“他必须把女儿嫁给阿葛瑞帕,否则就必须把阿葛瑞帕杀了。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因为他把阿葛瑞帕已造就得如此之伟大了”。泰比瑞亚斯一方面将西亚努斯升到很高的位置,竟至他们两人被称为一双朋友。泰比瑞亚斯在致西亚努斯的一封信里写道:“为了我们的友谊的缘故,我没有把这些事对你隐瞒。”并且整个的参议院给“友谊”特造了一座祭坛(就好像“友谊”是一位女神一样)以表扬他们两人之间的很亲密的友谊。此类或胜乎此的例子又可于塞普谛米亚斯·塞委·斯与普劳梯亚努斯的友谊中见之。因为塞委拉斯竟强迫他的儿子娶普劳梯亚努斯之女为妻,并且往往袒护普劳梯亚努斯种种欺凌皇子的行为,以这样的言辞下诏于参议院:“朕爱其人如此之深,愿其能后朕而死也。”假如这些君王是图拉真或马喀斯·奥瑞利亚斯一流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像上述的举动乃是出自十分善良的心田的。但是这些君王都是很有智谋、精神强健而严厉并且是极端爱己的,然而他们竟然如此,这就可以证明他们的幸福虽然已达人间之极峰,但是他们对之仍不满意,觉得若无朋友使之圆满,则这种幸福终是残缺不全的。更有甚者,这些君主都是有妻有子有甥侄的人,然而这些人竟不能使他们有朋友之乐。
康明奈亚斯关于他的第一位君主“勇敢的”查理,所说的话是不可忘记的,那就是,他不肯把他的秘密与任何人共享,尤其不肯把那最使他为难的秘密告人。于是康明奈亚斯又继续说道:“到公爵的末日将近的时候,这种秘而不宣的性情不免稍损他的理智。”其实,如果康明奈亚斯乐意的话,他对于他的第二位主子路易十一也大可下同样的断语,因为路易十一的隐秘的确是他自己的灾星。毕达哥拉斯的格言虽难懂但却是正确的,他说“不要吞噬你的心”。的确是这样,说得严重一点,没有朋友可以倾诉心事的人们可说是吃自己的心的野人。有一件事是很值得惊奇的,那就是一个人向朋友宣泄私情的这件事能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它既能使欢乐倍增又能使忧愁减半。因为没有人不会因为把自己的乐事告诉了朋友而更为欢欣者,也没有人会因为把自己的忧愁告诉了朋友而不减忧愁者。所以就实际的作用而言,友谊之于人心其价值真有如炼金术士常常所说的“他们的宝石之于人身”一样。这宝石,依术士们的话,是能产生种种互相反对的效力,总是有利于天性的。然而,即便不借助于术士,在普通的自然现象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的影子。因为物体相合则足以助长并滋养任何天然的作用,又可以削弱并挫折任何暴烈的外来打击:物体如此,人心也是如此。
友谊的第二种功用就在于它能喂养并支配理智,有如第一种功用之喂养并支配感情一样。因为友谊在感情方面使人出于狂风暴雨而入于光天化日,而在理智方面又能使人从黑暗和乱想入于白昼也。这不仅指一个人从朋友处得来的忠谏而言,即在得到这个之前,任何心中思虑过多的人若能与旁人通言并讨论,则他的心智与理解力将变为清朗而有别,他的思想的动作将更为灵活,其排列将更有秩序,他可以看出来把这些思想变成言语的时候它们是什么模样;他终于变得比以往的他聪明而要达到这种情形,一小时的谈话比一天的沉思效果更大——这些都是没有疑义的。塞密斯托克立斯对波斯王说:“言语有如一张展览的挂毡,其中的图形都是显明的,而思想则犹如卷折起来的花毡。”友谊的这第二种功用(就是启发理智),也不限于那些能进忠言的朋友(他们当然是最好的朋友了),即便没有这样的朋友,一个人也能借助言谈的力量自己增长知识,把自己的思想明白表现,并且把自己的机智磨砺得更为锋利,如磨刃于石,刃锐而石不能割也。简而言之,一个人与其使他的思想窒息而灭,不如向雕像或图画倾诉一切。
现在,为充分说明友谊的这第二种功用,我们再谈一谈那个显而易见、流俗之人也可以注意到的事情,那就是朋友的忠言。赫拉克里特在他的隐语中说得好,“光明永远最佳”。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诤言中所得来的光明比从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中所得的光明更要干净纯粹,这是无疑的:一个人从自己的理解力与判断力中得来的那种光明,总不免是受他的感情和习惯的浸润影响的。因此,在朋友所给的诤言与自己所作的主张之间,其差别有如良友的诤言与谄佞的建议之间的差别一样。因为谄谀我者无过于我,而防御自谄自谀之术更无有能及朋友之直言者也。诤言共有两种:一是关于行为的,一是关于事业的。说到第一种,最能保人心神健康的预防药就是朋友的忠言规谏。一个人的严厉自责是一种有时过于猛烈、蚀力过强的药品。读劝善的好书不免沉闷无味。在别人身上观察自己的错误有时与自己的情形不符。最好的药方(最有效并且最易服用的)就是朋友的劝谏。许多人(尤其是伟大的人们)因为没有朋友向他们进忠告的缘故,作出大谬极误的事来,以致他们的名声和境遇均大受损失,这种情形看起来是很可惊异的。这些人有如圣雅各所说,“有时看看镜子,而不久就会忘了自己的形貌的”。讲到事业方面,一个人也许以为两只眼所见的并不多于一只眼所见的,或者以为局中人之所见总较旁观者之所见为多,或者以为一个在发怒中的人和一个默数过二十六个字母的人一般的聪明,或者以为一枝旧式毛瑟枪托在臂上放和托在架上放一样得力,他可以有许多类似的愚蠢骄傲的妄想,以为自己隐身就很够了。然而能使事业趋于正轨者还数忠言。而且,假如有人想采纳别人的忠告,而愿意零碎采纳,在某一件事上问某一人,在另一件事上问另一人,这样的办法也好(这就是说,总比他全不问人的或者好一点)。可是他冒着两种危险:一是他将得不到忠实的进言,因为所进的言论必须是来自一位完全诚心的朋友的才好,否则鲜有不被歪曲而倾向于进言人之私利者也。另一种危险是他所得的进言,将为一种有害而不安全的言论(虽然用意是好的),一半是招致祸患的而一半是救济或预防祸患的。有如你生病请医,而这位医生虽然是在精心医治你所患的病症,却不熟悉你的体质,因此他也许会使你目前的疾病可以痊愈而将危害你健康的另一方面,结果是治了病症而杀了病人。一个完全通晓你的事业境遇的朋友则不然,他将小心注意,以免因为推进你目前的某种事业而使你在别的方面突受打击。所以最好不要依靠零零碎碎的忠告,它们扰乱和误引的可能多于安定和指导的可能。
在友谊的这两种高贵的功效(心情上的平和与理智上的扶助)之后还有那最末的一种功效,这种功效有如石榴之多核。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朋友对于一个人的各种行为、各种需要都有所帮助,有所参加。在这一点上,若要把友谊的多种用途很显明生动地表现出来,最好的方法是计算一下,看看一个人有多少事情是不能靠自己去办理的。这样计算一下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古人所谓“朋友者另一己身也”的那句话是一句与事实相较还很不够的话,因为一个朋友较一个人的己身用处还要大得多。人的生命有限,有许多人在没有达到最大的心愿——如子女的婚事,工作之完成,等等——之前就死了。要是一个人有了一位真心的朋友,那么他就大可安心,知道这些事件在他死后还是有人照料的。如此,一个人在完成心愿上简直是有两条性命了。一个人有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是限于一个地方的,但是假如他有朋友,那么所有的人生大事都可算是有人办理了。就是他自己不能去的地方,他的朋友也可以代表他的。还有,有多少事是一个人为了颜面的关系,不能自己说或办的!一个人不能自承有功而免矜夸之嫌,更不用说是不能表扬自己的功绩了。有时也不能低首下心地去有所恳求,诸如此类的事很多。但是这一切的事,从一个人自己的嘴里说出来未免赧颜的,从朋友嘴里说出来却是很好。类此,一个人还有许多身份上的关系,是他不能弃置不顾的。例如,一个人对儿子讲话就不能不保持父亲的身份,对妻子讲话就不能不保持丈夫的身份,对仇敌讲话就不能不顾虑自己的体面。但是一个朋友却可以就事论事,而不必顾虑到人的方面。这一类的事情要一一列举出来是说不完的。总之,一个人如果是有某种事自己不能很得体地去做时,我对他有一条权言可讲,那就是,如果他没有朋友的话,那么他只有“下台”这一种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