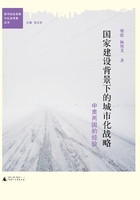$1929年前后第三党在四川的活动片段
黄子谷
1927年元月,我见到邓演达。当时,他是国民党军总政治部主任、武汉留守司令。这个时候,四川发展了5个军(20军至24军),但其中没有邓锡侯、田颂尧的军队。于是他们二人想活动一个军的番号,吕超劝我出面代表他们;吴玉章也同意我去,并介绍我去见邓演达。我向邓说明邓锡侯、田颂尧的要求,后又到庐山见到蒋介石。蒋同意任命邓锡侯、田颂尧为军长。当时,邓演达给我说:“你到邓锡侯的28军做政治部主任。”我就这样回到了成都。
吴玉章给我们28军政治部配备了几个共产党员,欧阳辑光任宣传科长,陈同生(当时姓名是张××,解放后任上海统战部部长)任组织科科员,黄××(忘其名,后去解放区)任组织科科员。“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们的处境不大好。军部与政治部摩擦很大,工作不能开展,我就不大想干了。“八一三”事变以后,四川的事情更不好办,我借口蒋介石委任邓锡侯为路司令,要我到路司令部做政治部主任,牛范九送来南京寄到的任命状,下午我就向邓锡侯表明我不能干了,从此就没有再去办公。邓竟擅自派刘景南继任,与我关系密切的同志都先后离开,约有一二十人。
一、黎明社和岷江大学
我辞去28军政治部主任后,从武汉、重庆退下来的人员,纷纷来找我。怎么办呢?我们就打算办个学校。1928年上半年,我们接收美术学校(校址在燕鲁公所),就把学校办起来了,起名为“岷江大学”。就在这个时候,武汉来了周澄波(训育主任)、夏子明(教书)。之后,岷江大学扩大了,有成都市东胜街、宁夏街和燕鲁公所三个校址。
南昌起义时,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曾用名)发表一个宣言,声讨蒋汪主张,继续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我们立即在四川响应。用“护党大同盟”的名义,继续拥护三大政策,声讨蒋汪。我们秘密组织了一个小集团,命名为“黎明社”,以政治干部为基础,其中主要负责人:黄子谷、旷继勋、黄聘三、李守白、董人宁等。黎明社办了一个《庸报》,宣传我们的主张,董人宁兼任社长,后来成为第三党(农工党的别称)的党报。
二、组织第三党
1928年冬天,我接到我的四弟黄慕颜从上海的来信,说邓演达先生最近准备约集一些国民党的左派和从共产党游离出来的分子组成一个新党,定名为“中华革命党”,他是发起人之一,要我在四川响应。
当时我在成都办了一所岷江大学。我就约了在岷江大学教书的周澄波、吕一峰、文光甫、董人宁(共产党员)等几个人作为四川的发起人。周澄波的主要关系是谭平山。周去上海也见过黄慕颜。周澄波从上海回来后,就组织我、文光甫、吕一峰、周澄波、董人宁五人成立第三党省委。我们组织起来以后对外公开活动的名字不叫“中华革命党”,仍然叫“护党大同盟”,我担任大同盟省委会的秘书(即书记),董人宁负责组织,文光甫、吕一峰负责宣传,周澄波负责对外联络。成都也成立了市委会,由董人宁、冉庆之负责。“护党大同盟”的主要任务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在四川来说就是反对“三军联合办事处”的一切反革命活动。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活动主要是按照《科学的三民主义》那本小册子进行的,上面有中华革命党的宣言和纲领,也有谭平山、宋庆龄、邓初民、苏兆征等人写的文章。记得做了这样几件事情:1.发展组织,培训干部。1929年底全川大概发展了100多个人,当然主要是成都、重庆两地。2.反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具体地说,就是采取分化的手法,把负责清党的国民党四川指导委员会弄垮了。3.支持工人的正义斗争,比如有一次成都的人力车夫为反对车行老板提高租金,开展了斗争,我们积极支持,取得了胜利。4.开展了学生运动。
当时,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准备对付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旋又改为省党务整理委员会。我多方利用熊子骏、李星辉、杨全宇、叶松石等改组派的关系,当他们要派人到县组织党务整理委员会,我们就给他们介绍人,如介绍德阳的戴新三、铜梁的熊公弼、宜宾的解维哲。其他县也这样做。表面上为他们工作,实际上是为我们开展工作。地方上,我们没有打出第三党的牌子。
三、党内的两派斗争
1929年春,孙侠夫到四川。他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成员,是第三党中央派来的。孙侠夫想在农村搞一个据点,发动农民暴动。因孙侠夫不是第三党四川省委成员,于是他让文光甫向省委会提出这个意见,但省委会没有通过。但孙侠夫硬要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周澄波反对很激烈,吕一峰、董人宁和我劝他不要搞。但省委会对他的擅自行动也未进行处分。我曾与孙侠夫谈,主张先把学校办好,打下基础。可是,孙侠夫不听我们的劝告,还大肆鼓吹要组织绿色国际,组织农民队伍。周澄波把孙的情况向第三党中央汇报了。
1930年四五月份,孙侠夫的妻子戴曙霞到成都,她带有一封信,说是邓演达写给我和吕一峰的,可是,没有把信交给我们。戴曙霞向孙侠夫说周澄波向中央告了他的状。第二天晚上,孙侠夫就自杀了。怎样自杀的,至今是一个谜。文光甫与一些学生教官造谣说孙侠夫之死是周澄波逼的。
孙侠夫自杀后,由文光甫、戴曙霞、王教官和学生20多人(有熊公弼、钱骏声等)准备搞农民武装起义。暴动那一天,他们宣布周澄波死刑。他们把周杀了以后,马上就出发到灌县与汶川交界的龙溪召开了农民武装大会,举行暴动,据说他们有300多支枪。四、武装暴动失败,岷江大学被查封
武装起义被邓锡侯的部队解决了。领导这次武装起义的文光甫、王教官、戴曙霞和岷江大学的二十几个学生全部被捕,关押在灌县江防军军法处。军法处长黄聘三(共产党员)与我是熟人,又是我二哥黄隐的部下(我二哥是江防军司令),他保证说:“我要负责保全他们。但你要出面到邓锡侯那里说情。”我去见邓,邓还讲交情,在我离开成都时,邓说半年以后释放他们。后来,邓如约把他们都释放了。文光甫、戴曙霞释放后到上海去了。
武装起义发生在5月份,6月份岷江大学就被查封了。学校被查封,除武装起义外,还有其他原因。旷继勋部队的起义,共产党员多,是我介绍去的;广汉起义,其中也有我的学生。这些都是被查封的原因。查封学校时,学生想搞游行示威,我不同意,怕酿成流血事件。岷江大学被查封后,邓、田、刘对我提出意见,要我同吕一峰一起离开成都。临行时,邓送了1万多元的旅费,并保证在路上不出事情。五、登报解散第三党
秋冬我们就到了上海,住在黄慕颜家。我见到了刚从欧洲回来的邓演达先生。后来,邓又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过一次饭,我们与邓交换了对革命的一些意见,双方观点分歧,不能统一。邓还劝我回四川,我说四川的第三党被孙侠夫毁了,岷江大学被查封了,自己又被迫离开成都,还能有什么搞头。
我们之间的分歧,归结一点就是邓先生认为国民党虽然反动,但还有力量,想把它作为基础,加以改造。他仍幻想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同时又是保定系的成员的他,能影响绝大部分黄埔军校学生,能号召一大批保定系在国民党军队内的将领,从而可以留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争领导权。而我们坚决反对这样做,我们认为革命骨干力量是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主张彻底抛开国民党,另起炉灶。我们的观点与谭平山的主张基本一致。当然,究竟将来应该怎么办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尤其是我在川所见、所做的所谓革命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之后,一时是颇感彷徨的。因此也只能一方面强调要宣传以三大政策为主要战略的科学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在组织方面则另起炉灶,在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骨干力量。
其后,在兴业里某处开了一个座谈会,有十几个人参加。因为意见无法统一,我们有几个人(我只记得有我、黄慕颜、吕一峰,其余与我们有同一观点的还有几个人,但记不清是谁了)坚决主张解散。之后,登报声明解散,我们也就各奔前程了。
(作者黄子谷,已故,原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副秘书长。本文成文于1981年)
$争取中间势力——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重庆与第三党的交往
杨力
1988年,我与胡康民(时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见义勇为,制止了一起公交车上的偶发事情,由此相识并多次交往。我向他谈了当年农工党史资料的情况,他对周恩来与第三党(农工党前身)在重庆交往的资料极为重视,他说这是周恩来研究的一个空白,他鼓励我深入地做这个专题资料的收集研究工作。那时我刚调入农工党重庆市委机关不久,接手农工党史工作,着手进行一些研究,与原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有过信函来往;在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方荣欣、原中央党史办主任肖翰香等老前辈来渝期间,曾详细地就有关问题向他们请教;我曾陪同肖翰香参观大足石刻,他给我谈了许多农工党史方面的情况;我有幸结识了农工党重庆市委的一批资深老前辈,如刘宗宽、李正清、彭伯通、周竞波等,我对他们作过多次深入的访谈,收集了他们掌握的书面材料;我还系统地查阅了农工党中央刊物《前进》和中共西南局党史书刊,对当时收集的所有档案资料进行检阅。在此基础上,我进行了分类整理研究,撰写了《争取中间势力——记抗战时期周恩来与第三党的交往》这篇专稿。1989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创办了月刊《红岩春秋》,全国政协前主席邓颖超为创刊号题写刊名。当时胡康民担任《红岩春秋》杂志社主编,在他的安排下,这篇文章在创刊号上公开发表。此后经过多次修改完善,在《前进论坛》《周恩来与四川》《重庆文史资料》《重庆政协报》等10多种中央或地方各级报纸杂志上发表或转载。这些成为我从事农工党史和政协文史研究的起点,是我的有影响的代表作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间势力的问题上是有过沉痛教训的。早在1930年,邓演达从苏联回国建党的时候,曾派人找共产党谈判,但未被接受。当时中共的“左”倾领导人拒绝与中间党派合作,“对其他党派的政策,没有加以区别,把他们一律看成敌人”,因而对第三党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致使两党之间形成了严重的隔阂,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最典型的莫过于1933年,在酝酿建立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时,第三党作为主要的策动者和参与者之一,首先提出“联共”的主张,并派人跟中共领导人联系,要求采取联合行动。但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拒绝与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合作,没有给予应有的援助,其结果是蒋介石集团在击败这个孤立无援的革命政权后,又回过头来加紧“围剿”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周恩来牢记这一沉痛教训,在抗日战争时期把争取中间势力作为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了与第三党等中间党派的合作。
自1937年底开始,周恩来在同国民党进行频繁谈判的同时,也与各中间党派初步建立了联系。在武汉,第三党的章伯钧、彭泽湘与中共的王明、周恩来代表两党举行会议,双方回顾了过去两党的关系,一致表示今后应密切合作,共同战斗,这就为发展两党的关系迈出了第一步。但在武汉时期,由于王明的影响,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事实上还停留在国共两党的范围,而忽视、冷落了中间党派,这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利的。
1938年9月,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湘和一批干部先后到达重庆,中央机关也由武汉迁来重庆,在重庆半山新村3号(今渝中区李子坝盘山公路旁)设立中央机关联络点。
1939年初,中国的政治中心由武汉转移到重庆之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建立,逐渐开创了与中间党派合作的新局面。周恩来当时很注重同第三党、救国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乡建派等党派团体建立联系,经常与中间党派领导人交往。尽管他们各有不同的经历,所代表的组织有各自的政治倾向,但周恩来总是平等相待,不断就国内外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以及国共两党关系等重大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逐渐消除隔阂,进而使中间党派和中共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可以协调行动,互相呼应。
1939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加强了团结中间势力的工作,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坚决与反共顽固派作斗争。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由主张抗日的各党派提出了七个有关宪政的提案。中共参政员同中间党派及无党派参政员共同发出了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的正义呼声。在共产党和中间党派的推动下,在大后方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掀起了第一次全国性宪政运动的高潮。这次会议后,由章伯钧、丘哲会同一部分国民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社会活动家,酝酿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是南方局成立后,对中间党派加强统战工作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中共领导人与中间党派人士经常聚会,了解时局变化情况,研究国内团结问题。12月25日,周恩来、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在章伯钧家会商时局及解决危机的办法。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的抗战形势进一步恶化,爱国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分裂政策十分失望,深感进一步团结起来,反对内战独裁争取民主自由之必要,认识到原统一建国同志会那一类松散组织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唯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第三者政治集团,才能有力地调停国共矛盾,坚持团结抗日。因此,章伯钧、丘哲向各方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一些中间党派的领导人纷纷同周恩来等“聚谈”或“正式谈判”,表达他们组织起来的迫切愿望及同中共合作的诚意。
1月中旬,章伯钧、丘哲代表第三党同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举行正式会谈,再一次向中共表示合作诚意,要求中共对第三党的纲领、组织和宣传以及经济给予切实的援助。中共代表表示完全赞同,答应给予种种支援。从此,第三党进一步靠拢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得到共产党的帮助和启迪,认定“共产党是抗战与民主中的最可靠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