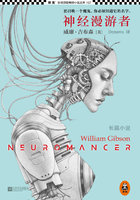第二天早上,利朋乘汽船去了夏兰顿,下船之后,很快他就找到了波瓦拉说的那家咖啡馆。进去之后,他要了一杯酒,坐了下来,旁边是一张大理石的桌子。此时,餐厅里的客人只有一位就是利朋,它的吧台在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正对着入口,因为没有客人,里头显得非常宽敞。
这时他背后的房间走出一个人,那是个留着白胡子的中年侍者。
“天气真好,不是吗?”侍者给利朋送来酒,放在桌上,利朋借机跟他搭讪说,“时间还早,还没到你们忙的时候。”
侍者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了。
“我是慕名而来的,听说你们的午餐很好。”利朋接着说,“我一位曾在这里吃过饭的朋友,对你们的厨艺赞不绝口呢。他那个家伙不轻易夸奖别人的!”
这下侍者高兴了,笑着鞠了个躬说:“提高厨艺也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能让你的朋友满意,我们真是很高兴。”
“他没把对你们的赞赏告诉你们吗?他这个人直来直去,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的!”
“抱歉,你的朋友是哪位,我不记得了。他几时来过这儿?”
“你会记得他的,这就是我的那个朋友。”利朋把波瓦拉的照片给他看。
“就是他吗?我是记得很清楚。可是,”他犹疑地说,“他并不没有如你所说,欣赏我们的厨艺,相反,从他脸上那个表情来看,是不怎么喜欢乡下食物的。”他一边说,一边耸耸肩。
“那时他的身体不太好,但他真的对这里赞赏有加。他来这里时好像是上周四,是吧?”
“上周四吗?我觉得应是更早一些。没错,应该是周一。”
“可能我记错了。不是周四,他是说周二,是周二,对吗?”
“可能吧。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总觉得应该是周一。”
“那天他还打电话给我呢。我印象中他一直在电话里夸的就是这家店,他是不是在这里打过电话?”
“倒是打了,还打了两次。我们店里装了部电话,专门给客人使用。”
“很体贴的服务。不过,他运气欠佳,赶上电话出了点故障。在电话里,我和他约好见面,却没见着他。现在想当时也许是我听错了。你有听到他在电话上说什么了吗?他是怎么说周二的约定的?”
侍者原本满脸笑容,友好亲切的,这时却警戒了起来,一脸的怀疑。虽然还是恭敬地笑着,但利朋感觉到,此时的他就像一只牡蛎,感觉到威胁缩回硬壳里去了。
“侍者总是忙个不停,我没时间听。”
利朋想这只是他的搪塞之词,他必须要改变策略了。马上,利朋不再和颜悦色,而是将声音放低,说:“听着,我是警察。调查那个人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是我的新任务。难不成,你要到了警察局才肯说吗?”接着,他拿出五法郎,“如果你告诉我,还可以得到酬金。”
侍者害怕了,惊恐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呀?”
“我知道你听见了。老实说出来,这五法郎就是你的,不说呢,我就带你去警察局问话。你自己选吧。”
侍者没有马上说什么。利朋看得出他在比较其中的得失,有些不知所措。看到侍者如此犹豫不决,利朋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推测,再给他施加点儿外力,他才能打消顾虑:“看样子,你是在怀疑我的身份?好吧,看看这个!”说着,利朋向他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证。
见到证件,侍者这才下定了决心说:“听他说话的语气,对方好像是个仆人。他跟那个仆人说,自己马上要到贝鲁基去旅行,让仆人给他准备什么东西送到北停车场。至于是什么东西,我就没听清楚了。另外他还说了一些其他的地名,并且他说在贝鲁基呆上两天。我就听到这些了。”
“很好,这些是你的了。”侍者收下钱,利朋从咖啡馆走了出来。
出来之后,利朋一边走一边想,结果和自己预料的一样。波瓦拉到的时候到底是周一还是周二,很容易查。管家和工厂的人都可以帮助证实,只要问问他们,波瓦拉打来电话时是什么时候就行了。
他就这样一直走到了夏兰顿车站,然后坐火车去了里昂,到站后又搭乘计程车去了香槟街,波瓦拉抽水机厂就在这条街上。到工厂时,正好是十一点半。光看工厂的门口,会觉得它不大,但从门口往里望,就知道其实里面很深。他迅速地观察着以便了解周围的情况。这儿是工厂唯一的出口。
一间咖啡屋坐落在离工厂五十码远的地方。利朋若无其事地走进去,选了一张靠窗的大理石桌子,坐了下来。从这里看去,办公室和工厂的入口一目了然。他要了一杯酒,抽出口袋里的报纸,身体往椅子上一靠,就开始看报了。但他表面上是在看报纸,实际上眼睛从没离开过那个入口。一有人经过,他就把报纸举起。在他悠闲地品着酒的同时,时间也一点点地过去了。
在工厂出入的人形色各异。一小时后,他已喝了两杯酒,也终于看到了他要等的人。办公室的门开了,波瓦拉推门走了出来,走上了去市中心的马路,这个方向正好和利朋所在位置相反。
过了大约五分钟,利朋将报纸慢慢收起来,掐灭了烟,从咖啡店走了出来,往办公室去了。进去后,他递上私人名片,说有事要找波瓦拉。
一位职员说:“真不巧,他才刚出去。你没有看到他吗?”
“没看到,也许是我没留意。如果他的秘书还在,我跟他谈谈也行。”
“我想可能还没走。稍等,我去看一下。”
不一会儿这位职员就出来了,告诉他秘书杜夫瑞还在,并把利朋带进了办公室。
秘书是位中年男子,利朋跟他说:“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和波瓦拉先生面谈一下。实际上,我有一些关于他个人的问题,想要问一下,但我没时间等波瓦拉回来。也许你能给我答案。顺便说一声,我是警察。”递上工作名片后,他接着说,“我正在查一个和波瓦拉先生有关的案件,要问的问题也是涉及到这个案子的。由于权力的限制,我不能把这案件的详情告诉你,请你谅解。以前波瓦拉曾去警察厅对案件做有关陈述,但当时遗漏了两个问题,原本我们以为那不重要,所以没有追问,但现在有必要查清。第一个就是周二时,他是什么时间离开办公室的。第二个是他什么时候从夏兰顿打电话回来说要去旅行的。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我只好在这里等着波瓦拉先生回来,请他当面告诉我。”
秘书没有应答。
利朋知道他在思考着要如何应对。于是接着说:“看来你不是很方便,算了,不要勉强了,我可以坐在这里等他。”
后面这句话起了作用。
秘书说:“别客气,如果不方便等还是不要等了。至少有一个问题我是可以回答的,不过另一个,我不敢肯定。波瓦拉从夏兰顿打来电话时,正好我在并接了电话,时间下午在两点四十五分左右。他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的,我不能确定。九点时他还在,要我拟一封答复函的草稿,那封信非常麻烦,要求又严格,他要的还很急。我仔细核对了每个数字,花了半个小时拟稿。九点半时,信写好了,可是我送进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这是周二发生的事吗?”
“是啊,是周二。”
“他是在周五早上回来的吗?”
“对。”
“谢谢,因为你的回答,我省下了不少的时间。”从办公室出来后,利朋步行往地铁站去了,他打算直接去市中心。但是调查进展顺利,使他心情很好。他又决定先不去市中心了,到奥玛大道的波瓦拉家去一趟。
到了之后,是管家开的门,他问候道:“弗兰索先生!又要打扰你了。不过这次两三分钟就可以,你有时间吗?”
“别客气,请进!”
管家带他来到小客厅,利朋拿出自己的烟来递给他。管家接过他的烟,利朋问道:“你觉得这烟怎么样,喜欢吗?有人嫌它呛,可是我非常喜欢。好了,言归正传,你上周二去火车站给波瓦拉送包时,有没有发现被人跟踪了?”
“有人跟踪?不,我没发现。”
“那人就在左边的行李寄存处,是一个高个男子,他身穿鼠灰色的衣服,留着红色的胡须,你看到这个人了吗?”
“没有,我没看到那样一个男子。”
“你几点存的包?”
“三点三十分左右。”
利朋稍微沉思了一下:“有可能是我记错了,这是周二的事吧?”
“对,是周二。”
“波瓦拉先生是在两点左右打来电话的吧?我印象中他是说的两点。”
“应该还要晚些。实际上,准确地说,应是快三点了。真是难以置信,你居然连我送手提包的事都知道?”
“昨晚,波瓦拉先生我和谈话时说过。他说要去贝鲁基的决定很突然,所以让你给他送手提包去,放在左边的行李寄存处。”
“那红胡子男子呢,是怎么回事?”
利朋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了,要自圆其说,编个故事也不是难事。
于是他笑着说:“那个人是我们的侦探。他正在那里侦查一宗案件,是关于装着贵重物品的手提包失窃案。我想也许你看到他了。波瓦拉回来时,他的手提包还在吧?没有东西被偷吧?”
管家也笑了,但笑得并不真诚,他好像知道了,利朋只是在开玩笑。
“没有,他带着包回来的。”
利朋心想,好了,玩笑就此打住!波瓦拉没有说谎,周二下午两点四十五分他打给管家电话,吩咐他送手提包,这是真的,同样他也真的去取了手提包。现在还有他周日与周一的行踪,和周一晚上打开桶子的事没有确认。接着利朋说:“还有件事要麻烦你。我要写报告,请你帮我对日期进行核对。”然后他拿出记事本,“我说事件,你只要告诉我对不对就行了。三月二十七号,周六,举行晚宴。”
“对。”
“二十八号,周日,没发生什么事,波瓦拉在晚上时打开桶子。”
“不对。他是到了周一才打开桶子的。”
“周一。”利朋随即更改了本上的记录,“周一晚上,对吗?周日晚上,他虽然在家,但等到了周一晚上才把桶子打开,对吧?”
“对。”
“他到贝鲁基的时间是,周二去周四回的,是吗?”
“是的。”
“太感谢了。”然后他又跟管家聊了一会儿。利朋越是跟这位老人接触,就越是信赖他,尊敬他。这位管家诚实可信,为虎作伥的事是绝不会去做的。这一点利朋深信不疑。
上午,他可谓收获颇丰,可是到了下午就颗粒无收了。出了波瓦拉家,他又去了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还去了餐厅,人们都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了。但周二的事情,波瓦拉说得都不假。再把他周三和周四的行踪调查清楚了,波瓦拉就能解除嫌疑了。为了得到确证,他不得不去布里歇一趟了。他先打电话,预约了一张当晚的火车卧铺票,然后又给警察厅打电话报告。
第二天一早,利朋就已经身在布里歇了。吃了早餐,他坐车往马里鲁去了。他不知道哈努曼家在哪,就去邮局打听。最后,还是一家商店的人告诉他的:“哈努曼家在距离这里四里地远的鲁番街上。过了十字路口,马路右边有一片树林,里面耸立着一座红顶白墙的房子,很容易看出来的。不过,今天恐怕你要扑个空了。”
“我很想见见他。”利朋说,“如果他不在,能见到他太太也行。”
“可能也不在。两周前,确切地说,到今天才正好两周,他太太曾来到我店里,跟我说:‘这两三周我要出去旅行,你就不要送货了。’看来你来得不巧。”
利朋向他道了谢,然后按照他说的找律师去了。从律师口中,他得知哈努曼在一家大型的民营银行工作,身居要职。出来后,他雇了一辆车去鲁番街了。过了大约十五分钟后,他在一幢漂亮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一看就知道家里没人,没有一扇门窗是开着的,门上有把大锁,窗帘都拉上了,把里面捂得密不透风。利朋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顺着门旁的道路,找到了三间小房,看样子好像是给仆人住的。他就近敲响了第一间房子的门。
门里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妇女探出头来,利朋问候道:“早上好。我从布鲁塞尔来,是专程来拜访哈努曼先生的,但他家的门锁了。请问他家有没有人看守,或者你能告诉我谁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我就是给他看家的,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出门前他跟我说,有信件的话,就往布鲁塞尔的麦奇耶银行转。”
“他出门多久了?”
“到今天为止,刚好两周。他说要在外面待三周,再过一周才会回来。”
“上周,我的一个朋友也来过,肯定也没见到他。你见过这个人吗?”利朋把波瓦拉的照片给她看。
“没见过。”
利朋还敲了其他两间房子,也没问到什么有用的,于是他就回布鲁塞尔去了。下午将近两点时,利朋来到麦奇耶银行,进入金碧辉煌的大门后,他出示了自己的名片,要求见经理。
过了一会儿,就有人给他带路,把他带到一位中年绅士面前。
简单地问候之后,利朋开门见山地说:“冒昧打扰你,是想向你请教些事情!哈努曼是贵公司的高级职员,请问他是安弗瑞特抽水机公司的波瓦拉的兄弟吗?今天早上,我特地去马里鲁拜访了哈努曼先生,但是他出门了。我们找他是有要事,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费尽周折非要见到他了。”
“哈努曼和波瓦拉是兄弟不假。虽然哈努曼跟我提起过波瓦拉,但我并不了解他,所以不知道他的事。不过,我可以把哈努曼现在落脚的地方告诉你,你自己问他。”
“太谢谢了!”
“他住在斯德哥尔摩的瑞贝奇饭店。”
利朋记录下来后,就道了谢从银行出来了。接下来他又走访了莫里剧院,正好售票处有人在。他问上周三的晚上上演的是不是贝利奥的《特洛伊人》,答案证实了波瓦拉说的没错,只不过预约记录上并没有他的名字。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断定他没来剧院,或许他来了但没有预约座位。
然后,利朋又去了马克饭店,波瓦拉说他是住这里的,他对职员说:“我和一位叫波瓦拉的先生约好在这里碰面,我想查一下他在哪个房间住。”
“波瓦拉先生?”职员似乎对这个人很陌生,他开始翻登记本,然后说:“这个人没在我们这里住过。”
利朋把照片给他看,说:“就是他,波瓦拉先生,从巴黎来的。”
“啊,这位先生啊,想起来了!他只是偶尔会来这里住。但是现在不在这儿。”
“难道是我记错日子了?”利朋一边查阅自己的记录本,一边说,“你的意思是,最近他都没来过吗?”
“不是。他上周在这住了一个晚上,这是最近的一次了。”
听他这么说,利朋好像非常不解,叫道:“这么说,今天我见不到他了!他哪天来这里住的?”
“稍等。”职员又在翻登记本了,“三月三十一号,周三晚上。”
“糟糕!看来是我记错了!”利朋感慨道,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有提到过我吗,我叫巴斯卡?”
职员摇摇头,给了他否定地回答。
利朋好像是在跟自己说话:“那晚他一定是从巴黎直接来到这儿的。”他转过身来问道,“你还记得那晚他到这里的时间吗?”
“记得。那时很晚了,估计有十一点了吧。”
“那么晚才到!这样赶来会不会太仓促了?万一要是没有房间了,怎么办?”
“不会的,他预订了房间。黄昏时,我们接到了他从安葩绣大道餐厅打来的订房电话。”
“五点以前打的吧?五点时我还见过他。”
“不是,没那么早,我记得接到电话的时间是在七点半到八点之间。”
“真是不好意思,占用了你那么多时间。我给他留个言,你帮我交给他好吗?”
利朋真是个有天分的表演艺术家。他经常给自己设定角色,扮演自如,演技纯熟。波瓦拉的言行中,经过查证的都没有虚假的成分。接下来,利朋要重点突破的是还未被证实的地方,比如在夏兰顿吃午餐之前,他真的去维桑奴森林散过步吗?散步后有没有沿着塞纳河逆流而上?还有在巴士第他到底在哪家餐厅吃的饭?他真的去过他弟弟那儿吗?这些都还有待查证。
第二天,利朋去了警察厅,向休威厅长汇报了调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