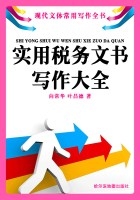83:月下吐心事
岳云看着她,只要轻轻伸手,就能把她拉住,纤细的皓腕正在视线间,衣角在夜风里微微飘拂,柔软地亦如他第一次看到小若时的心,再没有比她好的了,再没有了。
若殷缓缓地开门,关门。
疾风早已经自己回来,听得是她的动响,细细地打一个鼻酣,好似在笑。
手伸出去的时候,已经晚了一些,抓在空中,除了风,什么都握不住,岳云自嘲地摸一摸鼻子,即使伸出手去,恐怕也会被小若一巴掌拍开。
他已经失去那样的资格。
若殷立在门板后面,没有动。
不动,也不说话。
从门缝能看到岳云懊悔的表情一闪而过,不知是什么随着那样的沮丧扑面向她冲过来,好像小时候偶尔失足掉进洞庭湖中,躲闪不及的水花从口鼻钻进去,那般那般的不舒服,几乎透不过气来。
一直等岳云大踏步地离开,若殷将两扇门拉开,月色正中天,如银而泻,呼啦啦地泼洒下来,似乎可将心口的阴影缓缓吹散。
“疾风,你可睡了。”声音软得象折腰的眠花。
疾风甩甩毛,轻巧地走过来。
“怎么办呢,疾风,我怎么办呢。”若殷凑在那毛茸茸地耳朵边对它说,“小岳已经成婚了不是吗,我应该离他远点再远点。”
即使与岳大将军面对面地解开那个沉郁的心结,可是岳云终究是岳飞的长子,不去谈自己身上背负的整个寨子的人命,假如他们真的走在一起,有一天,多事之人查询起杨若殷的身世,只怕要牵连的又是整整一大家子的人。
这般的情景,只要一次,一次已经够人肝胆俱裂,痛不欲生。
若殷摸着心口,这个地方,再也承受不住同样的再经历一次。
他们都赞誉她冷静机智,处惊不乱,她亦同样是血肉之躯。
翻身上马,“疾风,带我远远地跑,没有方向,没有目的,不然。”不然在屋内只怕还是辗转不能入眠。
疾风心领神会地从小院柴门,撒蹄飞奔而出,若殷俯身,闭着眼,双臂扣在它的颈脖处,听得风声在耳边呼呼而过,疾风,跑得远些,再远些,一旦睁开眼来,来到全然陌生的地方,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情。
并未跑得多远,疾风放慢步子,停下来。
若殷尚未睁开眼,已经听到段恪的声音:“小若,这么晚,你怎么会来。”
疾风,你比我想象得好像更加聪明,若殷仰起脸,露出不太自然的笑容:“这么晚,你怎么还不睡觉。”
“正在整理抄录一些东西,写了两个多时辰,腰酸背痛出来走走,松松筋骨,正在想明明是无风的好天气,怎么感觉到好似有什么扑过来,原来是你们一人一马好兴致,来我这里坐坐?”
若殷顺势下马:“可有好东西招待贵客。”
段恪侧过头来想:“仔细找一找怕还是有些的,不过怕是入不得殷大姑娘的法眼。”
若殷佯装瞪他:“那还不快去找。”
“是,小的遵命。”
一待段恪背转过身,若殷下力对着疾风狠狠地踢了两脚:“坏疾风,让你多事。”嘴巴里说的凶,下脚是轻飘飘的,疾风是自己的宝贝,踢坏了,最心疼的人还是自己。
疾风果然不避不躲地,反而对着她又靠一些过来。
“你很得意是不是,我让你带我跑得远远的,你倒好,索性把我往段大哥这里一送,仔细我不要你了。”若殷总觉得疾风此时的表情可谓用得意两字来形容,强调地再补充道,“真的不要你了。”
“小若,又和疾风说话呢,我看它被你调教地都快成精了。”段恪左右手都端着东西,“还真被我找到好东西了。”
若殷连忙笑着应:“就来了,段大哥。”走前一步,袖子紧抽,低头去看,疾风叼着她的袖角不放,湿漉漉的大眼睛望着她,她拽一拽,疾风被牵动跟着移动半步,依旧不肯松口。
“小若,悄悄话,回去再慢慢和疾风说。”
若殷明白过来,摸一摸疾风的头:“好了,吓你的,不会不要你,疾风答应过要一直陪在我身边的,我怎么会舍得呢。”
疾风听了她的保证,才慢慢将牙齿松开,依旧紧贴在她旁边,一同走到段恪身边。
一碟子花生,一碟子醉鸡。
“家中无酒,只能以茶代酒。”段恪笑着替她将杯子斟满。
若殷轻轻喝一口,虽是粗茶也很清口,段恪夹了一块醉鸡放在匙中递给她,“我自己做的,你尝尝。”
若殷半信半疑地放进嘴里:“真的是段大哥自己做的,很香,肉质也紧。”
“那是在后山打的山雉,用花雕酒腌渍,原来做好也是给你送过去的。”段恪扔了几棵花生给疾风,“喜欢吃便多吃点,下次打到再给你做。”
“段大哥,你在岳府住得好好的,何必要搬出来,你义父不还住在那里。”
“那小若又为何要搬出来。”
“我是一个过客,不便多日叩扰。”
“我又何尝不是。七岁的时候被义父收养,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义父追随岳大将军保家卫国,将我留在岳府,与小岳同吃同住,一起习武念书,他有的我都有。”段恪将面前的茶杯转过半圈,“可我明白,我总是要离开,正如你所言,我们能做的是一个过客,那里并非你我的家。”
“家。”若殷淡淡地应道,家,她已经没有家了。
“小若。”段恪探过手,握住她的肩膀,是不是这一晚的月色太过美丽,让人的话语都变得魅惑而动听,“小若,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家,同样你也给我一个家。”
“段大哥。”若殷象是想躲开,一时又能躲得到哪里去,一片茫茫月色中,不过是两人一马的影子,被长长地拉在地上。
“小若,你喜欢的人是小岳吧,一直都是他。”段恪直视着她,不给她再一次躲避的理由,“你看他的颜色,同他说话的态度,你会和他发脾气,和他赌气,对我却一直温和有礼,款款笑意,起初,我还以为,你们象两个闹脾气的小孩子,后来慢慢地,我知道,那是因为你喜欢他。”
“我,我……”若殷说不出否认的话来。
段恪温柔地笑着:“我想不明白是什么让你们同时放开手,你与我一同去了韩世忠元帅那里,回来以后,小岳便定了亲,而你,眼睁睁地看着他娶了别的女子,仍然不声不响,他在婚宴中喝得不省人事,最后是被抬着进的洞房,小若,这些究竟是为了什么。”
“因为殷若不是我本来的名字。”瞒不下去了,也没有再瞒下去的必要,若殷咬着下唇,狠狠心,决定一口气从头说起。
好像说的是别人的故事。
洞庭湖水寨,杨幺的幼女,自小被众星拱月般细心养大,她以为及笄之年,读过万卷书,会跟随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先生去得很远很远的地方,行得万里路,又或是象子弦那般找一个英俊能干疼她爱她的人,相守一生。
幸福的东西只要一个刹那便能尽数摧毁。
刹那。
上天收回所有曾经给予她的一切,从那一刻起,她一无所有。
段恪静静地听她诉说。
原来。
原来真相比任何的想象更加残忍。
“岳大将军曾经告诉我,对朝廷的塘报中写道,杨若殷已经在押解回朝的途中暴毙身亡,就地掩埋,世间再没有我这个人,然而,然而我是活生生的人,总有一天,会被人挖掘出真实的身份。”
朝野中的事情,或多或少她也听得过一些。
当今天子眼中的岳飞,早已经是功高盖主的众的之矢,如若不然,怎么会在大师告捷的上下,允许首席功臣告老回乡。
可笑,岳大将军不过刚过而立之年。
告老从何而起。
那阙满江红,已经被收进重重深柜,再多的情绪已经关闭起来。
她,选择了退却。
小心翼翼,不愿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