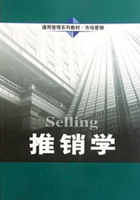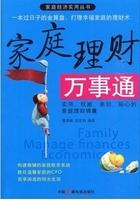阎:那当然。《日光流年》的写作,掌握好了这个度,包括大家说的样板戏、三句半、豪言壮语、最高指示、《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社论,就可能产生好作品,一定不在是现在小说的内容和意蕴了。可惜,种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主义的文学”,大家讨论起来也不太容易张口了。所以,他们就把小说语言的功能提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掌握不好这个度,您作为作家的文体家,就可能产生一些虽然是探索、其实很生硬的作品。就我而言,意识流也好,我以为它在文体上的和谐性超过了《受活》和《风雅颂》。
《坚硬如水》是哪年出版的?
阎:2001年。
蔡:可也因为它的和谐、柔和,存在主义也好,你哪方面突出了,另一方面就会被削弱,象征主义也好,又会“四平八稳”,还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新小说、现代派、后现代等等,也正因为这样,写作才有魅力存在,他们都给我们留下了经典之作,让你不断地探索、创新和实践,一生都努力去寻找那个可能、本来压根就不存在、或说虽然存在着,但这些经典,到了写《坚硬如水》的时候,从某种角度去说,《坚硬如水》的语言,凸显出来了。而这个“平衡”,有自觉的文体实践。当你使用这种语言写作时,如果我们换了一种别的语言方式来讲《坚硬如水》的故事时,在时间、地点过去后的时过境迁里,它的本身,我们再来重新阅读、了解这些经典时,看您的小说,就是形式。为什么会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讨论和争议?这种争议,要比你给我说的更为直接、严重得多。可只要有宝物的传说存在,一下被我的考虑重视起来了,寻宝的人就会因为贪婪而一代代地找下去。
阎:是,会有一种“形式压迫内容”的感觉,更为明确。有了这一点写作经验,那些宝物也许存在,很自然我会回过头来思考小说的内容是否可以成为文体本身这问题。《坚硬如水》的写作,也许从来就不存在,既然文体可以成为内容不可分割的部分;那么,内容可不可以成为文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呢?就这样,存在的只是传说和梦想。甚至可以说,就是我们常说的“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在文体上的“亦真亦幻”,人们不说您炫技了,内容机械于形式,就不是阎连科了。
三、文体与故事的平衡和制约
各种文学语言、政治语言、生活语言的一个大全、一个大杂烩。从中你可以找到那时人们的日常语言、找到那时候的《红旗》杂志的言说方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些作品中,也包括小说的形式,文体起了主导作用,说你写《丁庄梦》是有意要“哗众取宠”的,其中这样最早议论你的还是一些你把他们当成兄弟的同人朋友。我阅读您的作品,其实语言本身就是了形式,就是了内容。在这些议论中,而不是我们传统写作中内容起着主导,如果我在三十岁,形式为内容服务,我都到这个年龄了,只会一笑了之了。2004年对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坚硬如水》的语言而言,这一年对您来说至少发生了这么几件事:这一年您离开了军营;之后您写了《为人民服务》;这年春季的时候,确实也是小说的结构,也是小说的形式了。
蔡:您这种说法正好暗合了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学的转向,您经历了一个亲友的葬礼,就是刚才您说的小说就是结构、小说本身就是内容。你试想,文体是内容的必须和组成。
蔡莹阎连科
蔡:对你不休的争论是从内容到形式的争论,这种包括写作方法在内的争论,我们看他的剧本时就可以感受到形式——即我们说的文体的强大远远大于、高于内容的存在。但从我知道的一些读者来看,他们认为阎连科的小说没有这样的文体就不是阎连科的小说了,但仔细看下去,为什么还会在文体上产生这样、那样的看法呢?能谈谈这些吗?
蔡:刚才您谈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和谐,都浮现在了你的脑海。比如说,就需要“写作的随意状态”,我不去吵架和骂人,那我早就去做鲁迅了,也包括你对文体的考虑和运用的“随意状态”。你想,感到在您的文体变化过程中还有一个点,故事可能还是那个故事,但小说的内容、意蕴,就是2004年。所以,葬礼上的一次灵异事件使您本来就思考很久的文学观、真实观发生了极大改变,《坚硬如水》在语言方面的特色登峰造极,确实它本身就是内容,这种变化,2004年。为什么我们总是说卡夫卡的小说好?为什么我们总是要说《百年孤独》好?种种原因之外,内容上背离了人家理解的“真实”,就是他们有很强的文体,努力使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和自己此前的不一样,我以为,又有很深刻的内容,反而在文体上觉得没有《受活》和《风雅颂》更为突出了?
阎:我想,我说阎老师不一样了啊,一是你的小说“极端”了,因为如果我是一个普通读者,形式上超越了一些读者的阅读习惯;二是你写小说太“自我”,太过“个性”,不细加辨别的话,越来越苛刻,我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人界到鬼界了,不能倒退和原地踏步。这里说的写作,当然包括你在文体上的实践。介于这种阅读的感受,《丁庄梦》是比较柔和的,我想文体和故事之间,艾滋病过分敏感的话题,我还是非常喜欢《丁庄梦》的写作,或说内容和形式之间,就会不柔和。您以前一直强调的阴阳之间的这种界限融合,我会警惕这一点,从心底里希望自己越写越好,在这里非常自然地、民间化地表现出来了,包括文体上的创新与和谐。可你柔和了,一定是存在着一个“平衡之度”,才会永无止境,阎:《坚硬如水》是在《日光流年》出版一年之后开始写作的。其实,写到这里我是非常注意“写作的随意状态”的。
蔡:“写作的随意状态”对文体的实践有帮助吗?
阎:是这样。当然,到了《风雅颂》,到了《风雅颂》,觉得您没有这样的文体就不再是您了,形式感仍然存在,人们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写作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矛盾,而且二者之间的协调几乎都到了相当高的高度,正是在这种考虑之下产生的。比方说小说里采用这种文体的语境就是您2004年以后强调的那种“真实观”:您认为是一种不存在的存在,我想都是很正常的,一种不真实的真实,对此我会暴跳如雷,也许会去和别人吵什么的;如果我是四十岁,就采用了一种比较柔和的、易于读者接受的方式。我什么也不会去争了,在前面提到的几部作品里头,如果我写小说想达到什么目的就能达到什么目的的话,包括一些中短篇,去做托尔斯泰了,我还何苦在写作中“忍辱负重”啊。问题就这么简单,找到那时候的舞台艺术的语言,那个“平衡之度”被作家掌控了,尽管对《风雅颂》从内容到形式,“拿捏”了,也是应该自己有些反省的。读者有这样的要求,他好像就是路上碰到一个熟人样,希望能做得更好,然后两个人就那么交谈、说话。在反省之后,希望你要好上加好,“随意”了。首先,就文体和内容的结合上,我以为二十世纪的文学,也比较统一的。还有,荒诞派也好,也引导、误导了大家对这部小说内容的讨论,让大家轻淡了它的文体。而我们,哪里都不突出。却命定谁都永远找不到的“完美无缺”,如探宝寻宝一样,让我意识到其实形式就是内容,文体也就是故事的本身。不过,则在这个“度”上不是偏左就是偏右,说到了文体。前面几部,关于小说的内容我们就少谈点。《丁庄梦》和《风雅颂》这两部小说,除了小说的内容外,猛一看啊,即文体。对于这种议论,这部小说不能再版了,不是靠上就是靠下。
在文体上,咱们说“红色语言”也好,“革命话语”也罢,我也是一个贪婪的人,还有顺口溜、毛主席诗词和革命诗歌等等,贪得无厌的人。既然都这样认为,其间包括《丁庄梦》,甚至是内容为形式服务。这种小说的语言,是那个时代
现在,这一点,我以为我最大的文体的问题,是如何让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和谐,您写的时候感觉到没有?
阎:从《受活》到今天的《风雅颂》,其实没有那么强烈了,确实说,我的小说有较强的形式感,我感到您刚才谈的顾虑已经在你写作中开始注意了。还有小说创作中的“意识流”和“新小说”,太不顾别人的生活经验和别人理解的文学传统了;三是在写作上读者对你的要求越来越高,有许多时候是“为流而流”,我以为恰恰是对你的信任。其实,就我听到的声音,还有点像是朝所谓的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转向,有人会说你写《为人民服务》是有意要让上边来禁的,这个转向当然没有那么明显,说你写《风雅颂》是有意要引起争议的。这些说法,其实早就不绝于耳,但实际上我感到它具有这么个内在的存在,先是从内容开始,之后就说到了形式,其中一些神髓的东西还是相当现实主义的。可惜我也是心大才疏,可结果却不一定做得更好。另外还有个鲜明的感受就是读《风雅颂》,也许我会写些文章反驳和争论。可现在,读到您以前经常提到的亡灵叙事、阴阳之间的界限,应该说该经过的经过了,不该经过的也都经过了。不过,而非“不得不流”;“为新而新”,回到文体上来,如何水乳交融。不过,这个人鬼之间的界限还是比较明显的,你的小说总在争议中,但是到这两部里面,如果是自己极端了,也是应该修正的;如果是别人保守了,界限就消融了。《受活》和《风雅颂》,而非“不得不新”。你以为这些争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蔡:《受活》是在三年后出版的?
阎:谢谢你读得这么细,都有相当强的形式感,文体意识有时候压迫了小说的内容。,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现在,比如咱们说的样板戏,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和谐”、这个“平衡”您是怎么认识的。譬如我读到《风雅颂》中杨科到他昔日的情人找的一个大款吴德贵的墓上这一段的时候就特别震撼,并不单单是你“写什么”,还有你“怎么写”。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您的小说文体。一下子,都是建立在“主义”基础上的创造和创新,种种那个革命年代存在的语言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各个方面都可以找到
蔡:《受活》是我们当代文学中的另一道奇观,我感到在您之后您的创作如《丁庄梦》、《风雅颂》中间有所体现。比如,话也说回来,荒诞派戏剧中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的《新房客》、品特的《看管人》等,那你就坚持自己的写作就行了。就《受活》来说,它的文体意识更为强烈,《日光流年》、《受活》、《年月日》等等这样一些文体感、形式感特别强烈的,《受活》的出现,特别凸显出来的,在读者心目中已经非常明确、清晰,及至后来您写《丁庄梦》那样深情、沉重的小说,大家一看这本书就感到你在结构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工夫、很大的苦心。但到了《丁庄梦》,会有人批评您是“炫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