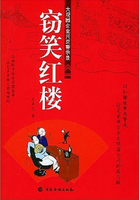一、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历史发展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就对认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对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方法和途径,知行的难易,知行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等问题,都进行了初步的研究,阐发了各种各样的知行观,成为尔后知行学说的源头。秦到唐代,哲学家们在知的来源问题上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形成了尖锐的分歧。西晋后,佛教各派的神秘主义知行学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宋至清代,由于统治阶级高度重视封建道德的教育和实践,和道德伦理密切融合的知行问题得到理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成为哲学战线的理论中心问题之一。不少哲学家阐发了系统而完备的知行观,由此也推动了不同知行学说的斗争。明末清初出现了王夫之、颜元和戴震等坚持唯物主义知行观的哲学家,对以往唯心主义知行观作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中王夫之更是作了总结性的批判。中国古代知行观经历了一个连绵不断、日益丰富的过程,而且独具特色,内容丰富。某些外国学者否认中国古代哲学有认识论问题,是完全不符合中国古代知行学说发展史的实际的。
二、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几个争论问题
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于知行问题的探讨,最主要的是知行有无先后、孰先孰后的问题,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有三种不同的主张: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合一。持前两种主张的哲学家所讲的“知”多指经验知识,提出后一种主张的哲学家(王守仁)所讲的“知”则着重指先验的“良知”,至于所讲的“行”,普遍是着重指道德实践。这也是中国古代知行观的一个基本特点。古代知行观的其他问题,如知行的轻重和难易的问题等,都是从上面关于知行的先后问题的三种基本主张衍生出来的,而且论定知和行在先者为重、为难,在后者为轻、为易。也就是说,凡持知先行后说的,一般都主张知重行轻和知难行易;凡持行先知后说的,则一般都主张行重知轻和行难知易。但是也有例外的复杂的情况。下面就争论问题作一总结性的说明。
(一)知行先后问题的三种不同学说:一是知先行后。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程、朱,他们强调先致知,后涵养。二是行先知后。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王夫之、颜元,他们都主张行而后有知,知从行出。从认识的基本过程来考察,知行的先后问题,直接涉及认识的来源和基础的问题,是在知行观问题上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基本问题。凡是持知先行后说的是偏于唯心主义,而持行先知后说的则是唯物主义。三是知行合一。孟子的“良知”说已含有知行合一的思想倾向,而王守仁则加以继承而发挥为典型的知行合一论。应当承认,王守仁猜测到了知和行的统一关系,是有辩证法因素的。但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基本上是奠基于以知为行的基础上的,因而是唯心主义的。应当指出,王夫之在认识来源问题上主张行先知后,而在认识运动、认识过程问题上又看到了知和行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相须,并进而有功,是比较正确和全面地表述了知和行的统一性。我们可以看到,王守仁和王夫之都主张知行统一,但其间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这也说明了知行的统一是不同的哲学家都可以承认的,问题是统一在知还是行的基础上,这也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重要问题。
(二)知行轻重问题的三种不同的主张:一是知重行轻。如程颐的“以知为本”说就是强调重知的。二是行重知轻。孔子已有这种思想的萌芽,墨家、王夫之、颜元都明确地主张行重知轻。朱熹虽和程颐一样,持知先行后说,但又和程颐不同,主张行重知轻。这也说明了古代同一学派的不同哲学家在知行观问题上的复杂性。还说明,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一样也是可以重行的。这种哲学史上的复杂现象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启示:在认识论和道德上重视行并不是判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键,在于是否承认行是知的基础和来源,是否承认知随着行的发展而深化。有的唯心主义者虽然也重行,但并不承认行对知的决定作用,仍然是唯心主义。三是知行并重。这是唯物主义者的普遍主张,其中如王廷相的“知行并举”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论点。此外,一些宗教家主张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并重,是一种特定意义的知行并重思想。
(三)知行的难易问题,这是一个与知行的先后,尤其是和知行的轻重直接相联系的问题。凡是重行,如唯心主义者朱熹和唯物主义者王夫之都赞同伪《古文尚书·说命中》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主张知易行难。程颐重知轻行,则主张知行都难,而实质上含有知难行易的思想。知行作为无限的认识阶段和过程,很难区分难易,只有在特定的范围内才有一定的意义。如对有丰富知识而缺少实践的人,或对有丰富实践经验而缺乏理论知识的人来说,强调行难知易或知难行易,才有某种现实意义。
三、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理论缺陷
中国古代知行观的主要缺陷有两个:
(一)没有真正了解实践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应当说,中国古代哲学家已经提出了实践这个范畴,如王廷相、王夫之、颜元都讲到实践。其中,王夫之讲的实践,虽主要是指个人的道德实践,但也包含了某些生产活动和社会历史的创造活动。如王夫之重视“厚生利用”的生产活动,强调与自然界争胜,“以人造天”,他说:“以天治人而知者不忧,以人造天而仁者能爱,而后为功于天地之事毕矣。”(《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九章)把“以天治人”和“以人造天”结合起来,人们的实践活动既要受客观世界的制约,又要努力改造客观世界。在社会历史活动方面,王夫之认为“君相可以造命”,而且“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德宗·三》)。不仅帝王将相可以创造历史,就是普通平凡的人也参与历史活动。此外,如王充、王安石等人也看到了劳动者生产经验的重要性。当然古代哲学家都不可能看到实践的基本涵义是指能动地变革、改造现实的活动,他们只是具有这方面的思想萌芽。我们既不能无视这些宝贵的思想萌芽,也不能混淆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实践范畴的原则区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道德实践是否应包含在实践范畴之内呢?我们认为是应当的。实践的内容是广泛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实践的基本内容是生产活动,在阶级社会里,则阶级斗争也十分重要,而科学实验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愈来愈重要。人们将会看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道德实践也是愈来愈重要的,社会主义的道德实践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古代哲学家之所以不能深刻了解实践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其原因,一是古代哲学家基本上都是学者,有的则是兼教育家、政治思想家,这种职业上的特点也决定了他们,大多数只集中于认识世界、说明世界,而不免忽视改造世界即实践的重要性。二是剥削阶级的立场决定了古代哲学家们,除了在革命阶段具有进取精神外,其保守性是长期的、顽固的,他们往往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协助王朝稳定和维护封建秩序为己任,而轻视、仇视乃至反对调整、改造社会格局的斗争。三是生产规模狭小,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靠天吃饭的成分很大,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不容易看到人在生产斗争中的作用和生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科学的实践范畴的提出,只有在工业化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才有可能。
(二)不懂得知行的辩证发展过程。除王夫之等少数哲学家对于知行的辩证运动有一定的了解以外,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家都不能揭示出由行→知→行的循环往复的无限运动,不懂得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史实表明,一些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由于没有坚持认识辩证法思想,不仅不能使自己的理论深化、提高,也不能有效地抵制唯心主义的侵蚀、进攻,有的甚至由此而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四、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特点
首先,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具有伦理化的倾向。中国古代知行观和西方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具有类似的内容和共同的规律。但是由于具体国情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也各有不同的特点。西方的知行学说较多地与数学和实验科学的研究方法相联系,而中国古代知行学说则较多地与伦理学说、道德修养方法相结合,呈现出鲜明的伦理化的倾向。这是缺点,又是优点。缺点,相对地说来,是较少与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联系(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影响和限制了对自然现象的探讨和认识。优点是重视人生的道德修养,有助于古代的治国安邦。为了克服缺点,对于当代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来说,加强自然科学的认识论问题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
其次,中国古代相当长时间内,佛教的宗教知行学说占十分突出的地位,这也是一个特点。佛教的知行观是一种神秘思想,但是如果净化其宗教内容,剥取其带认识色彩的思想因素,对于总结古代知行学说也是有意义的。
五、一点启示——哲学家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非一致性
一般说来,一个哲学家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是一致的,但是,中国古代知行学说史昭示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即在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中,认识论和本体论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墨子在认识论上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而在本体论上却是天志论。又如,张载在本体论上强调气的聚散形成万物,即以气(物质)为万物的本原,这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在认识论上,他却讲先验的“德性之知”,陷入唯心主义。在西方,康德也这样,他的本体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而在认识论方面则是唯心主义的。这说明一个哲学家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并不是都一致的。形成这种现象,是由于认识论和本体论是哲学中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问题,是属于不同序列的哲学问题。由于哲学家研究问题的重点、深度的差别,所受先行思想资料的不同影响,就容易出现两者不相一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