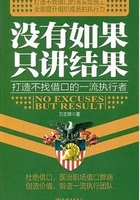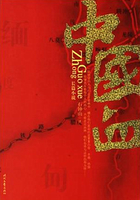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90915。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五“政通人和”历来是我国理想的政治理念之一。清人论政,极重求“通”。清代的一些谈论政风吏治的作品中,往往对“通”字给予很大的关注,并且赋予了相当丰富的内容。例如,陈宏谋的《从政遗规》和金庸斋的《居官必览》,都曾引用过“为政,通下情为急”这句话。袁守定的《图民录》则强调:“凡上下之情,通则治,不通则不治。”(卷3)还有人说:“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所以“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彭忠德、李正容编:《居官警语》,146页)。这里所说的“上下之交”而不“隔阂”,其核心内容也还是一个“通”字。
在当时,这些议论,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封建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尊卑悬殊,上下隔绝。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深刻揭露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君与臣隔,大臣与小臣隔,官与绅隔,绅与士隔,士与民隔,而官与官、绅与绅、士与士、民与民又无不自相为隔”。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既无心“询察疾苦”,老百姓也无处“陈诉利病”,举国上下,层层相隔,当然是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可言,整个社会就不能不呈“乌合兽散”之势。(《壮飞楼治事十篇》)康有为则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专制政治“如浮屠十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譬咽喉上塞,胸膈下滞,血脉不通,病危立至”。他得出结论说:“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上清帝第七书》)清代官德丛谈为政以通下情为急既然君臣之间、官员上下之间乃至官民之间的相互隔绝是由政治体制所决定,那么在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框架内,这种状况当然是无法根本改变的。清代政治伦理中所以大力宣扬通下情、尊舆论、顺民心的重要,正是力图通过政治道德的提倡和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去弥补、抵冲政治体制的弊端和缺失。这也正是这一政治伦理的积极意义所在,同时又恰恰是它的局限性的集中体现。
官民相隔、下情不通的最大弊害,是主政者井蛙观天,孤陋寡闻,视世情则管窥蠡测,察时势则如坐云雾。既摧残了民气,压抑了人们的政治活力,又堵塞了当权者的视听,杜绝了政治进步的通道。以这样自我封闭的态度去治国理政,犹如盲人骑瞎马,没有不出乱子的。所以有人把这看做天下最大的忧虑:“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是也。”(金庸斋:《居官必览》)如果不通下情,就不能及时察觉、处理与化解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还会使各种矛盾不断积聚和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造成“危亡之势”。这就把“通下情”提到了维护政治稳定的高度,在清代,不能不说是一个颇具卓见的认识。
封建政治的一大通病,是上下欺蒙,许多贪枉不法之事,往往由此而来。雍正时当过直隶总督的李绂在《与泰安各属书》中说:“居官大戒,第一蒙蔽。盖上下内外,非蒙蔽无以行其奸欺也。蒙蔽之在内者,有官亲、家人;蒙蔽之在外者,有猾书、蠹役。内外勾连,鬻情卖法,则为官者孤立无与,而坐听声名之败裂,其亦危险矣哉!”(徐牧、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卷1)不幸的是,这种“上下相蒙,只图苟免,全无后虑”的状况,已经成为到处皆然的官场陋习。“通下情”则正是打破欺蒙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这是因为,蒙骗只能施之于闭目塞听之辈,却难以奏效于耳聪目明之人。只要主政者能够博闻强识,洞烛幽微,宵小之徒就无所行其奸。陈宏谋《学仕遗规》中有一段话讲得十分透彻:“欲兴治道,必振纪纲;欲振纪纲,必明赏罚;欲明赏罚,必辨是非;欲辨是非,必决壅蔽;欲决壅蔽,必惩欺罔;欲惩欺罔,必通言路。所言虽未必可尽听,而人人皆得尽言,庶奸贪之辈,虑人指摘,不敢肆行无忌也。”(卷2)不通下情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政情扞格,政令不行。尽管封建政治充斥着尖锐的官民对立,但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与政治追求,还是提倡施政应以民为本。所谓“民之所乐,我则遂之;民之所苦,我则除之”(金庸斋:《居官必览》)。“事关民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蒋士铨:《官戒诗》)有的甚至提出“官必好恶同民”,“凡百姓所利,官亦曰利”,“百姓所苦,官亦曰苦”(袁守定:《图民录》,卷4)。可是,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根本一条,就是要了解与体察下情。只有真正懂得了老百姓的苦乐好恶,是非利害,一个关心民瘼的官员才有可能施惠民之政,行益民之举,这样的政治举措也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所以,《图民录》强调:“当官无他术,只务合人情,事之顺民情者可行,咈民情者不可行也。”“凡地方行一事,博采舆论,舆论可则可行,舆论不可则不可行。若咈众独断,则民必违犯,而事终柅矣。”(卷4)在“贵贱有等,上下有别”的等级观念及等级秩序的支配下,真正要做到“通下情”、“察民隐”,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需要有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勇气,放下架子,走出官衙,到“村镇篱落”、“穷乡下邑”,不论缙绅儒生、耆老隐逸,渔樵耕读、贩夫走卒、村姑童稚,都延访求教,“使民隐上通”。颇受雍正皇帝赏识的田文镜在所撰的《州县事宜》中发过这样的一段议论:州县官名曰知州、知县,顾名思义,必定要对一州一县的风土人情、物产生计、民生疾苦等“知之周悉,而后处之始当”。“故凡四境之内,毋论远近,或因公务出赴省郡,或缘命盗往来乡村,途次所经,必随事随时,详加体访。”“若深居简出,高坐衙署,使百姓难于见面,于一切物理民情,茫然无知,判然隔绝,不几负此设官之名乎!”(《官箴书集成》,第3册,682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陆陇其在《莅政摘要》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正德年间任南、赣、汀、漳诸州巡抚时,曾经把官员出行时的“肃静”、“回避”牌去掉,另举二牌,一个牌上写“愿闻己过”,一个牌上写“求通民情”。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肃静欲使无言,闻过则招之使言;回避欲其不见,通情则召之来见。”据说效果还不坏,“当时不闻以先生为亵体”(卷下),也就是说舆论肯定了这种做法,并没有人认为这就亵渎了封建官僚体制。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并没有十分坚实的依据,但人们乐于流传这个故事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一种意念,一种冀求。应该承认,在官员仪仗中去掉“肃静”、“回避”牌固属不易,要在头脑中取消让老百姓“肃静”、“回避”的观念,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对于老百姓的话,不但要能够去听,还要真正能听得进去,才能达到“周知民隐”、“体察民情”的目的,否则,就不免仅仅是一种政治作秀。所以大家都强调“通民情”的关键在一个“虚”字,就是必须虚心。“不虚则蔽”,“虚则生明”。觉罗乌尔通阿在《居官日省录》中说:“先哲云,官府政事繁多,下情阻隔,全在虚心体察。倘任其聪明,恃其刚介,挟其意气,种种皆能枉人。”“是以居大位而不虚心,则事坏;从政不虚心,则政坏;为学不虚心,则学坏。何也?意气太盛,虽有嘉言在耳,简册在前,不复潜心研究,惟凭私智臆见,谓操纵一切而无难,于是疏略偏蔽,百病交集,害有不可胜言者。”如果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趾高气扬,固执己见,“自视地位高于人,才识无不高于人,自是之见渐习渐惯,其尚能低首下心,勤学好问也哉?”这个警告,确实很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