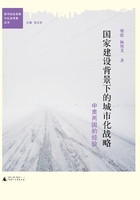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40406。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春天,直隶河南山东总督张悬锡,在参加完迎接义王孙可望的欢迎宴会后,一回到住处,就抽出佩刀,引颈自刎了。好在被家丁发现,把刀夺下,经过急救保住了性命。
担负着“总督三省重任”的堂堂封疆大吏,怎么会无缘无故地随意轻生呢?顺治皇帝得到报告,觉得“其中必有重大急迫情节”,便立即派人彻查。
调查报告很快就送了上来。表面的原因似乎很简单,说是张悬锡“迎节失仪,为学士麻勒吉所诘责,一时惶悚无地,遂引佩刀自决”(《清世祖实录》,卷117)。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有没有更加深刻的社会原因呢?
张悬锡虽然自杀未遂,但已抱必死之心,所以事前就给皇帝写了一封“遗疏”。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张悬锡这份“遗疏”不但值得一读,而且也道出了他轻生的缘由。
疏中说:“臣自莅任以后,矢心愿作忠良。喜怒不拂民欲,是非必告穹苍。意欲平治天下,谁知直道难行。清白招众之忌,戆直举国如狂。是以满腔愁郁,因而仪节乖张。自知此身必死,何如引咎而亡。”
清代官德丛谈总督张悬锡的自杀风波疏中又言:“臣家无余蓄,亦无良田美宅。莅任后不敢受地方官一钱,以负上恩。惜为人所误,亦天意耳!恭缴敕书关防,以及未用火牌等项,此外别无经手钱粮。”(《清世祖实录》,卷116)最后,这位总督提出,如真要“平治天下”,就必须“禁私征杂派及上官过客借名苛索之弊”,息“借假逃人之名以行诈”之风,以及“轸恤驿递”、严禁凌虐纤夫等。这里提到的,都是当时的一些突出的苛政,如高级官员每到一地,往往大肆勒索,地方官不但供应无术,还要遭受各种凌辱。在被逼无奈之下,有一些地方官愤而自杀。顺治十四年九月(1657年10月)的一道上谕就谈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谕曰:上官过境,“有司疲于奔命,勒索过当,除自尽之外,几无长策”(同上书,卷111)。
张悬锡在“遗疏”中虽没有对自己怎样“招众之忌”作具体说明,但在顺治帝的追问之下,他只得如实招来:“诸臣之待臣也不以礼。始而倨傲之,不与见;既见而鄙薄之,不与坐,不与言。侮辱情状,诚所难堪。然臣犹再三求见,再三求教,怡色下气,婉而受之。”
在张悬锡的自杀行为和他的“遗疏”中,最发人深省的是社会风气所具有的无形却威力巨大的力量。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能够使污浊的、丑恶的人和事受到鄙弃,受到谴责,受到孤立,受到惩罚。相反,如果贪黩和钻营之风弥漫官场,一个人想要清正廉洁,哪怕只是想洁身自好,也反而会遭到恶势力的嫉恨、排挤和打击。张悬锡的所作所为,展示给人们的就是一个一心想“平治天下”、对朝廷“矢心愿作忠良”、对百姓“喜怒不拂民欲”的好官,在一个恶浊不堪的社会环境里,不为官场所容,不受世俗所纳的历史形象。他关于自己“清白招众之忌,戆直举国如狂”的自诉以及“直道难行”的慨叹,其实质就在这里。
在那个时代,像张悬锡这样因不愿同流合污、力图洁身自好而遭受排挤、打击的,决不是罕见的特例。在康沛竹所著的《灾荒与晚清政治》中,就谈到过这样一件事:同治、光绪年间,有一位名叫苏廷魁的官员,平素一贯勤政清廉。在他担任河道总督期间,黄河在河南境内决口。他与河南巡抚一道,向朝廷奏请拨款100万两银子用于堵口工程。他亲自督工,积极备料,严禁贪污,决口很快就合龙了。最后决算,尚存余款30万两。大家知道,清代的“河工”,向来是个肥缺,从来都是“国家之漏卮,官场之利薮”,在这里,贪污不仅是司空见惯,简直是习以为常的。所以,河南巡抚主张把余款私分了事,但苏廷魁却坚持要悉数交还户部。巡抚因为“未遂其欲,恨甚”,便捏造种种罪名,上折弹劾苏廷魁。不料,户部对苏廷魁也是一肚子的气,因为按照惯例,报销河工,凡是浮冒虚报的部分,户部和地方官三七分成。苏廷魁实报实销,也就断了他们的财路。于是户部也百般挑剔,制造事端,同河南巡抚一起参劾。在内外夹攻下,苏廷魁最终落得个被“革职”的下场。(3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张悬锡的结局是耐人寻味的。顺治皇帝没有理会他革除苛政的请求,倒也没有追究他“失仪”“自尽”的罪过,只是说他“殊失大臣之体,本当罢黜,但念其素行清谨,姑著降三级调用”。麻勒吉因为“苛索挟逼总督张悬锡”,也得了个降二级留任的处分,也就是“各打二十大板”了事。就这样,张悬锡的自杀变成了一出小小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