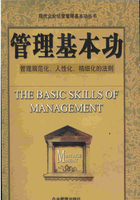老子非言无之无也,明有之无也。无之无者,是灭有以趋无者也,其名为断;有之无者,是即有以证无者也,其学为归根。夫苟物之各归其根也,虽芸芸并作,而卒不得名之曰有,此致虚守静之极也。盖学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即道;见色而不见空,故释明色即空;得有而不得无,故老言有即无。诚知有之即无也,则为无为,事无事,而为与事举不足以碍之,斯又何弃绝之有!(《澹园集》卷十四)
历代对《老子》一书的宗旨有各种解说。如唐王真以老子为兵书。焦竑的看法是,《老子》是“明道之书”。《老子》的宗旨在守柔贵雌,懦弱谦下,在于无为。但无为应是有无合一的,有无合一即有之无,无之有。有之无,是“即有以证无”,这相当于佛家所谓“色即是空”,非灭色以言空。灭色以言空,佛家斥之为断灭,庄子斥之为断。有之无,其宗旨在“归根”,“归根”即儒家所谓“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即万物皆在其本性的必然性活动而无乖违。这是“自然无为”,无为无事而为与事皆不碍其有。这样,庄子所极力抨击的仁义圣智可不必弃绝。焦竑这里的解释,实际上是对郭象“无心以顺有”、“有而无之”等有无统一理论的发挥。此外,焦竑这里将《易》之器即道、佛家之色即空、老子之有即无同等看待,又可以看出他会通儒释道的旨趣。《易》是儒家的形上学,道是其本体,器是其现象,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也。释家认为万物的本质是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但空之本体与有之现象圆融无碍。老子以道(无)为本体,以物(有)为现象,本体从逻辑上说在现象之先,因而比现象更根本,所谓“有生于无”。但本体与现象,有与无也是圆融无碍的。焦竑这里认为,儒释道三家在本体和现象的关系上说到底是一致的。所以,儒家之仁义圣智不必弃绝,佛道之出世也非必遗世独立,入世即出世,仁义圣智不碍清净无为。
在这一点上,焦竑借老庄而对儒家形上学有独特的理解,这就是,先进入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得到超然象外,绝然系表的“无”,然后再求其与“有”冥契。在这种超越境界的基础上所理解的仁义礼乐,就不像世儒所理解的那样肤浅。他曾说:
仁义礼乐,道也,而世儒之所谓仁义礼乐者,迹也。执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屏而弃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系表,而吾所挟者所以为也,庶几能进而求之乎有。如求之而有契焉,然后知象无非真,系无非理,仁义礼乐亦可以不必绝而弃之也。(《读庄子七则》,《澹园集》卷二十二)
先超系表,立象先,明仁义礼乐之本体,然后会通本体与现象,使本体现象皆真,融通无二,使重“无”而以现象为假、重有而拘执不化等等偏颇得到调和。
焦竑还认为,道家精神在无,这是不用讳言的,但道家之无正可以补儒家之有。而且这种补益,不是后世儒家见其有用而汲取之,而是道家老庄有见于儒者后学之不足而有意为之。他在《庄子翼》序中说:
孔孟非不言无也,无即寓于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谓下学而上达也。彼老庄者,生其时,见夫为孔孟之学者局于有,而达焉者之寡也,以为必通乎无而后可以用孔孟之有。于焉取其略而详之,以庶几乎助孔孟之不及。(《澹园集》卷十四)
就是说,有无统一,无即寓于有,这是孔孟老庄都见得到的道理。而二家路径不同,孔孟是下学而上达,就昭然明白的“有”这一面引导,由有而趋无。世儒局限于有,只见下学而不能上达。老庄有见于此,以为通乎无可以帮助理解有,故重点提掇“无”这一面。老庄实际上是在帮助孔孟。焦竑这一说法认为,孔孟老庄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路径不同,故各有提揭之侧重。这一意思在下面这段话中更加显豁:
老庄盛言虚无之理,非其废世教也,虚无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睹无者斯足以经有,是故“建之以常无有”。不然圣人之业将以成变化、行鬼神,而欲责之胶胶扰扰之衷,其将能乎!御有者必取诸无。(《读庄子七则》,《澹园集》卷二十二)
这里,焦竑是用王弼的理论去解释老庄与孔孟之互补的: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有物者不可以物物”,“无者斯足以经有”。儒家圣人大任在肩,必须有清净无为之心方能完成,所以必取无以辅有。由此足证老庄可以补益孔孟,老庄是孔孟的功臣而非反对者。焦竑指出,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不如苏轼眼光宏阔,司马迁说庄子诋毁孔子,而苏轼说庄子对孔子是“实与而文不与”,言语上批评而实际上赞同。世儒皆不知此,惟苏轼独具只眼,故苏轼之论“得孔孟之髓”。世儒所执者孔子之迹,庄子所论者是孔子之精意,故“尊孔子者无如庄子”。
从以上分析看,焦竑对于道家道教,也和他对于佛教的态度一样,屏除其属于宗教方面的东西,吸取其理论精华。道家思想养分也和佛教思想养分一样,是他学养中不可缺少的成分。而正由于儒释道三方面学养兼备,使他的思想呈现一种阔大而平舒的气象。他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态度,反映出明代后期三教融合的趋势。从这个方面说,他不是一般意义上儒家的卫道者,而倒像一个更平实、更全面、更不执门户之见的儒家之学的阐释者、发挥者。
四礼的形上学解释
焦竑融合儒释道三教和经史兼取的特点,使他的思想呈现不偏不倚的温和色彩。另外他欲惩王学末流猖狂自恣之失,提倡有规范、重仪制,故对于“礼”做了独特发挥。他的哲学宗旨“知性”同时就是“明礼”。
“礼”本是礼仪、礼节及社会等级名分借以表示的外在方面。儒家《礼记》一书,就是对于各种礼如冠婚丧祭等的解释与阐说。焦竑从形上学的高度对“礼”进行重新审视,把它解释成宇宙人心合规律性、合目的性这种特质,他说:
吾人应事虽属纷纭,乃其枢纽之者却是一物。所谓随时体验云者,于纷纭中识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马有衔勒,即纵横千里,无不如意。此颜子之所谓礼也。颜子功夫只是复礼。能约于礼,则视听言动头头是道,奚繁且劳之虑焉!(《答陈景湖》,《澹园集》卷十二)
这里,“礼”被解释成了“理”。在焦竑看来,礼是事物运作中表现出的节律、秩序。宇宙大化流行,万物各极其则而不乱,这说明宇宙运行有节律、秩序主宰其中。这种主宰并不具有人为的性质,也不是造物的安排,而是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这种自然而然、不得不然又是支配万物运行的所以然之理、所当然之则。所以“礼”即是“理”。不过“礼”重在秩序、节律义,“理”重在根据、本质义。孔颜之学精髓在复礼,体验者,体验此;依循者,依循此。在焦竑这里,礼不是外在仪节,而是人心本体,他说:
礼也者,体也,天则也。是礼也,能视听、能言动,能孝悌、能贤贤,能事君、能交友,可以为尧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万物。人人具足,人人浑成。所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乃其体自如是,非强与之一也。盖孔颜之学只是礼之为体认得精。认得既精,则真礼在我,一有非礼之礼自无所容留参杂其间。(《答友人问》,《澹园集》卷十二)
在焦竑这里,礼由于具有事物固有的节律、秩序之意,所以它是本体、天则。这个本体、天则同时又是人的道德理性,它是人的视听言动以及道德活动的根据。它既是道德理性、本体,所以是人人具有的。它同时是一种万物既相同一,又各具其性,“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的一体万殊境界。这又与《中庸》“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同一了。因为礼是本体,所以焦竑认为礼贯一切处。儒释道三教莫不有礼。礼在儒家不是修养道德的束缚,而是它的助力。这与释家戒能生定生慧同样道理。他说:
释之有律犹儒之有礼也。佛以六度示人,禅那特其一耳。而不知者欲以一废五,则其所谓一者可知已。何者,仁义以礼而立,无礼则仁义坏;定慧以律而持,无律则定慧丧。(《赠愚庵上人说戒序》,《澹园集》卷十七)
释家之戒可生定生慧,儒家之礼可立仁立义。阳明后学中的猖狂自恣派,以儒士而倡无碍禅,土苴道德,蔑弃礼法。焦竑斥责此派人说:近世一种谈无碍禅者,一知半解,自谓透脱。至其立身行己,一无可观,毕竟何益!此正小人而无忌惮者。(《古城问答》,《澹园集》卷四十八)
此派人在博与约的关系上,只看见约,不愿下工夫去“博学于文”;在礼与己的关系上,不懂得礼的本体论意义,把礼视作外在仪节规条而蔑弃之。焦竑认为“礼外无道,道外无礼”。老子曾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这是因为老子看到世人胶执于外在的度数礼
制而不知大道之实。若能返于道、返于实,抛弃虚文,则作为本体的礼与道本来是同一的。就博约与礼的关系说,礼是宇宙人心本体、本约,但此约不可骤得,必须由博以明。故博文之外无约礼。焦竑认为《中庸》“敦厚以崇礼”一句,最能道出儒家礼的精髓。敦厚者,博也;崇礼者,约也。敦厚是万物各极其则,崇礼是特别提揭其主宰者、纲维者。
从本体论上说,“敦厚以崇礼”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形上学概括说明。《礼记》一书,解说众礼,是博,是敦厚;而《中庸》一篇,虽未数数然言礼,但言礼之形上学,言性与道,言“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中庸》得《礼记》之精髓。儒家之精微处,全在一礼字。焦竑甚至认为,儒家六经,皆不出一礼字,他所说“礼者,体也,仁不可名而借于礼以名,如《易》之天则,《诗》之物则,皆名也”(《笔乘续》卷一),也是把礼上升到万物律则、主宰的高度。
焦竑对于礼所作的形上学解释,角度是全新的,这在明代儒家中是少见的。他的这种解释,与他的整个哲学宗旨是相符合的。统观焦竑一生,其仕宦生涯未见光彩,其学术则在明代后期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他的学术广泛涉猎儒释道及经史,而能加以融通。他可以说在泰州之学中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