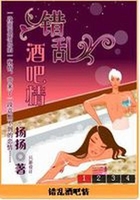皇帝急忙把自己的披风披在同昌身上,“同昌,以后不许这么任性,你的身子单薄,怎能如此折腾!可知父皇是多么心疼吗!”相比梅灵,皇帝更愿意叫同昌这个祥瑞的名字。
“同昌只是一时情急,母妃向来心高气傲,怎能忍受如此的不白之冤,此时定是心中郁结,怕是会憋出病来!”那郑公公也在一旁进言:“公主所言极是,方才老奴见娘娘神情恍惚,面容憔悴,真是凄凉不已!”那同昌公主更是心急如焚:“父皇,此事一定要尽早查明!”
那皇帝也连连答应:“同昌,此事要太后发话才可,这样,明日一早朕去求见太后,今夜皇儿就安心歇着吧!来人,送公主回宫!”不想公主撒起娇来:“父皇,同昌不想回去,一个人又要胡思乱想了,同昌要父皇陪着!”
一旁的昭容死死地拽着衣角,忽生恨意。那皇帝听得公主这样说,哈哈一笑,“同昌真是调皮,好了,就在这陪着朕吧!”“那父皇要陪同昌玩叶子戏!”“好好好,朕一定奉陪!”说罢父女俩手挽手去了棋室。
郑公公望了一眼呆呆站立的王昭容,不禁摇摇头。“昭容娘娘,看来今夜要委屈娘娘睡在偏殿了!”王昭容咬住下唇,气急败坏的走出飞霜殿。这个同昌,她是故意的!
翌日一早,公主就拉着皇帝来到长乐宫。太妃正在梳洗,得知皇帝与同昌公主来访,不禁微微皱眉。同昌公主一见太妃就急急跪下:“太妃,求太妃放过母妃,这件事一定不会是母妃做的!”那太妃虽然不喜欢郭淑妃,但是这公主却是异常痛爱,也许是公主真的是福星,自她诞生之后就好运连连。太妃温柔地拉起公主:“同昌,不是哀家要拿你母妃怎样,而是当时不幽闭你母妃实难堵悠悠之口。哀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太妃,同昌知道此事母妃嫌疑最大,件件指向母妃,但请太妃细想,如今既无人证可证明是母妃所为,连物证一并全无,实在不能让人信服!”
皇帝也说道:“母妃,此事不能单凭在鸣鸾殿发现水儿的尸首就断定是淑妃所为!”太妃叹了口气:“哀家也不是老糊涂,哀家早已命羽林军统领郭亦华仔细调查,相信不多时就会水落石出,尔等稍安勿躁!”
“太妃,若一时半日不能查明真相,母妃岂不是都要幽闭,同昌怕母妃熬不住!”太妃冷冷一笑:“后宫众人,必要禁得起喧嚣,耐得住寂寞,你母妃得宠了这么久,也该清净清净了!”说罢看了皇帝一眼。
那同昌公主见太妃这么说,连皇帝也责怪了,唯有小心说道:“同昌不求能放了母妃,可是同昌思念母妃,愿陪伴母妃!”太妃不胜其扰:“你要去就去吧,哀家还要去佛堂呢!”说罢拂袖而去。
却不说这杨璃瑜在合欢殿中也是百无聊奈,忽然来了两位丽人,原来是新册封的两位采女,杜采女和陆采女。那杜采女长相甜美,娇憨可人,一双明眸清澈见底,体态丰盈,笑容满面,让人如沐春风;陆采女却是清冷淡漠,眼神迷离,但别有一番风韵。
那杜采女娇笑道:“美人姐姐,你我好不容易做了邻居,一定要互相照应才是,今日风和日丽,不如我们去御花园游玩一番,好过闷在房中!”碧月和秋蝉正在烦恼怎么开解杨瑜,听了杜采女的话也连连称是。那陆采女也道:“不过是没有侍寝而已,不必如此吧!”那碧月一听,就大叫:“陆采女此话何意!”
杜采女连忙打圆场:“陆姐姐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想劝劝美人。”碧月正要发难,杨瑜一摆手:“妹妹所言极是,不过是侍寝不成而已,何必如此!”杨瑜见陆采女言辞直接,不懂修饰,反而觉得她真性情,多了几分欣赏。
陆采女看见杨瑜微笑的眼睛,也心中觉得亲昵。三人就结伴游御花园了。御花园中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美不胜收。那杜采女如孩童般兴高采烈,一会儿感叹,一会儿又尖叫,玩的好不开心。
突然,传来阵阵琴声,音乐就象远天的暮云,高空的飞絮,飘渺而又幽远,接着就象百鸟争鸣,明媚的春色中,震颤着宛转错杂的啁啭的歌喉,唯独彩凤不语。
瞬息高音突起,曲折而上,曲调转向艰涩,好象是每走一步,都很艰辛,正当步履艰辛之际,音声陡然下降,恍如一落千丈,掉入了深渊,声音嘎然而止…
杨瑜不禁惊呆了,后宫竟有如此琴艺高超之人,杨瑜循着琴声来道了染月亭。原来是韩国夫人在此听曲。只见那演奏之人是位风度翩翩的少年,风采不凡。
杨瑜在一旁如痴如醉,浑然忘我,一曲罢了,杨瑜已不知不觉走进亭中。
那少年见有人前来,微一抬头,不禁愕然,原来那杨瑜已是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