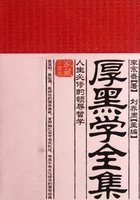——論張華文學及其玄儒思想
秦躍宇
內容摘要:張華作為西晉重要作家,鍾嶸《詩品》將其列入中品,並批評“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深入研究張華所處社會思想環境,就會發現這並非公允之論。張華玄儒兼治的入世言行精神內質類似於嵇康對名教的執著,其政治實踐體現的道家思想並非是他的文學作品的真實寫照,即“風雲氣”並不少;我們也不能夠通過具有“兒女情”多的文學創作,證明他是一個類似於王衍之類清談誤國的苟且隨時者。
關鍵詞:張華文學玄學儒學
張華,字茂先,西晉“太康文學”著名作家,《晉書》本傳云:“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其文學成就堪稱“是西晉尚繁縟、重技巧風氣的第一位代表”[1]。但是,以鍾嶸《詩品》為代表的理論批評往往對其具體作品評價不高,甚至有時還頗有微辭。《詩品》將張華詩歌列入中品,並評曰:“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從鍾嶸對曹植、左思等人的推崇,不難看出,其所不滿意者乃是指張華個人內蘊氣質稍遜“三曹”與“七子”創造的建安風骨。所謂“風雲氣”,有研究者以為是“英雄氣”[2],具體來說應該是指從漢樂府到“建安風骨”進而為“左思風力”所繼承的,關注社會直面現實慷慨激昂的創作風格。相對而言,所謂“兒女情”則是關注個人逃避現實具有消極傾向的思想流露,從而形成閑散平淡的作品風格。如果深入到張華所處的客觀社會思想環境,那麽就可以簡單把這兩種風格傾向歸納為儒家和道家精神的體現,這正符合玄學盛行國政昏暗的西晉現實。
我們以為,由於涉及張華思想研究及其命運的評價往往流於簡單化的批評,語焉不詳,使得人們對其文學作品的誤解具有因人廢言式的嫌疑。如果從玄儒兼治的角度分析,張華思想與權貴賈謐收羅的“文章二十四友”之潘岳、石崇、陸雲等人實難相提並論。張華生活的主要時期大約相當於玄理演進的中朝玄學階段。其基本形象是入世的名士。相較於袁巨集《名士傳》記載中朝名士群體結合名教與自然的入世人生態度,張華是當時能夠比較好地會通儒學、玄理於政治生活實踐的代表人物之一。
張華文學創作著述頗豐,《晉書》本傳謂:“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十卷,今存輯本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所收《張司空集》一卷。張華主要作品基本可見於清人嚴可均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五十八,今人逯欽立先生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三。縱觀張華詩文賦,除去一些應制作品,明顯體現出了當時玄風正熾的痕蹟,例如《答何劭詩三首》: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綏為徽纏,文憲焉可逾。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發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玩倏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其一)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群生。明暗信異姿,靜躁亦殊形。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竅所好,文學少所經。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其二)
這些詩句表達的的希玄忘世消極人生態度是毋庸置疑的,就其外在形式而言已經很有玄言詩的意味了,而張華的其他詩歌有時就直接用“遊仙”或“招隱”作為題目,思想內容自不待言。論及張華思想的玄學自然恬退傾向,學者一般還會選用《鷦鷯賦》、《輕薄篇》、《歸田賦》等作品加以說明,具體表示如“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鷦鷯賦》);“人生若浮寄,年時忽磋跎。促促朝露期,榮樂遽幾何”(《輕薄篇》);“眇萬物而遠觀,修自然之通會,以退足於一壑,故處否而忘泰”(《歸田賦》)。以上這些詩賦很好地證明了鍾嶸之批評所謂“兒女情多”。可是問題在於,只要我們放眼張華現存全部作品,則不難發現所謂“風雲氣少”未必盡然。例如《壯士篇》:
天地相震盪,回薄不知窮。人物稟常格,有始必有終。年時俯仰過,功名宜速崇。壯士懷憤激,安能守虛沖。乘我大宛馬,撫我繁弱弓。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素霓,嘯吒起清風。震響駭八荒,奮威蚋四戎。濯鱗滄海畔,馳騁大漠中。獨步聖明世,四海稱英雄。
其他包括《博陵王宮俠曲二首》“歲慕饑寒至,慷慨頓足吟。窮令壯士激,安能懷苦心”;“生從命子游,死聞俠骨香。身沒心不徵,勇氣加四方”,表現出的慷慨豪情可以說不亞於建安諸子的雄健筆力。其實,古人早已有提出對鍾嶸觀點的質疑,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說:“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沈德潛《古詩源》則直接表達了否定意見:“茂先詩,《詩品》謂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此亦不盡然”[3]。今天的研究者也部分指出了問題所在,徐公持先生說:“詩中有宣揚禮法者,亦有敷演玄禮者,思想駁雜,不一而足……這反映了張華內心經常存在矛盾,思考出處問題,首鼠兩端。”[4]玄理與儒學雜陳交錯於張華的文學創作,這已經是大多數研究者的一個共識,例如通過解讀《答何劭詩》,“有助於揭示西晉士人心態的發展變化歷程:即從建功立業的濟世豪情到既仕慕隱的彷徨心態,最終進入朝隱的消極狀態”[5]。張華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了玄儒兼治的思想結構。
姜劍雲先生《太康文學研究》基本否定了張華並蓄儒道的人格與政治表現:“在他的政治行為中,他雖然不像明哲保身者那樣唯唯諾諾,毫無原則性,但他的鬥爭精神也就止於諫諍。以暴烈的鬥爭方式,捨生取義,在他還做不到,患得患失,觀望僥倖,以待時變,苟且求安,不能不說乃機智玄學家們因時推移、隨遇適變心態在張華身上的具體反映。”[6]從張華的人格與行事結果出發,推導出其“鷦鷯”式特性決定了他的文學創作“雖辭美可稱,而不能脫於世網,可為文士追名者戒也”[7]。我們以為這些意見確實揭示了張華作品中委命順理、與物無患的玄學傾向,但是這樣批評一方面缺乏陳寅恪先生研究古代思想主張的“同情之理解”,未能真正換位思考體會張華實際處境之艱難;另一方面,也有對張華玄儒兼綜思想構成存在一些誤解,未能真正把握其近於裴頠“崇有”理論並導向郭象“名教即自然”玄學命題的精神實質。
作為任運自然、優遊卒歲人生態度在政治生涯中的對應體現,經常被研究者提及以说明張華缺乏慷慨磊落英雄氣概的重要事件是兩廢賈后未遂。裴頠是朝中重臣,劉卞是禁兵將領,他們先後與張華謀廢賈后,“乃必行且可行的壯義之舉,然而張華猶豫顧慮,錯失良機,誠可謂千古恨事也”[8]。徐公持先生則嚴辭指責:“張華晚年仕於暗主虐后之朝,不知進退,甚獲戀棧之譏。”[9]我們先從理論層面來看,張華自身學識修養鑄就的人生價值理想,是否真的會僅僅因於貪戀祿位而導致“不知進退”。魏晉時期,身處亂世的士大夫們對自身出處行藏的思考一直是玄學清談以及理論關注的焦點問題,其實“名教”與“自然”對立統一命題的現實政治意義明確指向就是“進退”選擇。關於“進”,如何進取有為,張華“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晉書·張華傳》),他的思想態度亦可以從他的朋友裴頠玄學理論獲知一二。張華與裴頠共事已久,最終同是死於趙王倫篡逆,二人既為官場知己,政治見識自然心有戚戚。裴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名士之徒口談浮虛,不以物務自嬰,以致風教陵遲,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崇有論》結合玄學“貴無”理論闡述“名教”規範於現實社會秩序的合理必然,提出了“以有為體”觀點。裴頠的目光更多集中在“以有為用”範疇,針對貴無放達極端行為,強調“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張華近儒思想相通於此,在愍懷太子被廢事件中體現尤其明顯,他與裴頠苦爭不從賈后之謀,“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晉書·張華傳》),這其實可以視為“以有為體”落實於現實政治層面的匡救時弊之功效。關於“退”,如何謙退自潔,張華“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晉書·張華傳》),我們可以從與他行事多有相似之處的山濤窺見一斑。山濤居官,勤於政事而能儉約自守,既能積極入世行不違俗,又奉道家處柔不爭平和守中政治哲學,世故深沉之餘不失清正樸素。他主選舉之事,位高權重,陳郡袁毅貪濁賂遺公卿,亦送之絲百斤,山濤不欲異於時,乃受而藏於閣上,後東窗事發推檢至其身,山濤“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晉書·山濤傳》)。《晉書》本傳云山濤顯達之後,“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奉秩,散之親故”;太康四年死後,左長史范晷等上書說:“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以至皇帝專門“為之立室”。這與“有台輔之望”的柱臣張華為官清廉自持何其相似,《晉書》本傳云,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機篋”。《世說新語·賞譽》注引顧愷之《畫贊》評論說“濤有而不恃”,其實同樣適用於評價張華。有而不恃,出於《老子》第五十一章“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張華行事正有此意。對於玄理的體悟,張華隱秘的道家思想就像山濤身上作為儒家價值倫理的補充一樣存在,是與俗世現實融於一體。這正如王衍品評山濤“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世說新語·賞譽》),張華雖未投身清談之場自標玄遠,但其實對老莊之旨深有會心。那麽,史書概括張華“器識弘曠”應該是涵括了其人格存在玄學化的內蘊,他對“進退”路徑與結果瞭然於心。張華貫通玄儒,進退有據的恰當操作,甚至專權的外戚集團都表示了認可,“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眾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晉書·張華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