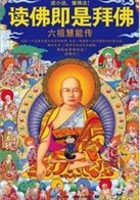综观中国佛教绘画,大体上可以分为像和图两大类。像主要是佛像、菩萨像、明王像(佛、菩萨的愤怒像)、罗汉像、鬼神像(天龙八部像)和高僧像等。图有佛传图(绘画释迦牟尼一生的教化事迹)、本生图(绘画释迦牟尼在过去为菩萨时教化众生的种种事迹)、经变图(描绘某一佛经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故事图和水陆图(悬挂在水陆法会殿堂上的宗教画)等。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经变图和水陆图的内容。经变是中国佛教艺术的一项创造,它促进了绘画艺术技巧和样式的发展,又摆脱了佛传和佛本生故事的范围的限制,开辟了更广阔的反映现实生活与创造新的形象的天地。如著名的“维摩诘变”,是依据《维摩诘所说经》绘制的图画,描绘了维摩诘居士与文殊师利等辩论的生动场面,表现了维摩诘居士的无碍辩才。顾恺之作维摩诘居士像,正是在崇尚清谈的魏晋玄学的影响下,表现博学善辩的典型人物形象。又如,唐代净土宗流行,相应地净土变相在寺院壁画中也表现得很多。在净土变相中,画家们把西方极乐世界描绘得非常壮丽:七宝楼台、莲池树鸟、香花伎乐,一派富丽堂皇、秀丽庄严的景象,这和佛教的苛严戒律、苦行禁欲大相径庭,正是唐代宫廷生活和人民愿望的曲折反映。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凡是与儒家伦理观念相吻合的故事、绘画,都得到广泛的流传。如“睒子本生”故事,记述迦夷国王入山游猎,误射正在山中修行的睒子,睒子临终时,仍念念不忘双目失明的父母无人奉养,后来果然获得天神的药救,死而复生。这则宣传孝道的故事是南北朝时极为流行的佛画题材之一,它还常与传统的孝子故事混杂在一起,被编入《孝子传》等图书里。水陆图一般分上堂和下堂两部分,上堂有佛像、菩萨像等,下堂有诸天像、诸神像、儒士神仙像、城隍土地像等,是集佛道画的大成。下堂中诸天和诸神像大部杂有道教画,是佛道合流的艺术表现。从中国佛教绘画中,可以看出中国佛教思想的演变轨迹。
佛教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是显著的、重要的。它不仅在形象上创造了许多典范作品,新创别开生面的形式,而且丰富了绘画的题材。这些题材的内容无疑是宗教性的,对人民产生过消极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应当明确的。但是也应当指出,在佛教绘画的宗教内容中,也表现了特定的积极精神,这就是艺术家们以丰富的想象力,通过佛画表现了生活中的欢乐与苦难、情感与希望,表现了人们的坚强、镇定、忍耐、牺牲的宝贵品格。如“维摩诘变”,表现了以热烈的辩论,追求“真理”的精神;“降魔变”则表现了以坚定的力量,去克服困难,镇服邪恶的信念。
§§§第四节佛教音乐
音乐通过有组织的乐音所形成的艺术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我国古代儒家十分重视音乐,《乐经》被奉为六经之一。《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乐记》和荀子《乐论》也都强调音乐的怡情悦性、陶冶心灵、教化人民、改善民心的作用。秦汉统治者设音乐官署“乐府”,武帝时的乐府掌管朝会宴飨、集会游行时所用的音乐,兼采民间诗歌和乐曲。我国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就广泛流行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八戒中有“歌舞观听戒”的约束,但是为了投合中国人民对文化生活、艺术欣赏的要求,为了宣传佛教和募集布施(化缘)的需要,也十分重视佛教音乐。中国佛教音乐家们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逐渐地熔历史悠久的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于一炉,形成了以“远、虚、淡、静”为特征的佛教音乐,并成为民族音乐的一部分。
佛教音乐是伴随着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这些传入的佛曲和中原地区的语言及音乐传统不相适应,不能配合用汉语译出或创作的歌词,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僧人就采用民间乐曲或宫廷乐曲,来改编传入的佛曲,或者是直接创造新佛曲,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的佛教音乐。后来,一些专长歌唱的僧人,一方面不断地吸收传入的佛曲,尤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又不死守佛教的旧曲调,善于创新,不断地补充新的佛曲,从而使中国佛教音乐获得不断的发展。
前面已提到,梵呗是模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用汉语来歌唱的。这种赞叹歌咏的唱腔,富有艳逸的音韵,旋律性强。史载,南朝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曾“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南齐书》卷40《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所谓“经呗新声”,就是佛教乐曲。梁武帝萧衍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也是佛教音乐家,他曾制作《善哉》、《神王》、《灭过恶》、《断苦轮》等十篇歌词,“名为正乐,皆述佛法”(《隋书·音乐志上》)。这些宣扬佛法的歌词,可以配佛曲演唱。北朝也流行佛教音乐,如北魏佛教很盛,佛寺众多,“梵唱屠音,连檐接响”(《魏书·释老志》)。“屠音”即“浮屠”(佛教)之音,就是佛教音乐。寺院经常演奏佛教音乐,是南北朝佛教的普遍现象。
隋代宫廷设置“七部乐”和“九部乐”。七部乐名是国伎、清商、高丽、天竺、安国、龟兹、文康的音乐。后改清商为清乐,又增加疏勒、康国两部,为九部乐。七部乐和九部乐中有少数民族乐舞,也有外来乐舞。天竺乐有舞曲《天曲》,《天曲》就是佛曲。这表明有些佛曲已在社会上流行,并为宫廷燕(宴)乐所采用。九部乐后为唐代所沿用,并增加高昌乐,为“十部乐”。隋代还出现了“法曲”。法曲由“法乐”发展而成。因系用于佛教法会的音乐,故名“法乐”。法乐是原西域各族音乐传入中原地区,与汉族的清商乐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以清商乐为主、吸收佛教音乐因素的法乐,后来发展为隋代法曲。乐器有铙、钹、钟、磬、幢萧、琵琶等;演奏时,金石丝竹先后参加,然后合奏。唐代法曲又掺杂道曲而发展到极盛。唐玄宗酷爱法曲,曾命梨园弟子学习,广为演唱。
唐代佛教空前兴盛,佛教音乐也日趋繁荣,并完成了全面华化。都市中有些著名的大寺院既是宗教活动的基地,也是百姓娱乐活动的游艺场所。唐代的“戏场”就多聚集在寺院里。僧人经常举行俗讲活动,演唱变文,还演出歌舞小戏、杂技幻术之类。在众多的艺僧中涌现出不少高手,其中唐德宗时的段本善就是最突出的一个。相传,德宗贞元年间长安举行盛大演出,时号称长安“宫中第一手”的著名琵琶演奏家康昆仑在东市彩楼演奏,获得极大的成功。此时一位盛装的女郎出现在西市彩楼上,她将昆仑所弹《羽调绿腰》移入更难奏的《风香调》中弹出,激昂辉煌,昆仑惊服,拜请为师。这位女郎就是扮成女伎的和尚段本善。这表明了唐代寺院中燕乐技艺的修养、琵琶演奏艺术,已达到出神入化的高度。诗人元稹在《琵琶歌》中曾高度赞扬段本善的上足弟子李管儿,说:“管儿还为弹《六么》,《六么》依旧声迢迢。猿鸣雪岫来三峡,鹤唳晴空闻九霄。”由此也可以想象段本善高超的艺术修养和风格。又如唐长庆年间俗讲僧文叙,善于采用乐曲演唱变文,声调宛畅动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唐·赵璘《因话录》卷4)文叙表演的说唱音乐曲调成为了当时教坊作曲艺人学习的典范。
唐代佛教艺僧还极善于吸收、利用民间音乐来宣传佛教,为佛教服务。如唐贞元年间净土宗名僧少康,“所述《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譬犹善医,以饬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之入口耳。”(《宋高僧传》卷25《少康传》)这表明中国佛教音乐主要是取材于民间而获得发展的。
北宋以来,搜集整理和传播民间音乐的工作,从官府艺人转到民间艺人手里。民间艺人组成了自己的团体,也有了固定的表演场所,称为“瓦子”或“瓦肆”。从此佛教寺院里的戏场也就逐渐转移到瓦子里了。但是有的大寺院还有戏台,也举办庙会,仍有音乐活动。佛教音乐仍然继续吸收民间乐曲和外来乐曲,来充实自己。元代盛行南北曲(南北曲:南方和北方的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合称。),为此后佛教的歌赞所采用。明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公元1417—1420年),僧人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50卷,就采用了中国内地的古典乐曲和流行乐曲300多首。在明王朝的倡导下,京城一些寺院都有管乐,如智化寺的管乐拥有单个曲调100多个。常用乐器为管两个、笙两个、笛两支、云锣两副,再加上鼓、铛子、铙、钹、铦子(小钹)等打击乐器。自1446年建寺之日起,智化寺音乐就以十分严格的师徒相传方式保存下来,至今已有28代传人。该寺演奏音乐曲调既有悲怆的宗教色彩,典雅的宫廷情调,也有浓郁淳朴的民间音乐的韵味。近年北京成立佛教音乐团,佛教音乐随着发掘、整理工作的开展,而得以恢复,并开始向欧洲介绍,获得普遍好评。
佛教音乐对于某些人信奉佛教起了感染、诱发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古代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贫乏枯燥,常借寺院的节目活动、庙会、戏场演戏,获得艺术欣赏和艺术活动的机会,佛教音乐对活跃人们的文化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与此相联系,佛教寺院在一定程度上是民间音乐的集中者、保存者、传授者和提高者,佛教音乐对于保存和发展民间音乐起了有益的作用。
佛教艺术是为宣扬佛教服务的,但是,艺术也并不完全是宗教的奴仆。无数有名无名的艺术家在描绘、塑造艺术形象时,总是要渗透进自己对生活的认识、态度和感情,体现人间的审美理想,反映在神权禁锢下人的主体意识的朦胧觉醒,从而表现出人间的光明,给人们以新鲜活泼、飞跃腾动的美感。应当肯定,中国佛教艺术同样闪烁着古代艺术家的智慧之光。坐落在深山密林或闹市街头的寺塔、佛像、壁画,这些煌然大观的艺术瑰宝,是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