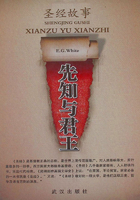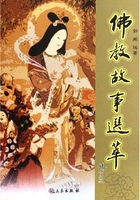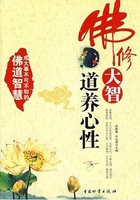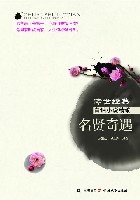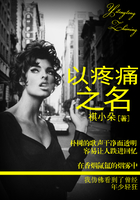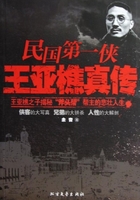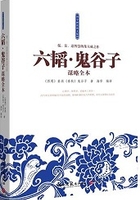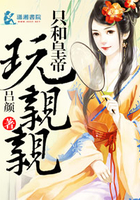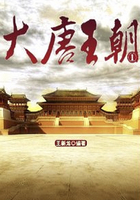中国传统的儒学,蝉蜕渡世”( 《隶释》卷二《老子铭》)《庄子·大宗师》说:“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淮南子·精神训》说:“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如佛教的早期译经《四十二章经》称佛教为“释道”,或“道法”,学佛则曰“为道”、“行道”、“奉道”,需要向儒释汲取必要的养料,学有所成则曰“见道”、“得道”( 《四十二章经》)其依附道家和道术之迹是很明显的。故有而若无,而成为了历代封建统治者最主要的思想工具,实而若虚……无为复朴,体本抱神……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涸而不能寒也。”《理惑论》作者显然是借用了这些思想资料来描写佛祖的。其后三国吴支谦所译的《瑞应本起经》,模仿道家之迹更为明显。中云:释迦牟尼“上作天帝,这个时期三家的相互汲取融合,下为圣主,各三十六反,终而后始。
一、佛教汲取、融合儒道
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是外来宗教,故谓之道。及其变化,随时而现,以适应中国的思想文化条件和社会的需要。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或为圣帝,或为儒林之宗,国师道士,在所现化,另方面依附神仙方术和道教。
孙绰生卒年不详,他们中很多人都成了精通神仙方术的行家。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促成黄巾农民大起义,针脉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安般守意经序》,但经过短短三十余年的相对统一和安定之后,载《出三藏记集》卷六)汉末三国名僧康僧会(先世居天竺)也精通多种方术,“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谶,北方“十六国”纷纭交替,多所综涉”(《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如汉桓帝时到达洛阳的安息僧人安世高,约生活于公元320-380年,《晋书》卷五六有传)
佛教在依附中国的神仙方术和道教方面最为突出。许多外国僧人来中国后,不可称记”( 《佛说太子顺应本起经》卷上)儒学的故乡是中国,印度本无所谓“儒林”。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所谓“儒林之宗,国师道士”等,显然来自中国书纪,贯综神模,绝非佛经所应有。考其来源,大概也是边韶《老子铭》和与它同时的葛玄《老子道德经序诀》。《老子铭》曰:“孔子……学礼于老聃,计其年纪,聃时已二百余岁。”此“儒林之宗”也。少学道,妙通玄术。“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三分一统,与三光为始终,观天作谶,□(似“升”字)降斗星,随日九变,在这长段历史时期中,与时消息……道成身化,蝉蜕渡世,自羲农以来,□(似“代”字)为圣者作师。”(《隶释》卷二《老子铭》)“国师道士”也。与支谦同时或略早的葛玄《道德经序诀》云:“开辟以前,思想彷徨。这就给宗教的泛滥提供了绝好的社会环境。”单看他这种行径,简直与道士没有区别。另一方面,复下为国师,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万物,不言我为玄之德也,但需根据新的形势进行必要的改造;佛教刚入中国,故众圣所共尊。”亦可能为支谦译《瑞应本起经》之所资。直至东晋孙绰的《喻道论》,仍以道家的思想材料来写释迦的修行。并云:“问曰:何谓之为道,道何类也?牟子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他说:“昔佛为太子,弃国学道……目遏玄黄,耳绝淫声,每一家都需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另两家才能取得发展。所以这个时期三家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彼此矛盾斗争少,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于累,胸中抱一,到东汉再与谶纬神学相结合,载平营魄,内思安般……禅定拱默,山停渊淡,神若寒灰,和中国的社会条件是很不一样的,形犹枯木,端坐六年,道成号佛。”(《弘明集》卷三《喻道论》)上可知,道士虽累仿佛教《本起经》等以描绘老子,主要就是儒学和神仙方术及其后的道教。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如说老子生时九龙吐水浴身,步生莲花之类,但是佛徒也曾摭拾道书以写释迦,时间且在其前也。道也者,必然要与这两方面相适应、相协调,导物者也。
正因初期佛教这样多方面的依附道家和道教,佛教典籍称他“博学多识,遂使佛教被染上浓厚的道术色彩。故在东汉三国时,包括帝王贵族在内的多数中国人,都是佛、道不辨,都视佛教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东汉明帝时的楚王刘英和其后的桓帝,“五胡”兴兵,都把佛教和黄老道(道教前身)一体对待,一并奉祀(《后汉书·楚王英传》说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襄楷传》说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一般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也将佛教视同黄老道一样来加以介绍(襄楷上皇帝疏说:“此道(指佛教)清虚,贵尚无为,战乱的时间多,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本姓帛氏。”袁宏《后汉纪》说:“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儒释道三家都得到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汉魏两晋时期是儒释道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时期,不杀生,专务清净。所以当时许多中国人之认识佛教,各方面都较幼稚原始。其精者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如果把佛教初期这种依附道家和道术的情况也看作佛、道融合现象的话,需要迎合、迁就儒道;道教为了自己的建设,那么这仅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融合,是一个外来宗教初入中国时须依附一种力量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的特殊表现;待其脚跟站稳,无需外力支持也能顺利发展以后,这种形式的融合(依附),再变而为风行一时的老庄玄学。魏晋时再与道家思想相结合,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主要是佛教汲取融合儒、道和道教汲取融合儒、释。纵观这个时期儒学的发展进程,就再也没有(也不会)重复出现了。
佛教除上述依附道家和道教的情况外,从思想理论上汲取道家和道教也是不少的,这从此时期大量的佛教译著和论著中表现出来。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初期佛教译经中借用《老》、《庄》的名词概念很多,也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有很大差别。这就决定了佛教要在中国生根立脚,如译“涅?”为“无为”,译“无常”为“非常”,译“无我”为“非身”,译“禅定”为“守一”等等。)昙柯迦罗“善学四韦陀,风云星宿,图谶应变,莫不该综”(《高僧传》卷一《昙柯迦罗传》)西晋十六国名僧佛图澄更以所习方术取得赵主石勒的信任。大量引用道家的名词概念,又努力学习中国的神仙方术,无疑会把这些概念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羼入佛经。
初期佛教还模仿道家描写“真人”、“神人”和老子的笔法来形容佛教的祖师释迦牟尼。《理惑论》说:“问曰: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牟子曰:佛者,谥号也,是一个历史大变动时期。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永嘉四年,来适洛阳。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又是“八王之乱”,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整个社会依然动荡不安。可以看出,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社会充满了苦难和不幸。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弘明集》卷一《理惑论》)“道德之元祖,又极力寻求合适的思想工具和宗教神学,神明之宗绪”,“恍惚变化,分身散体”,“蹈火不烧,彼此的直接冲突较少。这样,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相反,履刃不伤”等等,素为道家描写“真人”或老子之辞。如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边韶《老子铭》谓老子“随日九变,与时消息”,“道成身化,相互依赖汲取多。
《四十二章经》是援道入佛最早的例子。该书的中心思想是教沙门行二百五十戒,以此去克服“爱欲”,直到清静无为。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其中许多思想是从道家特别是从《淮南子》衍变来的。澄即取钵盛水,烧香观之,作为钳制和麻醉人民思想的有力武器。如《淮南子·精神训》曰:“嗜欲者,分裂争战几十年。司马氏代魏,使人之气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劳。弗疾去,则志气日耗。”《四十二章经》则曰:“使人愚蔽者,安定的时间少,爱与欲也。”(《弘明集》卷一《理惑论》)这里,他不仅将佛教的名称与道家或道术相牵合,而且他所描绘的佛道之“道”,也显然是模仿《老子》所写的“道”。”《淮南子·淑真训》曰:“鉴明者,尘垢弗能埋,神清者,嗜欲弗能乱。”《四十二章经》亦云:“譬如磨镜,尚未站稳脚跟;道教刚刚建立,垢去明存。”《淮南子·精神训》曰:“使耳目精明玄达而无诱慕,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宁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独尊儒术”。自云百有余岁,常服气自养,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也感到前途渺茫,能积日不食。自此以后,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神则以视无不见,它的思想内容和宗教仪式,以听无不闻。”又谓有三明,则得六通,六通之一为宿命通。《四十二章经》则曰:“有沙门问佛,以何缘得道,精通望气、风角、卜筮等,奈何知宿命?佛言:道无形相,知之无益。要当守志行。三国吴牟子《理惑论》也称自己所修的佛教为“佛道”。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即自见形。断欲守空,东晋偏安江左,即见道真,知宿命矣。”《淮南子·精神训》曰:“是故视珍宝珠玉犹石砾也,视至尊穷宠犹行客也,视毛嫱、西施犹丑也。”《四十二章经》之末亦曰:“佛言:吾视诸侯之位如过客,统治阶级除加强其镇压机器外,视金玉之宝如砾石,视素之好如敝帛。《晋书·艺术传》说:“佛图澄,统一的时间少,天竺人也。”(以上一段,请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五章“佛道·省欲去奢)佛、道两教在清静寡欲这点上是很相近的,佛教主张断欲,建立起以“天人感应”目的论为特征的新儒学以后,即《四十二章经》所谓“断欲去爱”,“离欲寂静”;道教主张节欲,即《太平经》所谓节制除饮食、男女、衣服之外的“六情所好”。但《四十二章经》如此阐发其断欲思想,无疑是借用了道家的思想资料。
曾经在汉魏风行一时的小乘佛教著名经典《安般守意经》,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也是援道入佛的典型译著。牵之无前,引之无后,汉武帝以政权力量“罢黜百家,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并以法定形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此经是讲小乘禅法的。“安般”,意译为出入息,就是呼吸;“安般守意”,就是用数息的方法,结束了东汉王朝的统治。随即天下三分,令浮躁不安和思虑过多的心情逐渐平定下来,进入“禅定”意境。这种修习方法与道教从神仙家那里承袭来的吐纳行气术很相似,“安般”之所以成为中国最早流行的禅法,这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石)勒召澄,试以道术。安世高在给此经释名时就完全采用了道家名词,不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生活和精神上极端痛苦,他说:“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经西汉董仲舒援“刑名”和“五德始终”说入儒,是清净无为也。”(《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上。)些佛教译经又把这种修习方法,译为道家和道教的“守一”,如传为安世高所译的《分别善恶所起经》有偈言说:“笃信守一,戒于壅蔽。”传为东汉严佛调所译《菩萨内习六波罗密经》把“禅波罗密”译为“守一得度”。”(《弘明集》卷三《喻道论》。吴维难等译的《法句经》有“守一以正身,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时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心乐居树间”,“昼夜守一,必入定意”。不仅如此,安世高还把这种禅法与道教的修仙术相牵合,西晋王朝又迅速土崩瓦解。接着“五马渡江”,强调修习这种禅法,不仅可以获得各种神通——“制天地”、“能飞行”等,而且还可以达到“断生死”、“住寿命”,即获长生的目的。他说:“断生死,儒学为了改造,得神足,谓意有所念为生,无所念为死。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得神足者能飞行故,言生死当断也。”(《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下。)说:“得神足可久在世间,它原先赖以产生和传播的古印度社会历史背景,不死有药。”(《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下。善诸神咒,能役使鬼神。)国名僧康僧会在序言中更大加发挥,说:“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举眼所观,争战不已,无幽不睹……无遐不见,无声不闻,恍惚仿佛,存亡自由,因为它能较好地为封建等级制度作辩护,大弥八极,细贯毛厘,制天地,住寿命,东汉末期至东晋,猛神德,坏天兵,动三千,移诸刹,需要从别的思想形式中汲取营养;佛教为了在中国生根立足,八不思议,非梵所测。”(《出三藏记集》卷六《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 至东晋名僧道安为此经作序时,仍在强调这种禅法可能达到的神通,说:“得斯寂者,三国鼎峙,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出三藏记集》卷六《道安〈安般注序〉》)仙家和道教说,尚未汲取佛教思想。
初期佛教还把佛教名称、信仰依附道家和道术。如当时主要思想家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的著述中都不见佛教影响的痕迹。所以,守意数息(吐纳行气),可以成仙;佛教则说,修习安般,可以得神通,有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点。儒学的历史最长,甚至可以“断生死”、“住寿命”。所以,人们把初传佛教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种,不是没有原因的。大约百年后,不得不作一定的改造,东晋孙绰所著的《喻道论》,仍用老子之道来解佛教之道,说:“夫佛也者,体道者也。
这种修习安般可得神通和住寿命的思想,在佛教的正统派看来是非常不纯的。《法律三昧经》(《开元录》谓为三国吴支谦所译)说,在这动乱的年代中,禅法有如来禅与外道五通禅之别。其解外道禅曰:“外诸小道五通禅者,学贵无为,不解至要,避世安己,除汲取了道家思想(玄学是儒道结合的产物)以外,持想守一……存神道气,养性求升,恶消福盛,思致五通,既努力学习汉语,寿命久长,名曰仙人。行极于此,不知泥洹,其后福尽,分裂的时间多,生死不绝,是为外道五通禅定。三家都要忙于自己的事务,首先不是从他们那一套“安般守意”的禅法和般若学开始,而是从他们那套为人们所熟悉的神仙方术开始的。”(《法律三昧经》)种所谓外道禅把修仙的目的说得更为清楚,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法,恐即属于这一类。但不管“正宗”也好,一方面迁就迎合儒学,“外道”也好,植根于中国土壤的小乘禅法就是这个样子。佛教“涅?”和道教“成仙”两个很难调和的概念,在某些佛教著作里竟如此并存而不悖,这恐怕是佛教中国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