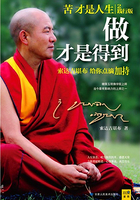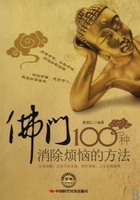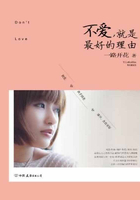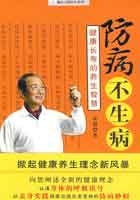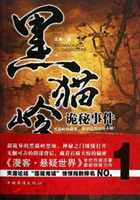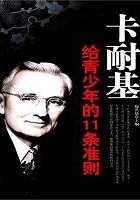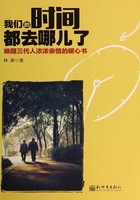第三,"忘彼忘此,无悦无恶"。金高守元《冲虚至德真经四解》中说:"自然死耳、自然穷耳,未必由凶虐与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赖生之地而威之,以死是之死,得其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道藏》第15册,第121页。道教将生死运动与演化之本性称之为自然,这种自然表现为"天福",其本质表达了生命本质运动所具有的基本内涵。而其中所谓"自然死"、"自然穷"乃为生命生死运动规律之体现,在没有人"凶虐"、"愚弱"等人为之干扰的情况下,才能称生命之死为"以死是之死",在这种生命运动情况下的"死"是为"得其死者",即"天福者也"。道教又将其称之为"无悦""无恶"。金末元初《洞渊集》还认为:
死生至理,民之大事,莫过于斯。惟食生丧德倒置,薄俗之流,嬉游四方,情欲关扃,穷年惵惵,忘乎本矣。夫体道之人则不然,通乎物之所造,达阴阳之变化,了心智之玄同,塞乎七穴,众态一起,考命虽终,有不亡之理,忘彼忘此,无悦无恶,以天为一谷,以太虚为友邻,岂有形骸之累乎。《道藏》第23册,第858页。
道教认为人应该深入了解生死变化的规律,将生死置之度外,以超然的态度面对生死之变化,"忘彼忘此","无悦无恶",才能在生命运动过程中寻找"不亡之理",超脱生死之累。"在传统中国文化中,还存在另一种生命观,即承认死后的世界,认为神(灵魂)脱离形体之后,还有其独自的生命存在形式"张光保《唐宋内丹道教》,第339页。道教对生死运动变化所持的基本态度,也包含这种"神"独自的生命存在形式而达到"无悦无恶"之"天福"的重要内容。生命生死之道只有"通乎物之所造,达阴阳之变化,了心智之玄同",才能实现"以天为一谷,以太虚为友邻,岂有形骸之累乎"之天福。但是如果人们在生命的生死问题上"惟食生丧德倒置,薄俗之流,嬉游四方,情欲关扃,穷年惵惵",那么,生命之生死则具有"形骸之累",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生命生死之天福则根本不可能实现。
二"知其生则自然知其死也"
——生与死的认识论
"对苦难与死亡的神义论的理性需求发挥了无比强大的作用。这种需求直接创造了诸如印度教、锁罗亚斯德教、犹太教等宗教,在一定的意义上还塑造了保罗派及后期基督教的重要特征。"(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页。道教对于生死的基本认识是建立在不可知论基础之上的,这种生死不可知论的基本内容是"皆知生之日,不知死之日",也就是说道教对于生命生死运动规律的认识是不彻底的,有条件的。如果说道教对于生死运动规律的认识是有条件可知的话,那么这个前提条件就是"知其生则自然知其死也"。但是这个具有前提条件的"知其生自然知其死"所表达的真正的思想则体现了另一条基本内容,即"不知其生当然就不知其死",从而使道教对于生命生死运动的认识是建立在有条件的可知论基础之上的,是一种不彻底的有条件的可知论,其本质则表达了道教对于生命生死运动的不可知性。
第一,"计生死者,如牛之翼"。道教认为"生死者,一气聚散尔",这种"气"的运动与变化是不确定的,"如牛之翼,本无有,复无无",是难以把握的,其生死运动变化乃是不可知的;同时又是客观必然的,"譬如水,火虽犯水,火不能烧之,不能溺之"。南宋《太上妙道文始真经》说:
生死者,一气聚散尔。不生不死而人横计曰生死。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药者等。死无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见生故不见死。人之厌生死、超生死皆是大患。譬如化人,若有厌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为妖,不名为道。计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无,或曰死已亦有亦无,或曰当幸者,或曰当惧者,或曰当任者,或曰当超者,愈变识情驰骛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马之手,如牛之翼,本无有,复无无。譬如水,火虽犯水,火不能烧之,不能溺之。《道藏》第11册,第519页。
道教对于生命生死运动的不可知性表达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死是不可知的,因为生死乃"本无有",如马之手、牛之翼,是根本不可知的。二是生死往往不被人们所认识,"人之厌生死"并想"超生死"使生死成为人们回避和逃避的现实问题,只有在有条件的前提下才涉及到生死问题:"若知道之士,不见生故不见死",即人只有在涉及到生命之生,才想到生命之死。三是生与死的运动转化是不可知的,况且,死的表现有多种多样,如"立"、"坐"、"卧"、"病"、"药"等形态,其内容又是不确定的,而对于生死的认识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无,或曰死已亦有亦无",其结果则"愈变识情驰骛不已",是难以被认识和把握的,是不可知的。同时,道教还表达了对于生命之生死有条件的可知性,并进一步将对于"生死"的认识与对于"道"之认识结合起来,人能否知生死主要看对于道的掌握情况如何,人如果知"道"则便知生死。反之,就不能知生死。
第二,"生死有命,贵贱有天"。道教吸收了儒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提出了"生死有命,贵贱在天"的观点。元代神霄派道士王惟一撰《道法心传》认为:"生死有命,贵贱有天,世人何不乐天知命,徒尔恶死而好生。"《道藏》第32册,第412页。这里的"恶死好生"是道教对于生死的态度,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生死之事乃人生之大事,生死之运动乃生命之必然,一个人只有顺应生命之本质必然才能以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对待生与死。元李道纯在《中和集·生死说》中说:
人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惟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是谓求生了不可得,安得有死耶。有生即有死,无死便无生。故知性命之大事--死生为重焉。欲知其死,必先知其生,知其生则自然知其死也。《道藏》第4册,第504页。
这里将生死作为人生性命之大事,"知其生则自然知其死"是道教生死有条件可知论的主要体现。其中"欲知其死"是结论,而"必先知其生"则是知其"死"之条件。但是如何才能知生死之性命,道教认为"从道受生谓之命"、"掌握大道谓之性",人只有掌握"道"之运行规律才能知其"人命有限",才能把握生命运行之规律。玄元真人《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解》说:"大众性者何也,命者何也。从道受生谓之命,掌握大道谓之性。是知人命有限,本性无生。故老君曰,有生必有死,无死亦无生是也。"《道藏》第17册,第45页。生命的存在与大道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就可以根据道之运行规律来预测生死,当然也就可以知道"生命有限",生死运动变化是道之运行所必然。
第三,"不知死生,岂能免乎"。道教的生死认识论是一种不彻底的"可知论",这种可知论是建立在有条件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当这种条件能够满足认识论所需要的基本要求时,这种对于生死的不可知论就将变为可知论。"万物之中人最为贵,而人处在天地之间,皆知生之日,不知死之日。善恶之人,富贵贫贱,各愿寿老,谁欲其夭。夫死者人所不乐,而见一切岂能免乎,唯有不生无此难耳。"《道藏》第24册,第716页。但是,由于道教关于"道"之本体本性的认识是建立在"玄之又玄"、"缈冥幽远"的不可知基础上的,道教关于生死可知的认识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暂时的和难以完全实现的,其实质乃是生死的不可知论。
三"生者人之所爱,死者人之所恶"
——生与死的恶乐观
道教的生死观是积极的,这种积极的生死观在生死运动与生死转化方面则体现在对于生命之生所爱,对于生命之死所恶。道教对于生死的恶乐观,一方面反映了道教作为人间宗教所具有的入世及贵生精神;另一方面则是道教本身生命观所具有的乐观态度之体现,具体表现在"畏死乐生,未央脱死"、"故有死王,乐为生鼠"、"道丧而死,道存而生"、"身死性存,死生自命"、"死生之变,恶能相知"等方面。其本质表达了对于生的渴望,对于死的憎恶,反映了道教作为"贵生"的宗教所具有的生命意义。
第一,"畏死乐生,未央脱死"。萨特认为,死处于人生的彼岸,生死是绝断的,由于死亡而消除了人生的意义。参见(日)岸根卓郎著,何鉴、王冠明译《宇宙的意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4-36页。道教对于"生死"所表现的态度是追求"恶死乐生",以及对于"生"的珍惜和重视,对于"死"的坦然和明智。"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死"是"生"的反面对立义;是"生"的终结;也是生的极限;因此对俗世的人生是最大的打击--终极的悲剧。"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老子想尔注》说:
死是人之所畏也,仙王士与俗人同知畏死乐生,但所行异耳。俗人莽莽,未央脱死也,俗人虽畏死,端不信道,好为恶事,奈何未央脱死乎。仙士畏死,信道守诫,故与生合也。《老子想尔注校笺》第27页。
"仙王士"与"俗人"虽然都具有"畏死乐生"之生死态度,但是由于其"信道"不同,其行为结果是不一样的。一是死是所有的人都畏之的事情,不论是"仙王士"还是"俗人"都具有"畏死乐生"之生死观。二是由于"仙王士"与"俗人"具有不同的"信道"之态度,因而也就具有"好为恶事"、"守诚"等不同的行为表现。三是"仙王士"与"俗人"虽然都"畏死",但是二者具有不同的生命观,这种生命观的差别表现为"断不信道"与"信道守诚"。四是由于"仙王士"与"俗人"由于"信道"不同,所以在对待生死方面则表现为"未脱死"与"与生合"之不同的生死结果。道教最终还是将生命的生死运动归结到了其道之本体方面,认为生命的生死运动最终体现在道之属性方面。"信道者生"、"不信道者死"。"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壹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太平经合校》第298页。生死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壹生"、"壹死"必须引起每个人的重视,并将其作为人生之"重事"认真加以对待,因为人死"脉骨成涂土"、"不得重生",应该将生与死同样当作"重事"对待,其思想体现道教对于生死之道的基本要求以及对于生之所乐,对于死之所恶的基本观念。
第二,"故有死王,乐为生鼠"。道教认为客观的生死转换与人之主观所具有的"惜生畏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追求"惜生畏死"是生命运动演化所具有的本能之体现,是生命演化发展的必然方向。"人总是求生而不求死,凡是动物都是避死而营生,何况高等动物人呢?"王明《论道教生死观与传统思想》,《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第226页。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生可惜也,死可畏也。"《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26页。并进一步认为:
古人有言,生之于我,利亦大焉。论其贵贱,虽爵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论其轻重,虽富有天下,不足以此术易焉。故有死王乐为生鼠之喻也。同上,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