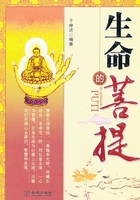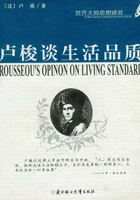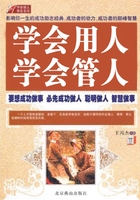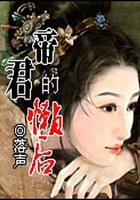一、贺麟的生平与著作
贺麟,字自昭,1902年9月20日出生在四川金堂县杨柳沟村一个乡绅家里,父亲是一位秀才,曾主持乡里和县里的教育事务。
8岁时,贺麟按规矩进入私塾读书,所学不外四书、五经,重在记诵而轻忽理解;但贺麟却凭其聪慧,尽量去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并深受其熏陶,对宋明理学特别感兴趣,为后来深入国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1917年,贺麟考入四川省立成属联中———石室中学学习。1919年,他考入清华学校,接受正规高等教育。除了圆满完成学校所规定的必修课外,他尽量选听各种专题讲座,以扩大知识视野。1920年春,梁启超应聘到清华讲国学小史,并在闻一多举办的文学研究会上讲授中国文学,贺麟前往听讲。梁对陆王心学精研入微,讲来如数家珍。这种融精深学识与天才演讲于一体的教学,贺麟为之倾倒,并把梁启超视为楷模。为此,他经常造访梁启超,在梁的指导下,写出了国学研究方面的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以及《博大精深的焦理堂》发表。
贺麟在清华时,经常请教客居清华园的梁漱溟。梁漱溟给青年指路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梁启超和梁漱溟对王阳明哲学的推崇与精深讲解,更给贺麟以深刻的影响。梁启超、梁漱溟将贺麟引进了儒学,贺麟创立“新心学”与受到他们的影响分不开。
在吴宓影响下,贺麟对翻译产生了浓厚兴趣,打算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己任,同时他还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上开始有了自己的见解。1925年秋,他写成《论严复的翻译》一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49号上。
1926年夏,贺麟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8月,赴美国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接受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由此跨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大门。在奥柏林大学老师的引导下,他对斯宾诺莎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纪念斯氏逝世250周年之际,贺麟专门写了一篇研究其思想的文章,认为斯宾诺莎所主张的人受到利欲、情感的奴役,要解除它就需求助于理性,因此产生自觉的道德的思想,与中国宋儒“尽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很相似;而斯氏所说的“实体”或“上帝”,就是自然,与主张“齐物我,一天地”的庄周思想颇为接近。受斯氏哲学和人品的影响,贺麟立志要把斯氏哲学思想翻译介绍到中国来。
1928年2月,贺麟从奥柏林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转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但因不满于该校的实用主义者,在下半年转往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极重西方古典哲学,他攻下了康德哲学这一大难关,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哲学打下了坚实基础。此间,他还听过怀特海的几门课,他觉得怀特海之风貌很像宋儒程颢。
在美国求学期间,贺麟对黑格尔哲学也有一定了解和兴趣,先后听过三个人讲黑格尔哲学课:芝加哥大学的实用主义者米德、哈佛大学新黑格尔主义者霍金、波士顿大学人格主义领袖布莱特曼。
对新黑格尔主义领袖罗伊斯的《近代唯心论演讲集》和《近代哲学的精神》两本著作,贺麟也很感兴趣。为了研究黑格尔,他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放弃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于1930年夏从纽约乘船至德国,入柏林大学。
在柏林大学,贺麟选了新黑格尔主义者哈特曼的历史哲学课,对哈特曼在黑格尔辩证法方面的见解深为服膺,以为哈特曼抓住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真谛,并在回国后发表了《辩证法与辩证观》。通过一年的学习,1931年8月,贺麟结束了五年的欧美求学生涯回国,北京大学聘他主讲哲学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等课程,并在清华大学兼课,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西洋哲学等课程。他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深受学生欢迎。
其间贺麟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回国后不久,他译出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第一、二部分作为教材;1936年,他将在美国时已译出的《黑格尔学术》与另一本介绍黑格尔的著作———开尔德的《黑格尔》同时出版;1943年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斯宾诺莎的《致知篇》。
抗战期间,贺麟力倡学术救国。1931年他写《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激励学人的救国之志。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发表《新道德的动向》、《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和《法制的类型》三篇文章,提出振奋民族精神、弘扬学术文化、实行政治革新等主张,受到蒋介石的关注,四次被召见。抗日战争胜利后,贺麟在北大担任训导长,多次出面保护甚至营救进步的青年学生和教授,深受学生拥戴。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在北大哲学系任教。1950年底至1951年,他一度走出书斋,投身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先后到陕西西安和江西泰和参加土改运动。1951年4月2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公开表示赞同唯物论,并批判了唯心论的错误观点。1954年,学术界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贺麟把批判活动看成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改造。195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他写的《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一文,他敢于解剖、批判自己,并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以前的思想观点的勇气,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55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哲学所任西方哲学组组长。
1957年以后,受到“左”的倾向影响,贺麟多次受到批判,而后远离哲学埋头于翻译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贺麟多次挨批斗,被关进“牛棚”一年多。之后以“劳动锻炼”的名义被遣送到河南农村干校改造两年。
1979年6月,他作为中国社科院访日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去日本作学术访问;同年8月,又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国际黑格尔哲学第十三届年会;1983年10月至11月,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赴港讲学月余。由贺麟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国内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一流专家学者组成,1981年和1988年分别成立了《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贺担任该会名誉主任委员)和西文哲学名著研究编译会(贺任名誉会长),为我国学术事业走向繁荣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他自己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集》(第四卷)、《精神现象学》(下卷)和《小逻辑》修订本相继再版;先后发表数十篇有关哲学研究(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论文。1984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根据他早年的讲课记录整理修订而成)和1986年出版的《黑格尔哲学讲演集》,被学术界看作他哲学研究道路上的两座丰碑。
1992年9月23日,在过完90岁生日后的第三天,贺麟因病逝世于北京。
学术界公认贺麟学贯中西,在中国哲学方面也有极高造诣,是“新心学”的创建者,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贺麟的“新心学”是对中西文化的融通,是中国的陆王心学与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贺麟新心学思想体系的特点之一就是调解两个对立面,使之融和合一。新黑格尔主义以主观唯心主义来代替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以形而上学来修正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论述、知行合一新论与直觉论、“心即理”的唯心论,构成了他哲学思想的主要部分。他的主要著作有:《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等;主要译作有:《小逻辑》、《黑格尔》、《黑格尔学述》、《哲学史演讲录》(与王太庆等合译)、《精神现象学》(与王玖兴合译);主要论文有:《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知行合一新论》、《宋儒的思想方法》、《黑格尔关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的理论》、《黑格尔的早期思想》、《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述评》、《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等。
二、力倡陆王新儒学
1925年,贺麟在清华学校学习时,在吴宓影响下,把翻译、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确立为自己的终身志业。1930年,他发表《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开始走中西哲学比较考证、融会贯通的道路。此后贺麟一直以译述为中心,将代表西洋哲学高潮的西方经典哲学作比较全面的介绍,且与中国古代哲学比照、沟通,将中西哲学的阐述和中西文化深层次的交融与中国的新哲学、新文化创建紧密联系起来。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贺麟把它与陆王心学相结合,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新心学”哲学思想。他在20世纪40年代先后出版的《近代唯心论简释》(1942)、《文化与人生》(1947)、《当代中国哲学》(1947)等著作,是其新心学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也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地位。
有感于治中国哲学者不能打通西洋哲学,而治西洋哲学者不能与中国哲学发生密切关系的现实,贺麟认为离开认真负责、坚实严密的翻译事业,而侈谈移植西洋学术文化,恐怕永远不会有自主的新学术,真正的西方文化也永远不会在中国生根。他提出“化西”
的概念,认为翻译的意义,在于华化西学,使西洋学问中国化,灌输文化上的新血液,使西学成为国学的一部分,使外来学术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对外来文哲典籍的翻译,既能理解原作的主旨,贴近原作的神韵,又能做到如出己口、如宣己意,那么这两种哲学、文化的交融会通就在其中了。他认为用中国名词去解释西方名词是好办法,比如用中国哲学基本范畴“太极”翻译黑格尔的“绝对”,是他创造的一个先例。
他自己坚持走新哲学的创建之路,认为在中国,要提倡这种哲学,必须很忠实地把握西洋文化,但又不是纯粹的抄袭,而是加以融会发挥,所以这种哲学仍可以称为中国的哲学。本来中国的正统哲学与西洋的正统哲学是能融会贯通的、并进的、合流的,过去我们不能接受西洋的正统哲学,也就不能发挥中国的正统哲学。在西洋,最伟大的正统哲学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在中国则有孔、孟、程、朱、陆、王。从各方面来看,这两种思想是相合的,所以中国正统哲学的发挥和西洋正统哲学的融化,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也就是说,他要“儒化”西方文化,其含义是:在吸取西方文化过程中要经过主体的主动选择,选择的标准便是儒家思想;选择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消化吸收的过程,要将西方文化融化在儒家思想中。其基本立场是以儒家思想为尺度来融会、转化西方文化,他的新心学充分体现了这一立场;其立足点在“化西”,就是“自动地自觉地吸收融化,超越扬弃西洋现在已有的文化”。
贺麟承认自己的思想有深远的来源,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儒家思想,他不仅对孔、孟、程、朱、陆、王,而且对老、庄、杨、墨等,都有同情的理解和切合时代的发扬。对西洋思想文化,他也绝对不反对,而是兼收并蓄,深深地寝馈其中,虚心以理会之,切己以体察之,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格林、怀特海、罗伊斯等西方历代圣哲的睿智大慧,尽量用自己的语言解释给国人。
贺麟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一篇题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文章中,就提出了“新儒家”、“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命题,认为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儒家思想现代性开展之可能,是贺麟给自己提出的时代性理论任务。他认为“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他看到新文化运动虽然表面上是一个“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但实际上,它在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方面的功绩远远超过曾国藩、张之洞等前代人的努力。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功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输入给儒家文化的现代性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此他认为,与其把西方文化的引进看作对儒家思想的沉重打击,不如看作是给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提供一个考验,“如果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
贺麟认为儒家思想包含着文化的共性和永恒的价值原则,包含着真善美的价值理念。儒家思想具有的真精神与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是等值的,是一种普遍的精神理念,“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儒家文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尽管存在诸多差别,但是文化的纯体均以道或蕴涵道的精神为体。儒家哲学是“普遍的哲学、典型的哲学、模范的哲学”。他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对梁漱溟、冯友兰、马一浮等现代新儒家思想的评述也体现了这一思路。贺麟对儒家思想检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他对五伦观念的同情理解。他经过考察,发掘出传统五伦观念所蕴涵的基本质素:“注重人与人的关系”,“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永久关系”,“以等差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常德为准而皆尽单方面之爱或单方面的义务”。儒家思想的现代性开展的另一个关键环节便是对西方文化的彻底了解和把握。只有真正认识一种文化才有可能超越它,转化它。所以,“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在他看来,宗教和科学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基督教和科学并非互相反对,基督教对科学是有保护促进之功。“科学家一面固然追求纯理智的真理,一面在情感上亦仍旧须求得宗教的安慰,两者可并行不悖,并无不兼容之处。”他无比深情地说:“一个城市中如只有烟囱而没有教堂,总觉得是像缺了一面,是变态。烟囱是工业化的象征,教堂的塔尖是精神文明的象征,两者都高耸入云,代表着同一种向上的希天的精神的两方面。”贺麟认为宗教和道德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都以求善为宗旨,“宗教与道德皆同为善的价值之表现”。两者同为精神乃至道之用,大致可归为同等层次的范畴。在求善的方式、所求之善以及求善之目的上,宗教与道德之间的界线是分明的。他给宗教的定义是:
“如果认为有一神圣的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这就是宗教。或者从内心说,人有一种崇拜的情绪,或追求价值的愿望,就是宗教。”“宗教所追求者为神圣之善,道德所追求者为人本之善,宗教以调整人与天的关系为目的,道德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为目的。在此意义下,我们不能不说,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他把道德纳入宗教的统摄之内,与他泛化宗教的思想倾向直接关联。在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上,贺麟把人的一切价值取向和评判系统一律调拨到宗教的名下,使道德受制于宗教,成为宗教之用。
贺麟的基本立场是以儒家思想为尺度来融会、转化西方文化,他的新心学就体现了这一立场,其立足点在“化西”,“自动地自觉地吸收融化,超越扬弃西洋现在已有的文化”。
由此,学术界认为贺麟的哲学立场,可归于“新陆王”的范畴。
相对于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思想学说被称为“新心学”。新心学虽然没有形成像“新唯识论”或“新理学”那样严整的思想体系,但“回到陆王去”的旗帜毕竟显示出贺麟同新理学相抗衡的特点,在学术风格与学术旨趣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三、新体用说
贺麟下工夫探讨了文化的本质问题。贺麟指出:“道之凭借人类的精神活动而显现者谓之文化”,“道之未透过人类精神的活动,而自然地隐晦地昧觉地显现者谓之自然”。对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贺麟认为,道是宇宙本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和自然一样,都是道之用,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文化与自然尽管同出一辙———以道为体,但对二者并不能等量齐观。他指出:“文化与自然虽皆所以载道,但文化是文化,自然是自然,两者间确有重大区别……文化乃道之自觉的显现,自然乃道之昧觉的显现。同是一个道,其表现于万物有深浅高下多少自觉与否之不同,因而发生文化与自然的区别。”这就是说,文化是道之自觉的显现,而自然则是道之未觉的显现。所以,在由道、精神、文化和自然构成的相互关系中,自然处于最低级的层次。就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文化为自然之体,自然为文化之用。文化作为体,是价值物;自然作为用,与价值相对立。在此前提下,他提出了自己的新体用说。
贺麟在《文化的体与用》中集中研究了体用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自己的体用观。在他看来,体用可以分为常识的和哲学的两个不同层次。“常识上所谓体与用大都是主与辅的意想。”“哲学意义上的体用须分两层来说。一为绝对的体用观。体指形而上的本体或本质(essence),用指形而下的现象(appearance)。……一为相对性或等级性的体用观。将许多不同等级的事物,以价值为准,依逻辑次序排列成宝塔式的层次(hierarchy)。最上层为真实无妄的纯体或纯范型,最下层为具可能性、可塑性的纯用或纯物质。中间各层则较上层以较下层为用,较下层以较上层为体。”贺麟认为,“绝对的体用观”是“柏拉图式的”———以本体与现象言体用;而“相对的体用观”则是“亚里士多德式的”——— “除以本体现象言体用外,又以本体界的纯范型作标准,去分别现象界个体事物间之体用关系。
以事物表现纯范型之多或寡,距离纯范型之近或远,而辨别其为体或用”。
精神与文化的关系,贺麟认为,从总体上说,文化以道为体;作为文化之体的道即价值观念要通过精神显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以精神为体,精神以文化为用。于是出现了精神与文化这一对体用范畴。在他看来,作为价值观念的道活动于内心就是精神,精神是道显现为文化的凭借;作为文化之体的精神,就是价值体验。文化是道的自觉体现,文化作为道和精神之用来说,就是价值观。他说“文化乃是精神的产物,精神才是具众理而应万事的主体”。
贺麟借助于西方的实体学说与方法,论证了心外无物、心物不分的“心体物用”论,调解了宋儒在心、理关系上的畸轻畸重,提出了心即是理、理在心中的“心与理一”论。
对心、物关系,贺麟援引斯宾诺莎“心物一体两面平行论”,以陆王心学改造其心物互不干涉论,提出了心体物用论,心与物在“科学研究上,自可无主从体用之分……但哲学上不能不揭出心为体,物为用之旨”,实际上“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他指出:
“普通人所谓‘物’,在唯心论者看来,其色相皆是意识所渲染而成,其意义、条理与价值,皆出于认识的或评价的主体。”这就是说,物只有依赖于心才能存在,物是从心那里获得实在性的。反之,离开心之物,不过是漆黑的一团, “均非真实可靠之物或实在”。正因为如此,贺麟再三强调:“所谓物质,一定是经过思考的物质。所以不可离心而言物。”“严格讲来,心与物是不可分的整体,为方便计,分开来说,则灵明能思者为心,延扩有形者为物。据此界说,则心物永远平行而为实体之两面: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贺麟的心物平等说与心体物用论就事实界与逻辑界立论,强调心对物的决定乃是逻辑上的决定,坚持心在“逻辑上”永远先于物、决定物。对心、理关系,贺麟论述有两种心,一是“心理意义的心”,二是“逻辑意义的心”。对于第二层意义的心,他认为此心即理,比心理意义的心更为根本和重要,“乃一理想的超经验的精神原则”,是认识或评价的主体,决定着一切事物具有其客观性,“自然与人生之可以理解,之所以有意义、条理与价值,皆出于此‘心即理也’之心”。
出于上述考虑,贺麟着实凸显了心相对于物的“主”、“体”地位,渲染了自己的“唯心论者”的立场。他强调说:“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故所谓物者非他,即此心之用具,精神之表现也。”对哲学和文化的体与用之间的关系,贺麟阐述说:“(一)为体用不可分离。盖体用必然合一而不可分。凡用必包含其体,凡体必包含其用,无用即无体,无体即无用。没有无用之体,亦没有无体之用。”“(二)为体用不可颠倒的原则。体是本质,用是表现。体是规范,用是材料。不能以用为体,不能以体为用。”“第三个原则,为各部门文化皆有其有机统一性。因为各部门的文化皆同是一个道或精神的表现,故彼此间有其共通性。一部门文化每每可以反映其他各部门的文化,反映整个的民族精神,集各种文化之大成。”“因精神中所含蕴的道或价值理念有真美善的不同,故由精神所显现出来的文化亦有不同的部门。因不同部门之文化之表现精神价值有等差之不同,遂产生相对性文化的体用观。”
对道与文化的关系,贺麟认为,道是文化之体,文化是道之用,道与文化构成了体用关系。对此,他写道:“所谓‘道之显者谓之文’应当解释为文化是道的显现,换言之,道是文化之体,文化是道之用。所谓‘道’是宇宙人生的真理,万事万物的准则,亦即指真善美永恒的价值而言。……全部文化都可以说是道之显现。”在贺麟的哲学中,道是宇宙万法的本体,统摄整个世界,是世界万物的宇宙本体,当然也是文化之体了。作为文化之体,道就是价值理念。
身心关系的体用关系表现为,心为身之体,身为心之用。这是心物体用观的必然结果,是贺麟对“心即理”的进一步发挥。这里心有两层含义:一为心理意义的心,一为逻辑意义的心。逻辑意义的心即是理,理则之心为身体提供了行动指南。从这一意义上说,身体行动的意义,只能到心那里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只有在心统辖下的行动,才是有价值的行动,才能收到预期的目的。所以,贺麟强调:“心是身之所以为身之理。身体的活动所代表的意义、价值、目的等,均须从心灵的内容去求解释。”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贺麟认为,作为道之显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互补充、不可或缺。贺麟表示:“我以为文化必不是纯粹文化,而必定以武力和物质为其因素;文化失去这两者就会变成空虚;例如我国,凡是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必定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时发达。”文化并不是纯粹的精神现象,必须以物质为其要素,否则文化会变得空虚无实。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两者相互配合,才能构成一个有机的文化的统一整体。贺麟说:“精神与物质乃同一实在之两面,经济实业与思想道德乃同一社会生活之两面,不能互为因果,互相决定。”然而,思想道德与经济实业的关系是“就哲学理论言”的;“就事实言”或者说“就常识言”,则可以说经济实业能够影响思想道德,思想道德也能够影响经济实业。只是“被动的为经济所影响的思想道德,非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思想道德。反之,为思想道德的努力所建设的经济实业,方是真正的经济实业。不然,未经过思想的计划、道德的努力而产生的物质文明,就是贵族的奢侈,贪污的赃品,剥夺的利润,经济生活的病态”。无疑,贺麟在这里实际上等于说,作为道德思想的精神文明是体,作为经济实业的物质文明是用。贺麟还进一步视精神文明与文化为同等概念,因为“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真美善即是真理化、艺术化、道德化,而由于系高尚的情感、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的理智所产生,可以说即是精神化———精神文明”。这明显是在强调精神文明是体,强调物质文明是用,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
贺麟认为,按照绝对的体用观,哲学与科学同属于文化的范畴,均为道或精神之用,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进而言之,在相对的体用观中,哲学与科学虽然皆是真理之显现,但两者之苗莠朱紫自不待言。“哲学追求价值的真理,科学追求自然的真理。哲学阐发关于宇宙人生之全体的真理,科学研究部分的真理。因此虽就绝对的体用观说来,科学与哲学皆同是精神之用,精神兼为科学与哲学之体,但就相对的体用观说来,我们不能不说哲学为科学之体,科学为哲学之用。”在贺麟看来,既然哲学与科学追寻不同的价值取向,既然它们拥有不同的研究内容,而无论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在研究范围上哲学都给科学以指导,那么,哲学是体,科学为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四、新知行说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其目的在为道德修养即他所说“致良知”功夫建立理论的基础。贺麟认为“知行合一说与王阳明的名字可以说是分不开的。王阳明之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在为道德修养,或致良知的功夫,建立理论的基础。”到晚年阳明便专揭出致良知之教,以取代有纯理论意味浓厚的知行合一说。所以后来王阳明的各派门徒,所继承于他而有所发挥的,几乎完全属于致良知之教及天泉证道的四句宗旨。对他的知行合一说,不唯没有新的发挥,甚至连提也绝少提到。贺麟痛感此后三百多年内,赞成或反对阳明学说的人虽多,但对知行合一说,有学理的发挥,有透彻的批评或考察的人,几乎一个代表都找不出。知行合一说虽因表面上与常识抵触而易招误解,但若加以正当理解,实为有事实根据,有理论基础,且亦于学术上求知,道德上履践,均可应用有效的学说。贺麟发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运用生理学和心理学知识给知行下了这样的定义:“‘知’指一切意识的活动。‘行’指一切生理的活动。”“知行同是活动”,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量上的。在此基础上,贺麟提出了“知行自然合一”说。他说,沉思、推理或研究学问,此为“显知”,但“显知”必伴随着脑神经运动的“隐行”;同样,下意识的活动、本能的意识等是“隐知”,而“隐知”必伴随着动手动脚等“显行”。可见,知行不可分割地拴在一起,没有原则界限。然而,知行合一不是混沌的模糊一团,而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在知行各自清晰的合一中,知行的地位显然并不等同,其中隐藏着不容混淆的主从关系。知永远决定行,故为主;行永远为知所决定,故为从,这就是“知主行从”。“知主行从”表明,在知行的关系中,知是行的本质,行是知的表现;知是行之体,行是知之用;知是目的,行是手段。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所以贺麟说:“知是行的本质(体),行是知的表现(用)。行若不以知作主宰,为本质,不能表示知的意义,则行为失其所以为人的行为的本质,而成为纯物理的运动…… ‘知’永远决定行为,故为主。
‘行’永远为知所决定,故为从。”人们应该永远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到知的指导和统辖之下,切切实实地以知为体,以行为用。因为知是行的本质(体),行是知的表现(用)。行若不以知作主宰,为本质,不能表示知的意义,则行为失其所以为人的行为的本质,而成为纯物理的运动。知是不可见的,知借行为而表现其自身。总之,知是体,行是用;知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行是传达或表现此意义或目的的工具或媒介。贺麟认为,知行同时发动,两相平行,本不能互相决定。但是,这里所谓的决定为内在的决定或逻辑的决定。
这也就是说,知为行的内在的推动原因,知较行有逻辑的先在性。
知永远是目的,是被追求的主要目标;行永远是工具,是服从的、追求的过程。任何人的活动都是一个求知的活动。贺麟的知行观的主要精神是阳明心学的。
贺麟认为,近现代的人生哲学已经走出传统的禁欲主义的藩篱,人们追求功利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功利本身并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和目标应该是非功利或者说超功利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功利与超功利是截然对立的,其实,作为人生的目的和手段,超功利和功利之间构成了主从和体用关系:
功利与非功利(道德的)不是根本对立的,是主与从的关系。非功利是体,功利是用,理财与行仁政,并不冲突,经济的充裕为博施济众之不可少的条件。……功利不仅不与超功利相敌对,反而可以成就理想人格的手段。我们不能说求金钱是人生的目的,但可利用金钱作为发展个性、贡献国家、服务社会的手段。
贺麟在多维度、多视角、全方位的透视中,凸显了文化的有机统一体,展示了文化的全貌。他利用这种文化体用观,逐一检讨了当时流行的各种文化主张,推出自己的文化重建方案——— “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充用”。“以体补充体”,是把西方的正统哲学和基督教精神与中国的儒家思想融为一炉;“以用补充用”,是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贺麟发展儒家的三个构想作为“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充用”的具体实施,以便实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第一,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第二,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第三,须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歌。”
贺麟力图站在哲学人类学的高度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他把哲学看作人类精神的共同财产,认为中西哲学理论风格虽然不同,但本质上仍有相通之处。他强调说:
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无论中国哲学,甚或印度哲学,都是整个哲学的一支,代表整个哲学的一方面。我们都应该把它们视为人类的公共精神财产,我们都应该以同样虚心客观的态度去承受,去理会,去撷英咀华,去融会贯通,去发扬光大。他认为中西哲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应该拘泥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而应该在深刻了解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汲取各方的精神营养,以博大的胸襟超越两者之间的区别,建构一种容纳古今、学贯中西的体用完备的新文化。他说:“我们不必去算这些谁优谁劣的无意识的滥账。我们只需虚怀接受两方的遗产,以充实我们精神的食粮,而深彻地去理会其体用之全,以成就自己有体有用之学。”然而“目下,无论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以及个人生活方面,都使人感觉到有一种危机,从而烦闷、不安。其间原因固然很多,但客观地仔细推究起来,较根本的可说是文化失调。自中西文化接触以来,始终还没有得到好好的调整。中国的文化未曾复兴,对西洋的文化亦还没有正确的认识;而对西洋文化认识不清楚,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亦无法得到正确的了解与评价”。
学者评价贺麟说,在进行文化重建时,贺麟在把握各种文化形态之间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防止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两种片面性的同时,始终力图超出中西文化的界限,向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进而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中国儒家传统融为一体、冶为一炉,其重建中国哲学的努力和中西文化合璧的大方向,对当前文化转型与重构有良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