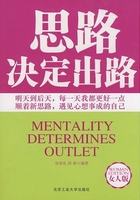然后我再看第二家的汽站资料,嗯,该汽站有六名员工,蛮好,蛮好,我点头。
然后我又翻说是派我去却未能成行的安埠汽站的资料,打开一看,嗯,该汽站有一百六十四名员工,蛮好,蛮好,我点头。
然后我的烟瘾犯了,站起来东瞧西瞅,想找个人没人的地方偷偷抽支烟,向前走了两步,猛然寻思过来不对劲,急忙掉头冲回来,抓起安埠的那份资料再仔细一看,刚才我确实没看错,这家汽站居然真的有一百六四名员工,员工的人数都超过一个连了。
当时我吓得差一点哭出声来,拜托董事长老爹,你不会这么修理我吧?
(3)重操砍人旧业
其实这也不是董事长在修理我,而是没办法的事情。
前者在汽站收购大站中,由于竞争对手的从中阻挠,两方相互抬价,地方汽站自以为奇货可居,不断的加码,提高收购条件。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公司不收购,就肯定会失去终端市场,事实上,正是因为公司实在接受不了那八家大汽站的漫天要价,这才买下了十二家小汽站。
但是汽站虽小,花样却多。尤其是这家安埠汽站,居然往员工花名册上填了一百六十四个人,就是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们的汽站原来会养这么多的闲人,员工又不是肥猪,岂有一个越多越好的道理?而且我们的董事长也清楚是这家汽站恶搞,目的无非是想多弄几个遣散费用,但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却只能任由对方割之宰之,连点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而现在董事长派我去安埠做这个区域经理,话虽然没说,但目的却明明白白,就是要一分遣散费也不掏的把问题解决掉。
如果公司愿意出遣散费用的话,那还轮得到我这么一个区域经理出面?董事长自己早就跑去做善人了。
可这是一个连的兵力啊,我一个人,能够拿下来吗?
当时我是真的傻了眼,直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
我舍不得每月八千元的薪水,可又干不了这力气活,那么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走到窗前,看着外边九州大道上来往的汽车,心里在琢磨,如果我现在从这里跳下去的话,那八千块钱,不知道还算不算数了?如果算的话,那我就干脆跳下去得了。
就在这样想的时候,人力资源经理过来,说是董事长找我。我意兴栅阑的过去,没精打彩的正要敲门,人力资源部经理却已经殷勤的替我推开了门。我抬头一看,只见房间里坐着三男一女,男的有一个是董事长,另两个胖头胖脑,虽然不是董事长,也都差不了多少,另一个女人淡妆,看不出年龄,门一开,几个人抬头都向我望了过来。
见到我,董事长如获至宝,一个箭步跳了起来,拉住我的手,叫着我的名字,连声道: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几个董事。
董事的名字他说完我就忘了,记那玩艺没用。但是,董事长向董事们介绍我的时候,那番话我却是记忆犹新,记得两年前我还和一位朋友说起董事长对我的评价,那位朋友顿时嗤之以鼻:骗了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醒过神来啊?真没见过比你更傻的。
细想我当时的确是一脸傻像,诚如圣人所言,天生傻于予,董事长能奈我何?就这样傻兮兮的站在门口,听着董事长不负责任的乱吹一气:从行政机关里出来的,管理经验一流,处理棘手问题的专家,知道那什么什么企业吧?就是由他来搞定的。
董事长所说的那几家企业我听都没听过,不过这种场合,我还是虚心接受了。
我总不能太不识趣,硬说我没有在哪几家企业做过,让人家董事长难堪吧?
然后,一件让我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三名董事站了起来,排成一队同我握手,并学着日本人的样子不断的向我鞠躬,言不由衷的说道:拜托了,老弟,公司里边的事情全部拜托了。
董事长设计得这一幕让我顿时热血沸腾。
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
不就是个跳楼吗?谁怕谁啊!
董事们躬都鞠了,你再不跳楼,那未免也太不识抬举了吧?
次日,我坐长途小巴赶往安埠,隆重的踏上跳楼之程。
这是我第一次坐小巴士出差,从这以后的几年来,我就是坐着这种卫生情况极差的小巴士,和半路拦车的乡农及他们的青菜行李卷挤在一起,从一个小城市赶往另一个小城市,救火队员一样的奔忙个不停。
直到今天,我一想起那几年的情形,还象是最初一样的激动不已。
那真是壮怀激烈啊!
只可惜那一切的努力,却因为企业内部的相互攻讦,竟尔烟消云散。
但当时我可不知道后来的情况,我要谋生,虽然前面有一个连的兵马阻路,那我也只能是硬着头皮冲过去,别管输赢,死活不论,冲过去再说吧!
我到了安埠当地,下车后就打电话找汽站原来的负责人,询问他汽站的确切地理位置。经由原汽站站长的详细解释之后,我更加糊涂了,只好坐进一辆出租车,让司机送我过去。
司机开车出了城。
司机开车进了山区。
司机开车进了一条泥泞的土路,我开始怀疑这个司机居心不良。
这时候司机向我解释说:汽站属于危险用品,禁止设立在市区之内的。
原来如此。看看,人家一个出租司机,居然比我这个区域经理还明白,你说我还混个什么劲啊。
到了一片荒郊野岭,出租车停了下来,指着路边的一幢破旧房子告诉我,那里就是我要去的汽站。
我站在路边,仔细打量着那幢小楼房,要说这里边装上三二十人,还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想把一连的人马藏在这里,那这些人都得会软骨特技才行。于是我就放了心,迈步向着汽站走了过去。
汽站里只有一个老人值班,该老人神彩奕奕,精神焕发,给了我极好的印象。他热情的招呼我坐下,陪我聊天。当时我就琢磨着,等把这里的事情搞个七七八八,这个老头,还是要留下来的。
老头给我讲当地的风俗,说是当地人迷信,最爱穿红裤子,无论男女,裤子一律是红的,并问我注意到了没有。我闲着没事注意这玩艺干什么?就含笑点头,说我一到这地方就发现了。正聊着,原来的汽站站长开一辆稀哩哗啦的破烂小东风来了,车上还拉着十几个煤气罐。
那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小型的东风,驾驶室里如果挤两个人的话,就会紧紧的贴在一起,适宜情侣工作的时候使用,也适合女员工骚扰男领导,我这么说话,是因为后来果然有一位女员工企图用这辆车骚扰我,幸好我这人虽然笨得可以,可脑子却花花,一看到这辆车的时候就想到这事,提前有了预警,这才免于劫难。
原站长却是个实在人,实在得憨憨厚厚,木枘寡言。他原是老山前线运输连的司机出身,复员转业后就来到了这家汽站,从最底层的搬运工做起,一直做到汽站的站长。但是由于这家汽站是“国营”的,概因天下之事,一旦沾了国营二字,就铁定亏损不可。如美国纽约市的地铁就是国营,不仅脏乱世界知名,亏损得更是一塌糊涂。这家小汽站,自然也不会例外。
有人要买亏损的企业,市府何乐而不为?底下办事的人趁机塞点私货进来,这都是免不了的事情。
上面这句话,是原汽站站长自己说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顿时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事情做得太过了,那就不能怪我跟他们不客气了。
还是在半路上的时候我就不停的考虑这事,现在再一听老站长介绍情况,我的心里就更有底了。我准备考虑的办法,就是把杜老板家族企业的招术全盘搬过来,丢一块骨头让他们自己啃去!
只不过我久在机关,知道人逢到大事的时候会很容易的认命,但却往往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所谓怯于公义,勇于私斗。那些连亏到要塌的煤气站都要捞上一把的人,多半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所以我一定要考虑好退身之策。
我选择了一楼的一间原来用以放杂物的旧房间办公,并把后面的窗户打开。
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后面有着大片的树林,一旦有了突发事件,便于我在第一时间内跳窗夺路而逃,只要我逃到那片树林里,别说区区的一个连,就是一个团的人马,也未必能够找得到我。
(4)贪官造就劳模
一切准备就绪,进入高层公关程序。
其实没什么好公关的,早在董事长一行购买这家汽站的时候,就已经伏下了一条暗线。
当地的政法委书记。
说到政法委书记,这个职务对于绝大多百姓来说,是个稀哩糊涂的职位,如我在辞职前办报纸的时候,就曾因为报道刑事案件几次同政法委书记打过交道。当时那个政法委书记给我的印象是:他独自一人坐在一间大大的办公室里,面对着一堵墙壁发呆,好象除了发呆,他找不到别的更有价值的工作来做。
但等我到了汽站,才终于明白过来。这个政法委书记,实在是不可或缺,重要之极。这一职位统辖警方刑侦力量,沟通司法相关环节,与政府保持着高度的信息往来,协调着民间正在兴起的企业力量与多方政治势力的博弈态势。总之,政法委书记一职是建立在警、政、司法与企业这四者之间的重要枢钮,缺少了这个枢钮,这个社会非乱了套不可。
我真佩服当初设立政法委书记职位的那个人的天才思维,如此精密的社会组织设计,真不知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如果没有政法委书记这个职位,汽站与消防、民政以及其它社会环节的沟通,成本势必会突破企业的承受能力。而现在有了这位天天对着墙壁发呆的老兄,企业就省了太多的麻烦。而现在企业主动找上门来求助,政法委书记也是兴奋得热泪盈眶语无伦次,他终于不用再对着墙壁发呆了,企业找上门来,这就证明了他的存在价值。
喝酒,我酒精过敏,酒精之于我一如毒药。政法委书记说:瞎说!我咬牙点头,是瞎说,然后灌酒,然后一头钻桌子底下,人事不省。这件丢人现眼的事过去好多年了,我一直记忆犹新,因为那次喝酒我喝到人事不省,是政法委书记老兄买的单。估计那老兄至今还恨我入骨。
酒醒了,办正事,继续和老汽站站长谈话,我说:一百六十四个人,这太出格了,给我一个合理的人数吧,不然的话咱们俩都没法交待啊。
汽站站长果然老实,就点头,退让,拿出新的员工花名册来,人数少了一半。万万想不到事情的解决竟然是如此的容易,我抑制住心头的狂喜,假装极不满意的皱眉,等站长一出去,我飞扑过去拿起电话,向董事长报喜,着重渲染了一下我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人数清理掉了一半的战绩。
我越来越变得油滑,变得厚颜无耻了。
董事长听了,无喜无嗔,鼓励道:继续努力!就挂了电话。
我看汽站站长如此老实,就欺负他,继续谈话:八十多人,这也太离谱了,全地球上也找不到第二家这样的汽站,咱们没法子跟总部交待啊。
汽站站长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回他自己办公室,咬牙切齿,又勾掉了二十多个人,然后又把名单拿回来,说:我的能力就到这一步了,六十多个人是多了一点,可这些人都是有来头的,我是一个也碰不起,你看着办吧!
我心花怒放,接过名单,心想一个连的兵力眨眼功夫就缩水了一多半,这生意划得来。早知道这事情如此容易解决,我当时就应该再跟董事长卖卖乖!但眼下这六十多号人马,只怕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好在我早有妙计于心,谅这六十多人,也不会如何难对付。
先招集员工开会,员工到了三十多个,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其中有系围裙的家庭妇女及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十几名,不知道她们都是谁的关系,硬是混进来充数来了。先是汽站站长讲话,然后我开讲,但我讲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我不知怎么竟突然紧张了起来,站在这些人前面,两条腿激烈的颤抖着,抖到了我几乎站立不住的程度,而且我的头开始发晕,大脑缺氧,一片空白,感觉自己随时都会晕过去。背了多半夜的“亲民善词”,到这时候却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实际情况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在超过三十多人的场合上讲过话,此前虽然不时有夸夸其谈之举,却都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内,对着最多不过三、五个人,而现在突然要对三十多人讲话,不由自主的就露了怯。
虽然露了怯,但我还在讲,至于我到底讲了什么,那就不太清楚了。只记得老站长带头鼓掌,然后大家响起了稀拉拉的掌声,我长舒了一口气,急忙退回去坐下,身体还失去控制的战瑟着。
然后老站长又说了几句,问我:下面呢?我当时心里害怕得真想撒腿逃开,就嘟囔了一句:散会。实际上接下来是要宣布新的管理规章,要求全体员工回汽站上班,但因为我心里怕到了极点,只想快点逃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就稀哩糊涂的提前宣布了散会。
这次意外的事件让我恨透了自己,我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平时一张嘴呜哇呜哇,怎么偏偏到了关键场合,就顶不住了呢?我最害怕的是老站长识破我色厉内茬的真实面目,万一这老东西要是跟我对着干,那我就死定了。
幸好老站长是个实在人,他居然非常佩服我临时在员工大会上取消了宣布严厉的规章的“决定”,并认为我这个人“太有心眼了”,靠不住。此后虽然我多次向他表示友善,这老家伙对我却始终不远不近,不卑不亢。关于他对我的这种态度,我也是隔了好久也想清楚:
原来,相对于我来说,这个老家伙更希望能够快一点把汽站的人事关系理顺,因为他和我不同,我只是个无根飘浮的职业经理人,汽站搞好搞不好,跟我关系并不大。可他却是这一辈子都要靠着汽站吃饭的,一旦汽站搞砸了,他这辈子就没的混了。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对于我的严格管理方案,是极为支持的,并满怀期望的等我大发神威,一劳永逸的解决掉因为汽站收购所带来的人员问题,万不曾想我在会议上却突然不提这事了,在他看来,我不提这事,就明摆着还是把这事留给他处理,所以他才说不出来的窝火。
我当时全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也不明白我是怎么想的,我们两个就这么胡乱猜谜。我坐在办公室里琢磨着怎么解决问题,而他却硬着头皮再从花名册上将当地的小官员趁乱添写在员工花名册上的家庭妇女和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都划掉,并告诉对方说我早已知道了这件事,他完全是按了我的意思办的。
我猜那些家庭妇女们到现在可能还在恨我。
最后老站长拿了一张仅有二十三人的员工名单给我,还拿出了以前的财会开支凭据,这些人,在汽站已经支领工资好多年了,他们都是汽站的正式职工。
这件事当时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只是后来离开公司之后,我静下心来慢慢反省,才发现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这个社会里,越是处于底层的人,越是卖力的苦干,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立身之本。而许多熟谙社会游戏规则的人,却全不管这些麻烦事,他们知道底下人肯定会为了糊口而拼命干的,所以他们只管捞自己的,如果遇到捞得过凶的上司,下面的人多半还会出一个两个的劳模,因为劳模把贪官应该操心的事情全都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