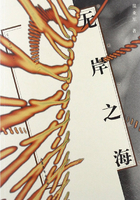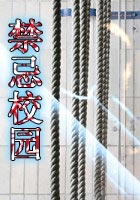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像只猫似的,死死地盯着他看,接着又说道:“效力不像以前那么大了?是啊!也许开头是这样。在这点上你可能是对的。习惯成自然嘛。我会找到办法让你开口的,我的好人。”
不管怎样,他都没有再开口。他死一般地躺在那里,毫无声息,只有脸和四肢不时地扭动几下,样子十分丑陋。肮脏的蜡烛快要点完了,女人用手指夹着即将熄灭的蜡烛头,点亮了另一支,把烧剩的蜡烛头深深地塞进了烛台,把新蜡烛插在它的上面,仿佛在给一件又臭又难看的行使妖术的武器装弹药。新蜡烛也快点完了,他还是躺着,没有知觉。最后,剩下的一点蜡烛头也点完了,曙光照进了屋子。
过了没多久,他坐了起来,冷得直哆嗦,渐渐地恢复了意识,想起了自己在哪里,于是准备动身走了。女人收了他付的钱,道谢了一声:“上帝保佑你,我的好人!”似乎已经相当疲倦,只等他一走就打算睡了。
但是“似乎”只是猜测,猜测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这一次却错了。因为他刚刚走下楼,楼梯的吱嘎声刚刚消失,她便蹑手蹑脚地溜出屋子,跟在他的后面,恨恨地嘟哝着:“我绝不会让你第二次溜走的!”
这个院子除了进来的门,没有其他的出口。她站在门洞里,诡异地向外张望着,怕他回头看见。他在消失以前并没有回头,脚步摇摇晃晃的。她跟在后面,从院子里往外看,只见他趔趔趄趄,只顾向前赶路。她紧紧地盯住了他。
他走到奥尔德门街的背后,在一扇门上敲了敲,门马上开了。她蜷缩在另一个门洞里,注视着那扇门,毫无疑问,他目前就暂住在那里。她守了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坚持不懈。如果饿了,一百码以内就有家面包辅,也可以从路过的小贩手里买一杯牛奶,她就这样解决了饮食的问题。
到了中午,他又出现了,已经换了衣服,但是手中没拿什么,也没有人帮他拿什么。这么看来,眼下他还不准备回乡下。她跟踪了一段路,犹豫了一会儿,马上毫不迟疑地折回了原处,径直地走进他刚刚离开的屋子。
“修道城来的一位先生在不在屋里?”
“他刚出去。”
“真不巧。那位先生什么时候回修道城?”
“今晚六时。”
“啊,谢谢你。愿上帝保佑你们生意兴隆。你们真好,对一个可怜的穷女人提出的问题,也回答得这么客气!”
“我不会让你第二次溜走的!”这可怜的女人在街上反复嘀咕着,口气可不太客气,“上次被你溜走了,你下了火车,坐进来往于火车站和修道城的公共马车,就不见了。那时我还不能肯定你是否会直接到城里去。现在我可知道了。我这修道城来的主顾啊,我要先赶往那儿,等你回去。我发誓,我绝不会让你第二次溜走了!”
就这样,当天晚上,这个可怜的女人已经站在了修道城的大街上,眺望着修女之家那面古色古香的高墙,随意消磨着时间,一直等到了9点钟。这时,公共马车到了,她估计,她关心的人可能就在车上。好在黑夜是友好的,使她可以躲在暗处,看看究竟如何。一点也不错,那个她绝不让他第二次溜走的人,果然就在旅客中间。
“现在,让我看看你是个什么角色。走吧!”
这是对着空气讲的,然而好像也是对着那个旅客讲的,因为他显得那么听话,马上沿着大街匆匆地走去,但是到了拱门的入口处便出人意料地不见了。可怜的女人加快了步子,敏捷地跟了上去,紧跟着来到了拱门下面,但是只看到一边是一道楼梯,另一边是一间古老的拱顶屋子,有一个大脑袋、满头白发的先生正坐在屋里写字。这样开着门对着大街写字是很奇怪的,而且还看着街上的人从他的面前走过,仿佛他是守在门洞口收通行税的,尽管这条路其实是不收税的。
“喂!”他看到她在门口站住了,小声地喊道,“你要找谁?”
“有一位先生刚才走到这儿,忽然不见了,先生。他戴着孝。”
“是的,有这么一个人。你找他有什么事?”
“他住在哪里,我的好人?”
“住在哪里?就在这楼梯上面。”
“谢谢你!让我们小声一点。我的好人,他叫什么名字?”
“姓贾思伯,教名约翰。约翰·贾思伯先生。”
“我的好先生,他有职业吗?”
“职业?有啊。他在唱诗班唱歌。”
“在唱歌学校?”
“唱诗班。”
“那是什么?”
戴吉利先生从桌边站了起来,走到了门口,诙谐地问道:“你知道什么是大教堂吗?”女人点了点头。
“那是什么?”
她有些为难,心里琢磨着应该怎样去下定义,突然想起,不如利用该实物本身来进行说明,于是便指了指矗立在黑暗的天空下,漫天的星星面前的那个庞然大物。
“回答得不错。明天早晨7点,你去那儿,就可以看到约翰·贾思伯先生,还可以听到他唱歌。”
“谢谢你!谢谢你!”
这种如获至宝的感激神态,并没有逃过这位老单身汉的眼睛,尽管他的性情随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他打量了她一下,一边按照这类老人的习惯,背着双手,在发出回声的马路上,跟她一起信步走去。
他把头向后一扭,试探着问道:“不过,你也可以现在就到贾思伯先生的屋里找他。”
女人露出狡猾的微笑,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
“哦!你不想找他讲话?”
她重复了保持缄默的回答,让嘴唇形成了一个无声的“不”字。
“只要你高兴,你每天都可以从远处瞻仰他三次。不过特地从远道赶来可不大值得。”
女人突然抬头看了他一眼。如果戴吉利先生以为,他这么略施小技就可以使她说出她的来历,他未免太自不量力,太小看了她。不过她想,看他那副吊儿郎当的走路样子,这不过是当地一个人人讨厌的无名之辈,他何必对她耍这种花招呢。他没有戴帽子,一头白发随风飘动,无所事事的手还在裤兜里把几个零钱弄得叮叮直响。
钱的叮叮声吸引了她贪婪的耳朵:“好先生,你能给我几个钱付旅馆费和路费吗?我是个可怜的穷女人,真的,又有病,咳嗽得厉害。”
“我看,你知道旅馆在哪儿,你正朝那里走呢。”戴吉利先生做出了和蔼的反应,仍然在把裤兜里的钱弄得叮叮直响,“可怜的女人,你经常到这儿来吗?”
“一生中只来过一次。”
“哦,是吗?”
他们走到了教士葡萄园的入口处。看到这个地方,女人心中相应的回忆复活了,它发挥了出色的模仿能力,把过去的一幕情景再现在她的眼前。她在门口站住了,兴奋地说道:“这个地方使我想起了一件事,说出来你也许不信,但这是真的。上次我正在这片草地上咳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先生给了我三先令六便士。我向他讨了三先令六便士,他给了我。”
“你自己提出数目,是不是显得不太客气?”戴吉利先生说道,仍然把钱弄得叮叮作响,“一般来说,数目应该让别人来定,对不对?你那样做,不是好像——当然只是好像——在向那个年轻人讨债了吗?”
“我告诉你,我的好人,”她回答道,用的是信任和劝说的口气,“我要这钱是准备买药的,这种药对我很有用,我也靠它来做些生意,维持生活。我就这么告诉那个年轻人,他就给了我钱,我一文都没有乱花,全都用在这药上了。我现在也需要同样的数目,做同样的用途。要是你肯给我,我也会一文都不乱花,都用在这药上,我保证!”
“这是什么药?”
“我不妨对你老实说,我绝不想骗你。是鸦片。”
戴吉利先生突然变了脸色,迅速地看了她一眼。
“是的,是鸦片,我的好人,就是这东西。它像人一样,你老是听到别人讲它的坏话,可是很少有人会讲它一句好话。”
戴吉利先生开始照着她要的数目数钱,动作非常缓慢。她用贪婪的眼睛望着他的手,继续讲下去,向他提供一个伟大的榜样。
“那是在去年圣诞节前夜,上次我来的时候,天刚刚黑下来,那个年轻人给了我三先令六便士。”
戴吉利先生停止了数钱,发现他数错了,于是又把钱合在一起,重新再数。
“那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埃德温。”她接着说道。
戴吉利先生掉了几个钱,于是俯下身去捡钱,由于用力,脸都涨红了。他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个年轻人的名字?”
“我问他叫什么,他告诉了我。我只问了他两个问题:他的教名是什么,他有没有情人。他回答道,他名叫埃德温,没有情人。”
戴吉利先生拿着数出的钱,停了一会,好像在默默地估计它们的价值,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似的。可怜的穷女人看了有些不放心,对他的改变主意感到有些生气,正打算发作,他却把钱递给了她,似乎他另有心事,根本没有在想这些钱。她对他千谢万谢,然后就走了。
戴吉利先生独自回来时,约翰·贾思伯房间里的灯亮了,他的屋子像灯塔似的照耀着。水手在危险的航行中,来到岩石包围的岸边,总要凭借灯塔的光芒,才能看清楚它另一边的港口,否则就无法到达目的地。戴吉利先生目前也是这样,他把目光集中在这灯塔上,要靠它才能走向在另一边的目的地。
不过眼前他返回寓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戴上他的帽子,尽管它在他的衣着中似乎是一件多余的装饰品。这时,根据大教堂的钟声是十点半,他又走出了门,来到了街上。他慢慢地走着,注意着周围的动静,似乎德道斯先生被石子赶回家中的迷人时刻早已过去,有希望找到那个担当扔石子任务的小鬼了。
确实,这个小鬼还在马路上。这时他的石子已经找不到活靶子了,因此戴吉利先生发现,他正在做一件对鬼神不敬的事,他正从墓园的栏杆外面打里面的死人靶子。这件事他觉得不但非常有趣,而且可以表现他蔑视权威的气魄,因为,首先,灵魂安息的地方一向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次,那些高高的石碑很像他们本人正在夜间出巡,打它们可以引起美好的联想,仿佛他们本人挨了打,受了伤似的。
戴吉利先生向他喊道:“喂,夜猫子!”
他回应道:“喂,温克斯!”他们认识以来,似乎已经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但是,我要说,”他接着提出了抗议,“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公开嚷嚷。要知道,我从来不稀罕有什么名字。他们在拘留所要登记我的名字的时候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你们自己调查去。’同样的,他们还问我:‘你信什么宗教?’我说:‘你们自己调查去。’顺便说一句,在这个国家里,不论它有多少统计表格,要查清楚这点还是非常困难的。”
“再说,”这个男孩接着说道,“你怎么也查不到夜猫子这个姓。”
“我想一定有的。”
“你撒谎,肯定没有。旅客们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是因为我整夜睡不安稳,随时可以被叫醒,我只能闭上一只眼睛,另一只一直睁着。这就是夜猫子这个名字的来历。还是叫我小掌柜最合适,但是我才不会要求别人这样称呼我呢。”
“那么今后我就叫你小掌柜吧。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小掌柜,对不对?”
“相当好。”
“我将我们第一次认识时你欠我的债一笔勾销了。从那之后,我还有不少个六个便士进入了你的腰包。小掌柜,对不对?”
“是的!更重要的是,你不是贾思伯的朋友。那家伙为什么总是要把我提到半空中,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但是现在暂且不去管他。今晚我可以给你一个先令,小掌柜。你们店里刚来了一个旅客,我跟她谈过话,那是一个老是咳嗽、身体虚弱的女人。”
“大烟鬼。”小掌柜回答道,一边狡猾地眨着眼睛,表示他认识这个女人,一边尽量侧转了头,做出抽鸦片的姿势,眼珠骨碌碌地直打转,仿佛要从眼眶中跳出来似的,“抽鸦片的。”
“她叫什么名字?”
“鸦片公主。”
“她应该还有别的名字。她住在哪里?”
“住在伦敦。跟杰克们在一起。”
“那是指水手们?”
“是的,我叫他们杰克。其中有中国人,还有随身带刀的坏人们。”
“我想通过你知道她究竟住在哪里。”
“可以。把钱给我。”
一个先令递了过去。一切商业交易中,信用第一,现在这笔生意也根据这个原则谈妥了。
“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小掌柜喊道,“你猜,明天早上鸦片公主要去哪儿?她要去大教堂!”他讲得来了劲,竟把“大教堂”这个词拖得那么长,还直拍大腿,笑得前仰后合的,声音非常尖利。
“你是怎么知道的,小掌柜?”
“她刚才亲口对我说的。她说她必须早起,有事出门。她说,小掌柜,我一早就得洗脸,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因为我要上大教堂。”他像刚才一样起劲,把“大教堂”这个词的音节一个个分开,拉得长长的。似乎在地上跺脚还不足以发泄他的幽默感,他干脆慢腾腾地、大模大样地跳起舞来——也许在他的想象中,教长就是这么一副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