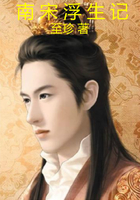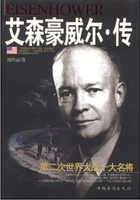收复三京
1233年10月,权倾一时的丞相史弥远去世了。在登基八年之后,宋理宗终于能够亲政了。与他的好几位祖先一样,这又是一个“时刻不忘恢复大计”、“急欲洗濯三十年积弊”的皇帝。为了表示自己励精图治的决心和能力,他立刻决定将第二年的年号改成“端平”,还“诏求直言”,罢斥史弥远一党,召回了被史弥远贬谪的真德秀等十几名大臣,对他们委以要职。一时间俨然成了明君,史称“端平更化”。
仅仅这些,理宗显然觉得是不够的,他还要拓展疆土,恢复中原,建立他的中兴伟业、不世功勋。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黄河以南领土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以赵范、赵葵兄弟为代表的一些人欲乘机抚定中原,提出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建议。而大部分朝臣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认为已经被战乱破坏殆尽的中原地带无法提供粮草,再加上南宋军队没有骑兵,军队的机动能力有限,无法防御漫长的黄河防线。另外,这也会造成蒙古向宋朝宣战借口。就连赵范部下的参议官邱岳,亦认为不应破坏盟约;史嵩之、杜杲等也说宜守不宜战;参政乔行简更是上疏谏阻,所言最详,其表曰: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复之机,以大有为之资,当有可为之会,则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忧出师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有功而至于不可继,则其忧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内而后治外。陛下视今日之内治,其已举乎,其未举乎?向未揽权之前,其敝凡几?今既亲政之后,其已更新者凡几?欲用君子,则其志未尽伸;欲去小人,则其心未尽革。上有厉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务任责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贪墨之令,而州县之黩货不知盈厌者自如。欲行楮令,则外郡之新券虽低价而莫售;欲平物价,则京师之百货视旧直而不殊。纪纲法度,多颓弛而未张;赏刑号令,皆玩视而不肃。此皆陛下国内之臣子,犹令之而未从,作之而不应,乃欲阖辟乾坤,混一区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尽如吾意乎?此臣之所忧者一也。
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为根本。数十年来,上下皆怀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谓义。民方憾于守令,缓急岂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爱其将校,临陈岂有奋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愤,积于平日,见难则避,遇敌则奔,唯利是顾,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转移固结之,遽欲驱之北乡,从事于锋镝,忠义之心何由而发?况乎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厄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报怨,茶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萧墙之忧凛未可保。万一兵兴于外,缀于强敌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复有如江、闽、东浙之事,其将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内郡武备单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时江、闽、东浙之寇,皆藉边兵以制之。今此曹犹多窜伏山谷,窥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势不能以相及,宁不又动其奸心?此臣之所忧者二也。
自古英君,规恢进取,必须选将练兵,丰财足食,然后举事。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能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辈,恐不足以备驱驰。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非按籍得二三十万众,恐不足以事进取。借曰帅臣威望素著,以意气招徕,以功赏激劝,推择行伍即可为将,接纳降附即可为兵,臣实未知钱粮之所从出也。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之馈饷,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岁,不知累几千金而后可以供其费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县多赤立之帑,大军一动,厥费多端,其将何以给之?今陛下不爱金币以应边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后,兵事未已,欲中辍则废前功,欲勉强则无事力。国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矣。中原蹂践之余,所在空旷,纵使东南有米可运,然道里辽远,宁免乏绝,由淮而进,纵有河渠可通,宁无盗贼邀取之患?由襄而进,必负载二十钟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达。若顿师千里之外,粮道不继,当此之时,孙、吴为谋主,韩、彭为兵帅,亦恐无以为策。他日运粮不继,进退不能,必劳圣虑,此臣之所忧者三也。
愿陛下坚持圣意,定为国论,以绝纷纷之说。
乔行简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但只说到了知己知彼的“知己”一半,关于“彼”的情形,乔行简尚不曾提及。关于蒙古军队的编制、战略、战术、战力等情况,当时宋朝的大小官吏知道的很少,不了解敌情就试图贸然兴兵,南宋可谓未战便先输了一半。
然而,诸多忠臣良将苦口婆心地劝谏,却被收复三京鬼迷心窍的理宗置若罔闻。沉醉在中兴大宋美梦中的理宗皇帝,一面虚与委蛇地表示从善如流,一面又固执己见地颁布了“端平入洛”的出师檄文:“蠢兹女真,紊我王略,遂至同文之俗,半为左衽之污……因彼鹬蚌之相持,甚于豺狼之交啮。百姓至此极也……痛念君师之责,实均父母之怀。乃敕元戎,往清余孽。”总的意思就是说,当年这里就是我的地盘,现在蒙古人和金人打仗,老百姓受苦了,我要解民于倒悬,派兵救你们来了!
由于理宗亲自拍板,朝廷最终决定发兵入洛,但发兵入洛能否成功实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成了关键人物。当朝廷把这一决定告诉史嵩之时,他坚决反对,并上书六条,力陈己见;在两淮军出动之后,理宗以兵部尚书的职位来诱惑他参加,竟也被他一口回绝!
西据雄关,北凭黄河,如同金朝后期那样与蒙古抵抗。当年北宋依靠这条防线只抵抗住金兵几个月,金朝依靠它也只抵抗住蒙军几个月,而此时的理宗和赵范、赵葵兄弟,却仿佛认为可以用它来永久地抵御强大的蒙古。
在宋理宗赵昀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下,南宋的军队和物资开始在淮河前线迅速集结。宋军的意图是,由知庐州的全子才为前锋,率淮西兵一万人从庐州出发,由寿州渡淮河到亳州,再向北直扑汴京;由淮东制置使赵葵为主将,率淮东兵五万,准备先攻占泗州、宿州等淮河流域地区,而后也折向汴京与全子才会合。同时加封赵葵为南京(今河南归德)留守、京河制置使、兵部尚书,作为前线的总指挥。另外派赵范为两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作为全局的总指挥和总后援。
理宗只派两淮的六万军队北伐,试图以这六万人去收复中原,确实有些异想天开。要知道,原先即使是主战派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表示要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防御,才能守住黄河防线,才能拒蒙古人于黄河以北。本来十五万都是很不现实的数字,金朝用了四个十五万最终都守不住黄河,南宋的百战精锐能够一个当金兵五个吗?何况宋理宗还一下子将兵力削减到六万,既要抢占要塞,攻城夺地,又要建设防线巩固河防,而且还是在刚经历了十多年战乱、“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地区。此时,心血来潮的宋理宗已基本丧失了理智。
1234年(端平元年)6月,自不量力的宋理宗正式下诏出兵河南。12日,已至庐州,不久又以被晋升为关陕制置使的全子才为主将,率淮西军万余人作为先遣部队,首先从庐州出发,向寿州、蒙城、亳州方向前进。不久,赵葵亲率宋军主力淮东军五万余人向泗州、宿州进发,两军约定会师汴京。就这样,端平入洛开始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战争之一的、一场将要决定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生死大决战的序幕正在悄悄拉开,它的意义之大可能人们在数百年之内也看不到。
滚滚的长江一刻不停地向东奔流着,它可曾知道,不久之后,人们的鲜血将会染红这条大江吗?也许,对它来说这早已是司空见惯了吧。
全子才指挥的宋军先遣军,很快到达了进军出发地寿州,并于6月18日从寿州出发,北渡淮河。离开宋境不久,一片劫后余生惨相就展示在宋军官兵面前,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偶尔有几个劫后余生的居民,也只是在一旁悄悄地望着他们,或是来乞讨一些食物。6月21日,宋军抵达蒙城,“城中空无所有,仅存伤残之民数十而已”;22日,宋军抵达当年曾被称为“小东京”的著名繁华城镇城父,发现城中未毁的建筑只剩下官舍两三处,民居十几家而已;24日,全子才军进入亳州,获得了出师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守城官兵七人向他投降!
更糟糕的是,知道宋人出兵的消息之后,蒙军竟然掘开了黄河南岸的“寸金堤”,仅仅从这个名字,我们就不难想象出这一堤防的重要程度。寸金堤一旦被掘开,黄河顿时改道,豫东尽成泽国!事实上,过了淮河不久,宋军就必须在泥泞中前进了。
虽然不断有谍报传来,但宋朝君臣怎么也想象不到,蒙古人的破坏性竟然是这样的强!欧洲历史学家记载,在蒙古西征大军通过之后,从中亚到东欧,出现了一条数千公里长、数百公里宽的无人地带。而在中原地区,这个不久以前还是世界上最繁华富庶的地区,已是“寂无烟火,骨殖横道”。蒙军的破坏力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宋军将士很快就失去了刚出发时的亢奋,一路看到的这一切仿佛一股阴云笼罩着他们。不过他们毕竟是两淮军的精锐之师!要知道,在南宋第一线的三个战区中,两淮战区由于直接掩护着临安府的正面,因而是最受重视,兵力最强的战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宋军的精锐也是不过分的。因此,即使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也还是坚持在泥水中跋涉着前进,“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在近乎无人的水网地带跋涉了二十天之后,全子才军终于在七月初二抵达汴京城东。
宋军刚到达汴京城外不久,就与投降蒙古的金朝官吏李伯渊等人取得了联系。对他们来说,毫无疑问宋军要比蒙古人可亲得多,这里毕竟是北宋的故都,居民大多也都是汉人。蒙古派原金降将崔立留守汴京,崔立平时骄横跋扈、为所欲为,都尉李伯渊、李琦素为崔立所虐待,他们对崔立早已恨之入骨。平常被逼无奈,只得忍气吞声、不敢发作;今闻得宋军来攻,悄悄与宋通书约定投降,李伯渊假意与崔立商量守备,趁其不备,随即拔出匕首将其刺死,再把崔立的尸体系在马尾,号令军前说道:“崔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所无,应该杀么?”百姓齐声应道:“该杀!该杀!他的罪恶,杀兴还嫌轻的。”李伯渊当下割了崔立的首级,尸骸横在街上,军民脔割,顷刻而尽。后打开城门,迎接全子才军入城。兵不血刃收复汴京的胜利多少鼓舞了一些宋军的士气,他们终于进入这座从他们曾祖、高祖时代就梦寐以求和望眼欲穿要恢复的城市了!
1234年,即南宋端平元年七月初五,全子才率宋军进入汴京城,梦幻般地实现了岳飞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实现的梦想。大宋的旗帜在消失了一百零七年五个月整之后,再次在汴京城上飘扬,只是汴京已经不是当年的汴京了。当他们整队开进汴京开封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迎接宋军的,不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繁华都市,而是六七百守军、千余户人家和遍地荆棘遗骸的废都。绝大多数居民不是死于战火,就是被蒙军掳至河北“就食”,只有一对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老夫妻,站在街中心仿佛在迎接他们的到来。全子才离得很远便下马,步行走到这对老夫妻近前,深施一躬道:“多谢两位老人家夹道而迎,子才感激之至。”老汉眼含热泪看着全子才,显得异常激动,他一把拉住全子才的手道:“你咋才来咧,这些年你们都弄啥去了?”
全子才一声长叹,塞给老汉一把散碎银子,然后翻身上马,率军入城。曾经拥有一百四十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市东京汴梁,如今已是满目疮痍、一片凄凉。可谓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更加始料未及的是,宋军在长途跋涉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粮饷已经不济,军中几乎没有存粮可言。如果说一支轻装的精锐部队只能勉强抵达这里的话,那么运粮的车队又该怎么办呢?
由于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坚决反对端平入洛,朝廷诏令史嵩之筹划粮饷,史嵩之上奏道:“臣熟虑根本,周思利害,甘受迟钝之讥,思出万全之计。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其势必至于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馑之卒,未战先溃。当此之际,正恐重贻宵旰之虑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纸调发,东西唯命。然事关根本,愿计其成,必计其败;既虑其始,必虑其终,谨而慎之,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若夫和好之与进取,决不两立。臣受任守边,适当事会交至之冲,议论纷纭之际。雷同和附,以致误国,其罪当诛;确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宁之旨,罪亦当诛。迕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其大意就是,荆襄之地连年受灾,百姓民不聊生,再征调他们去运粮,他们就逃亡各地了,无家可归就必然当强盗了……
史嵩之所说看似向皇帝诉苦,实则完全是制造借口。史嵩之在襄阳十几年,主要功绩在于经理屯田,至绍定元年,史嵩之已积谷六十八万石。一年前的冬天,京湖战区能给围攻蔡州的蒙古军运去三十万石军粮,今年夏天就没法给开封、洛阳提供军粮了么?非得要从两淮千里迢迢地转运?可见补给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南宋没有协调解决好内部矛盾的结果。
事实上,史嵩之找借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其个性而论,他是不愿意给人做嫁衣裳的。据关守河的策略是守将赵葵等提出的,如果成功了,无论怎样,头功自然不会落在史嵩之的头上,更何况史嵩之素来不愿与淮东制置使赵葵合作。二是自史弥远去世后,史氏家族虽然在各方面仍然受到优待,但相比之下,史家受到的优待,得到的重用,与弥远在相位时就大相径庭了。当时郑清之为弥合朝廷裂痕,达到和谐团结,召还了真德秀、魏了翁、游似、洪咨夔、李宗勉、杜范等不愿与史弥远合作的名贤,这些名贤涵盖了朱学、陆学、吕学三个学派的知名人士,由他们共同来执政,朝堂一时出现振兴气象,被称为“小元祐”。但这一做法显然彻底改变了史弥远执政时期“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明人”的局面。郑清之这种出于内外政治需要的对各学派人士主动示好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冷落了四明人,在“小元祐”的朝堂没有一个四明人(端平二年才算让四明人陈卓入朝任参知政事),结果郑清之不仅既得罪了四明人,也没有达到弥合朝廷裂痕的目的。相反,这些召还的名贤,尤其是朱学人士杜范等人,因曾得益于乔行简的提拔,便很快就与乔行简建立同盟,帮助乔行简谋相位以取代郑清之。在史嵩之看来这就是“迂缓这一套”。因此想复兴史氏家族,恢复四明人的地位,史嵩之觉得只能靠他自己了。这是史嵩之不愿同郑清之携手合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