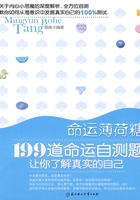梦醒过来,梦里头那些欢声笑语仿佛打散的玻璃碎片,一块块拿起了都听得见看得明,可想凑齐了却做不到,裂缝边缘俱是利刃,即便皮糙肉厚兼意志坚定的穆先生,也会扎得满手鲜血,伤痕累累。
梦里的空间,以其惯有的荒诞布局,却显示一种异乎寻常的真实感,真实到他仿佛确实在那生活了几十年,确实有过一个叫倪春燕的老婆,他们俩生了一个叫慕斐然的小男孩。那孩子很调皮,被家里的女性成员宠过了头,时不时会有些娇气,可是他天性善良,崇拜自己的父亲,小小年纪就被教导得很有责任感。
他们一家人中还包括一个叫穆珏的奶奶,有一个智力永远停滞的小舅子,他们家很热闹,有两个孩子,家里便状况不断,整天鸡飞狗跳,可人气很足。
不像穆公馆,富丽堂皇,仆佣成群,一堆成年人伺候他一个,可却时时刻刻显得冷清空旷,很奇怪。
穆昱宇活到三十出头,才发现有那么一种活法居然可能是存在的:房子不大,存款想必也没多少,生存压力不减反增,职业生涯也未见得有多出息,年纪一大,中年男人的颓势就出现了,那些个抱负野心势必要在现实跟前节节退让。一个大男人要养活一大家子人,想必经济窘困也时时出现,这样的人生在他看来,几乎都可以冠以窝囊两个字。
哪里及得上他现在成就之万一?
可他的家人都在。那个穆昱宇,他但凡有个头疼脑热的有的是人心疼,老婆会把热饭热菜伺候到他床头,孩子们会格外乖巧,围着他唱儿歌;还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还在,她会用她特有的幽默一边调侃他,一边照料他快点康复。
在那种环境下活着的穆昱宇,想必性格要软弱得多,相应的,他也必然无能得多。但是,那一个穆昱宇有什么必要非得算无遗策刀枪不入?他又不用对那么多员工的生计负责,不用挑着一个大公司的担子时刻提防明里暗里那么多敌人。他大概从未经历过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刺激和危险,他也没尝试过巨大的成功和成功后呈几何倍数增长的压力。
那个穆昱宇还有一点令他耿耿于怀,那就是他无论怎样都不会一个人。他干什么都有家人帮衬扶持着,他哪怕在外边跟一坨狗屎似的一败涂地,回家了还是有人将他当宝。
不用花钱,不用签合同,不用恩威并施,不用如心理学家一样洞悉人性弱点,将人际关系弄成心理对峙战,不用做任何事,就他妈的有人对他好。
无条件的好。
穆昱宇有些怅然,他并不是见了梦里那么多的温情就忙不迭地否定自己,他到目前为止,仍然不对自己选择的人生有任何怀疑。因为那是符合他性格的,遵循他的价值观和野心必须要做的选择,他对此绝不后悔。
但在此之余,那个梦中的温情却令他获得异乎寻常的平静,他想,原来多少往事就这么在指缝间宛若流沙倾泻殆尽了啊,原来回溯过往,在某年某日的某个分叉点上,他选择了倪春燕,那整个人生真的会截然不同。
他冷静地想着另一个穆昱宇的得得失失,在梦醒以后,他在自己华丽而空旷的宅院里,看着叶芷澜弄出来的各种后现代艺术痕迹:墙上挂的抽象画,地上铺的色彩冷峻的地毯,边角上耸立的形状怪异的金属雕塑品,配合上全玻璃设计的通透和冷硬,整栋房子就如一个扮演着激进与先锋的艺术青年,嘴里喊着口号,动不动要批判和申诉一样。穆昱宇忽然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自己能在这样的房子里活了这么久?他跟这栋房子,跟这个房子里的女人如此格格不入,简直南辕北辙,可他却一直以无视的姿态忍受了下来。
这时他回想起自己在梦中的那套房子,小三房,陈设老土杂乱,因为有了孩子还经常能抬脚就踩到一个玩具,可在那个环境中,他觉得很合契,像房子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一呼一吸,都能感同身受。
穆昱宇点上雪茄,在自己的书房里,以谋算某个重大项目的谨慎,第一次认真思考那个怪梦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想,梦里空间带给他的全部触动,就在于他慢慢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人,剔除掉穆先生的强硬外壳后,他的内里,其实还是一个普通男人。
而且是个普通的中国式男人,他并不反感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观念,那个琐碎到鸡毛蒜皮的梦中生活,其实留有他全部的温存。
就如亲生母亲留下的绣花手绢,在现实中几经人世沧桑,分明早已不知道丢哪去,想找也不可能找得到。可它在梦里被完整复制了,它所代表的全部爱意,也被完整保存在那里。
这种爱意联系着内心的渴望,尽管不激越,不焦灼,可是却细水长流,不停冲刷。穆昱宇慢慢站了起来,他徐徐吐出烟圈,食指叩击桌面,他想既然自己是个普通男人,那有这样的渴望也不奇怪,但他绝对不愿意放弃作为穆昱宇先生的所有既得利益,因此,他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在当穆先生的同时,又能将梦里的温情原封不动搬到现实中享用?
他从来不否认自己又贪婪又自私,这两样品德在他看来就是原始资本积累的原动力,也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他想我既然是个商人,那么就该干点商人应该干的事,明确目标,将利益现实化。
很简单,把倪春燕弄成自己的。
让她成为自己的女人,让她在现实中为他操持家庭,爱他,照顾他,等条件成熟的时候为他生个孩子也无不可。作为回报,他会给她优渥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的经济保障,当然还有她那个傻弟弟,那孩子嗓音不错,找专人教授一番再炒作一把,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小投资。
穆昱宇忽然就兴奋起来,他在脑子里迅速开始盘算如何实施这个目标的相应步骤,越想越激动,几乎忍不住就想立即实施。但多年的从商经验迫使他在越兴奋的时候越要保持冷静,于是他想了想,先分出轻重缓急,首先给离婚律师打电话,慷慨地在离婚条件中加了一笔一次性的赡养费,数目不多,但也不算少,目的是让叶芷澜快点签下离婚协议。其次,他给林助理打电话,让他再给倪春燕的面馆招两个人手,让她快点从那摊子事中抽出空来。最后,他想了想,又给姚根江打了个电话。
“先生。”姚根江缺乏情绪的声音响起,“对不起,您有事请尽可能简短吩咐,我太太这两天不舒服,我正在给她熬中药。”
穆昱宇愣了愣,说:“老姚,我给你打是公事,你熬药是私事,你这是公私不分。”
“中药是讲究火候和放药时间的,错过了药性就会减弱。”姚根江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要继续给您科普这些常识吗?”
穆昱宇没好气地说:“甭跟我废话了,我想知道最近叶芷澜那边的动静。”
“她学精明了,最近都单身。”
“这可奇怪了,难道你没将她可能分我一半身家的消息散播出去?”
“有,不少青年才俊信以为真,但叶芷澜大概得到高人指点,这段期间没出半点错,她每天的作息很规律,规律到奇怪的程度。”
“怎么讲?”
“因为她从来不是这种人。”姚根江说,“这点先生您也知道。”
“反常必妖。”穆昱宇冷笑了一下,“安排几个狗仔队,我跟她见见面时让人偷拍两张,至于他们该怎么写,你心里有数。”
“是。”
“老姚,你这样有意思吗?”穆昱宇突然问,“成天围着老婆转,这日子过得真那么有劲?”
姚根江的声音暖了不少,似乎还带着笑意:“我觉得挺有意思。”
穆昱宇沉默了,随后骂了句:“没出息。”
“谢谢。”
穆昱宇挂了电话,又想了想,再次打给林助理,让他帮自己约叶芷澜,顺带找个静僻点的地方,他还没吩咐完,突然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随后,书房的门被人敲响,余嫂的声音带着颤抖说:“先生,出了点事,我需要跟您汇报。”
穆昱宇皱了眉头,挂上电话,冷冷地说:“进来。”
余嫂紧绷着脸走进来,神情是前所未有的严肃:“先生,我发现原先挂在休憩室的一幅画被人偷了。”
穆昱宇想了一会没想起那是谁的作品,他不喜欢现代抽象画,看不懂,看着也闹心。但他记得价格,那是在春季拍卖会上别人拍下来贿赂他的,总价超过一百万。
这笔钱足以让一个普通人铤而走险了。
穆昱宇直觉认为这个事不简单,宅子里最多的就是保全人员,三班轮换,还装了先进的监测系统,一般贼要偷这个几乎不可能,高明的贼又不该花大工夫偷这么不上不下的东西,他盯着余嫂半响后,淡淡地问:“你是说有内贼?”
“是的,”余嫂带着压抑的怒气说。
“找到了?”
“找到了。”余嫂说,“东西还在,人我让他们看起来了。”
“报警吧。”穆昱宇漫不经心地说,“敢偷东西,就得付出代价。”
“可是先生,”余嫂犹豫着说,“警察一来,那个人也就完了,这事说出去也不好听。而且大家毕竟一场同事,我是想着,咱们把东西追回来,把人开除了就算了,我相信那个人也是一时糊涂而已。”
“你倒好心,”穆昱宇淡淡笑了笑,问:“谁偷的?”
“是,”余嫂停了停,低声说,“孙福军。”
穆昱宇微微吃了一惊,瞪大眼睛看她。
“真是他,我也没想到,可厨房的人看见他三更半夜鬼鬼祟祟去休憩室,而且我刚刚带人过去,画就在他床底下搜到,”余嫂急忙说,“我问过他了,他承认是他偷的,我还听说他乡下的父亲生病了住院,是肝癌,治起来得花不少钱,他这么铤而走险,也是能理解……”
穆昱宇皱起眉头,他想了想问:“他在哪?”
“我已经开除他了。”
穆昱宇站了起来,瞪着余嫂,随后淡淡地说:“你居然没问过我就把我的员工开除,你能耐大了你……”
余嫂白了脸,颤声说:“先生……”
“他要还没出这个大门,就让他过来,要走了,你就给我把他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