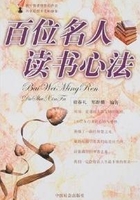一朝
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读《红楼梦》,似懂非懂,读到林黛玉葬花的那一段,以及她的《葬花词》,里面有这样几句: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落花也会令人忧伤,而人对落花也像待人一样,有深刻的情感。那时当然不知道林黛玉的自伤之情胜过于花朵的对待,但当时也起了一点疑情,觉得林黛玉未免小题大作,花落了就是落了,有什么值得那样感伤,少年的我正是“侬今葬花人笑痴”那个笑她的人。
我会感到葬花好笑是有背景的,那时候父亲为了增加家用,在田里种了一亩玫瑰,因为农会的人告诉他,一定有那么一天,一朵玫瑰的价钱可以抵上一斤米。可惜父亲一直没有赶上一朵玫瑰一斤米的好时机,二十几年前的台湾乡下,根本不会有人神经到去买玫瑰来插。父亲的玫瑰是种得不错,却完全滞销,弄到最后懒得去采收了,一时也想不出改种什么,玫瑰田就荒置在那里。
我们时常跑到玫瑰田去玩,每天玫瑰花瓣,黄的、红的、白的落了一地,用竹扫把一扫就是一畚箕,到后来大家都把扫玫瑰田当成苦差事,扫好之后顺手倒入田边的旗尾溪,千红万紫的玫瑰花瓣霎时铺满河面,往下游流去,偶尔我也能感受到玫瑰飘逝的忧伤之美,却绝对不会痴到去葬花。
不只玫瑰是大片大片的落,在我们山上,春天到秋天,坡上都盛开着野百合、野姜花、月桃花、美人蕉,有时连相思树上都是一片白茫茫,风吹来了,花就不可计数地纷飞起来。山上的孩子看见落花流水,想的都是节气的改变,有时候压根儿不会想到花,更别说为花伤情了。
只有一次为花伤心的经验,是有一年父亲种的竹子突然有十几丛开花了,竹子花真漂亮,细致的、金黄色的,像满天星那样怒放出来,父亲告诉我们,竹子一开花就是寿限到了,花朵盛放之后,就会干枯,死去。而且通常同一母株育种的竹子会同时开花,母亲和孩子会同时结束生命。那时我每到竹林里看极美丽绝尘不可逼视的竹子花就会伤心一次,到竹子枯死的那一阵子,总会无端的落下泪来,不过,在父亲插下新枝后,我的伤心也就一扫而空了。
多几次感受到竹子开花这样的经验,就比较知道林黛玉不是神经,只是感受比常人敏锐罢了,也慢慢能感受到“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坵?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那种借物抒情,反观自己的情怀。
长大一点,我更知道了连花草树木都与人有情感、有因缘,为花草树木伤春悲秋,欢喜或忧伤是极自然的事,能在欢喜或悲伤时,对境有所体会观照,正是一种觉悟。
最近又重读了《红楼梦》,就体会到花草原是法身之内,一朵花的兴谢与一个人的成功失败并没有两样,人如果不能回到自我,做更高智慧之追求,使自己明净而了知自然的变迁,有一天也会像一朵花一样在无知中凋谢了。
同时,看一片花瓣的飘落,可以让我们更深地感知无常,正如贾宝玉在山坡上听见黛玉的葬花诗“不觉恸倒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那是他想到黛玉的花容月貌终有无可寻觅之时,又推想到宝钗、香菱、袭人亦会有无可寻觅之时,当这些人都无可寻觅,自己又安在呢?自身既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
看看这种无常感,怎么能不恸倒在山坡上?我觉得,整部《红楼梦》就在表达“人生如梦”四字,这是一种无可如何的无常,只是借黛玉葬花来说,使我们看到了无常的焦点。《红楼梦》还有一支曲子,我非常喜欢,说的正是无常: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从落花而知大地有情,这是体会;从葬花而知无常苦空,这是觉悟;从觉悟中知道万法了不可得,应该善自珍摄,不要空来人间一回,这就是最初步的菩提了。读《红楼梦》不也能使我们理解到青原惟信禅师说的:“三十年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后亲见亲知,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如今得个休歇处,依旧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过程吗?
相传从前有一位老僧,经卷案头摆了一部《红楼梦》,一位居士去拜见他,感到十分惊异问他:“和尚也喜欢这个?”
老僧从容地说:“老僧凭此入道。”
这虽是传说,但也不无道理,能悟道的,黄花翠竹、吃饭睡觉、瓦罐瓶杓都会悟道了,何况是《红楼梦》!
虽然《红楼梦》和“悟道”没有必然关系,但只要时时保有菩提之心,保有反观的觉性,就能看出在言情之外言志的那一部分,也可以看到隐在小儿女情意背后那广大的空间。
知悉了大地有情、觉悟了无常苦空、体会了山水的真实、保有了清明的菩提,我们如何继续前行呢?正是“一朝春尽红颜老”的那个“一朝”,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一朝”,是知道“放弃今日就没有来日,不惜今生就没有来生”!是“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是“当下即是”!是“人圆即佛成”!
那么就在每一个“一朝”中保有菩提,心田常开智慧之花,否则,像竹子一样要等到临终才知道盛放,就来不及了。
油面摊子
家附近有一担卖油面的小摊子,我平常并不太注意,有一回带孩子散步路过,看到生意极好,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人。
我和孩子驻足围观,这时见到卖面的小贩,把油面放进烫面用的竹捞子里,一把塞一个,刹那之间就塞了十几把,然后他把叠成长串的竹捞子放进锅里烫。
接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十几个碗一字排开,放作料、盐、味素等等,很快地捞面、加汤,十多碗面煮好的过程还不到五分钟,我和孩子都看呆了。更令人赞叹的是,那个煮面的老板还边煮边与顾客聊着闲天。
在我们从面摊离开的时候,孩子突然抬起头来说:“爸爸,我猜如果你和卖面的老板比赛卖面,你一定输!”
对于孩子突如其来的谈话,我感到莞尔,并且立即坦然承认,我一定输给卖面的人。我说:“不只会输,而且会输得很惨,这个世界上能赢过卖面老板的人大概也没有几个。”
后来我和孩子谈起了,他的爸爸在这世界上是输给很多人的。
接下来的几天,就玩着游戏一样,我带着孩子到处去看工作中的人,我们在对角的豆浆店看伙计揉面粉做油条,看油条在锅中胀大而充满神奇的美感,我对孩子说:“爸爸比不上炸油条的人。”
我们到街角的饺子店,看一位山东老乡包饺子,他包饺子就如同变魔术一样,动作轻快,双手一捏,个个饺子大小如一,煮出来晶莹剔透,我对孩子说:“爸爸比不上包饺子的人。”
我们在市场边看见一个削梨子与芭乐的小贩,他把水果削好切片,包成一袋一袋准备推到戏院去卖,他削水果时,刀子如同自手中长出,动作又利落、又优美,我对孩子说:“爸爸比不上削水果的人。”
就在我们生活四周,到处都是我比不上的人,这些市井小人物,他们过着单纯的生活,对生命有着信心与希望,他们的手艺固然简单,却非数十年的锻炼不能得致。
当我们放眼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很可能会以为自己是顶尖人物,一旦我们把狂心歇息下来,用赤子之心来观照,就会发现自己是多渺小,在人群之中,若没有整个市井的护持,我们连吃一套烧饼油条都成问题呀!这是为什么连圣贤都感叹地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的缘故,我们什么时候能看清自己不如人的地方,那就是对生命有真正信心的时候。
看到人们貌似简单,事实上不易的生活动作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值得给予最大的敬意,努力生活的人们都是可敬佩的。他们不用言语,而以动作表达了对生命的承担。
承担,是生命里最美的东西!
我时常想,我们既然生而为人,不是草木虫鱼,就要承担,安然接受人生可能发生的一切,除了安然地面对,还能保持觉性,就是菩提了。一般人缺少的正是觉悟的菩提罢了。
在古印度人传统的观念里,认为只要是两条河交会的地方一定是圣地,这是千年智慧累积所得到的结论。假如我们把这个观念提炼出来,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在人与人相会面的那一刻,如果都有很好的心来相印,互相对流,当下自己的心就是圣地了。
油面摊子是圣地,豆浆店是圣地,饺子馆是圣地,水果摊是圣地……到处都是圣地,只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神圣的心来对应这些人、这些地方。当然,在我们以神圣的心面对世界时,自己就有了承担,也就成为值得敬佩的人之一。
我带着孩子观察了许多人以后,孩子感到疑惑,他问:“爸爸,那么你有什么可以比得上别人呢?”
我说:“如果比写文章,爸爸可能会比得上那卖油面的老板吧!”
孩子说:“也不会,油面老板几分钟煮好十几碗面,爸爸要很久才写完一篇文章!”
父子俩相对大笑,是呀!这世界有什么东西可以相比,有什么人可以相比呢?事实上,所有的比较都是一种执著!
只手之声
如果要我选一种最喜欢的花的名字,我会投票给一种极平凡的花:“含笑”。
说含笑花平凡是一点也不错,在乡下,每一家院子里它都是不可少的花,与玉兰、桂花、七里香、九重葛、牵牛花一样,几乎是随处可见,它的花形也不稀奇,拇指大小的椭圆形花隐藏在枝叶间,粗心的人可能视而不见。
比较杰出的是它的香气,含笑之香非常浓盛,并且清明悠远,邻居家如果有一棵含笑开花,香气能飘越几里之远,它不像桂花香那样含蓄,也不如夜来香那样跋扈,有点接近玉兰花之香,潇洒中还保有风度,维持着一丝自许的傲慢。含笑虽然十分平民化,香味却是带着贵气。
含笑最动人的还不是香气,而是名字,一般的花名只是一个代号,比较好的则有一点形容,像七里香、夜来香、百合、夜昙都算是好的。但很少有花的名字像含笑,是有动作的,所谓含笑,是似笑非笑,是想笑未笑,是含羞带笑,是嘴角才牵动的无声的笑。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看见含笑开了,我从院子跑进屋里,见到人就说:“含笑开了,含笑开了!”说着说着,感觉那名字真好,让自己的嘴也禁不住带着笑,又仿佛含笑花真是因为笑而开出米白色没有一丝杂质的花来。
第一位把这种毫不起眼的小白花取名为“含笑”的人,是值得钦佩的,可想而知,他一定是在花里看见了笑意,或者自己心里饱含喜悦,否则不可能取名为含笑。
含笑花不仅有象征意义,也能贴切说出花的特质,含笑花和别的花不同,它是含苞时最香,花瓣一张开,香气就散走了。而且含笑的花期很长,一旦开花,从春天到秋天都不时在开,让人感觉到它一整年都非常喜悦,可惜含笑的颜色没有别的花多彩,只能算含蓄地在笑着罢了。
知道了含笑种种,使我们知道含笑花固然平常,却有它不凡的气质和特性。
但我也知道,“含笑”虽是至美的名字,这种小白花如果不以含笑为名,它的气质也不会改变,它哪里在乎我们怎么叫它呢?它只是自在自然地生长,并开花,让它的香远扬而已。
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事物都与含笑花一样,有各自的面目,外在的感受并不会影响它们,它们也从来不为自己辩解或说明,因为它们的生命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不需要任何语言。反过来说,当我们面对没有语言,沉默的世界时,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
在日本极有影响力的白隐禅师,他曾设计过一则公案,就是“只手之声”,让学禅的人参一只手有什么声音。后来,“只手之声”成为日本禅法重要的公案,他们最爱参的问题是:“两掌相拍有声,如何是只手之声?”或者参:“只手无声,且听这无声的妙音。”
我们翻看日本禅者参“只手之声”的公案,有一些真能得到启发,例如:老师问:“你已闻只手之声,将作何事?”学生答:“除杂草,擦地板,师若倦了,为师按摩。”老师问:“只手的精神如何存在?”学生答:“上拄三十三天之顶,下抵金轮那落之底,充满一切。”老师问:“只手之声已闻,如何是只手之用?”学生答:“火炉里烧火,铁锅里烧水,砚台里磨墨,香炉里插香。”老师问:“如何是十五日以前的只手,十五日以后的只手,正当十五日的只手?”学生伸出右手说:“此是十五日以前的只手。”伸出左手说:“此是十五日以后的只手。”两手合起来说:“此是正当十五日的只手。”老师问:“你既闻只手之声,且让我亦闻。”
学生一言不发,伸手打老师一巴掌。
一只手能听到什么声音呢?在一般人可能是大的迷惑,但禅师不仅听见只手之声,在最广大的眼界里从一只手竟能看见华严境界的四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有禅师伸出一只手说:“见手是手,是事法界。见手不是手,是理法界。见手不是手,而见手又是手,是理事无碍法界。一只手忽而成了天地,成了山川草木森罗万象,而森罗万象不出这只手,是事事无碍法界。”
可见一只手真是有声音的!日本禅的概念是传自中国,中国禅师早就说过这种观念。例如云岩禅师问道吾禅师说:“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做什么?”道吾说:“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云岩说:“我会也!”道吾:“汝作么生会?”云岩说:“遍身是手眼!”道吾:“道太煞道,只道得八成。”云岩说:“师兄作么生?”道吾说:“通身是手眼!”
通身是手眼,这才是禅的真意,那须仅止于只手之声?
从前,长沙景岑禅师对弟子开示说:“尽十方世界是沙门一只眼,尽十方世界是沙门全身,尽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尽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里,尽十方世界无一人不是自己。”这岂止是一只手的声音!十方世界根本就与自我没有分别。
一只手的存在是自然,一朵含笑花的开放也是自然,我们所眼见或不可见的世界,不都是自然的存在着吗?
即使世界完全静默,有缘人也能听见静默的声音,这就是“只手之声”,还有只手的色、香、味、触、法。在沉默的独处里,我们听见了什么?在噪闹的转动里,我们没听见的又是什么呢?
有的人在满山蝉声的树林中坐着,也听不见蝉声;有的人在哄闹的市集里走着,却听见了蝉声。对于后者,他能在含笑花中看见饱满的喜悦,听见自己的只手之声;对于前者,即使全世界向他鼓掌,也是惘然,何况只是一朵花的含笑呢!
不是茶
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是日本无人不晓的历史人物,他的家教非常成功,千利休家族传了十七代,代代都有茶道名师。
千利休家族后来成为日本茶道的象征,留下来的故事不计其数,其中有三个故事我特别喜欢。
千利休到晚年时,已经是公认的伟大茶师,当时掌握大权的将军秀吉特地来向他求教饮茶的艺术,没想到他竟说饮茶没有特别神秘之处,他说:“把炭放进炉子里,等水开到适当程度,加上茶叶使其产生适当的味道。按照花的生长情形,把花插在瓶子里。在夏天的时候使人想到凉爽,在冬天的时候使人想到温暖,没有别的秘密。”
发问者听了这种解释,便带着厌烦的神情说,这些他早已知道了。千利休厉声地回答说:“好!如果有人早已知道这种情形,我很愿意做他的弟子。”
千利休后来留下一首有名的诗,来说明他的茶道精神:
先把水烧开,
再加进茶叶,
然后用适当的方式喝茶,
那就是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除此以外,茶一无所有。
这是多么动人,茶的最高境界就是一种简单的动作、一种单纯的生活,虽然茶可以有许多知识学问,在喝的动作上,它却还原到非常单纯有力的风格,超越了知识与学问。也就是说,喝茶的艺术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每个人的个性与喜好,用自己“适当的方式”,才是茶的本质。如果茶是一成不变,也就没有“道”可言了。
另一个动人的故事是关于千利休教导他的儿子。日本人很爱干净,日本茶道更有着绝对一尘不染的传统,如何打扫茶室因而成为茶道艺术极重要的传承。
传说当千利休的儿子正在洒扫庭园小径时,千利休坐在一旁看着。当儿子觉得工作已经做完的时候,他说:“还不够清洁。”儿子便出去再做一遍,做完的时候,千利休又说:“还不够清洁。”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了许多次。
过了一段时间,儿子对他说:“父亲,现在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石阶已经洗了三次,石灯笼和树上也洒过水了,苔藓和地衣都披上了一层新的青绿,我没有在地上留下一根树枝和一片叶子。”
“傻瓜,那不是清扫庭园应该用的方法。”千利休对儿子说,然后站起来走入园子里,用手摇动一棵树,园子里霎时间落下许多金黄色和深红色的树叶,这些秋锦的断片,使园子显得更干净宁谧,并且充满了美与自然,有着生命的力量。
千利休摇动的树枝,是在启示人文与自然和谐乃是环境的最高境界,在这里也说明了一位伟大的茶师是如何从茶之外的自然得到启发。如果用禅意来说,悟道者与一般人的不同也就在此,过的是一样的生活,对环境的观照已经完全不一样,他能随时取得与环境的和谐,不论是秋锦的园地或瓦砾堆中都能创造泰然自若的境界。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千利休的孙子宗旦,宗旦不仅继承了父祖的茶艺,对禅也极有见地。
有一天,宗旦的好友京都千本安居院正安寺的和尚,叫寺中的小沙弥送给宗旦一枝寺院中盛开的椿树花。
椿树花一向就是极易掉落的花,小沙弥虽然非常小心地捧着,花瓣还是一路掉下来,他只好把落了的花瓣拾起,和花枝一起捧着。
到宗旦家的时候,花已全部落光,只剩一枝空枝,小沙弥向宗旦告罪,认为都是自己粗心大意才使花落下了。
宗旦一点也没有怨怪之意,并且微笑地请小沙弥到招待贵客的“今日庵”茶席上喝茶。宗旦从席上把祖父千利休传下来的名贵的国城寺花筒拿下来,放在桌上,将落了花的椿树枝插于筒中,把落下的花散放在花筒下,然后他向空花及空枝敬茶,再对小沙弥献上一盅清茶,谢谢他远道赠花之谊,两人喝了茶后,小沙弥才回去向师父复命。
宗旦是表达了一个多么清朗的境界!花开花谢是随季节变动的自然,是一切的“因”;小和尚持花步行而散落,这叫做“缘”;无花的椿枝及落了的花,一无价值,这就是“空”。
从花开到花落,可以说是“色即是空”,但因宗旦能看见那清寂与空静之美,并对一切的流动现象,以及一切的人抱持宽容的敬意,他把空变成一种高层次的美,使“色即是空”变成“空即是色”。
对于看清因缘的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也就不是那么难以领会了。
老和尚、小沙弥、宗旦都知道椿树花之必然凋落,但他们都珍惜整个过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惜缘”,惜缘所惜的并不是对结局的期待,而是对过程的宝爱呀!
在日本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茶师都是学禅者,他们都向往沉静、清净、超越、单纯、自然的格局,一直到现代,大家都公认不学禅的人是没有资格当茶师的。
因此,关于茶道,日本人有“不是茶”的说法,茶道之最高境界竟然不是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们透过茶,是在渴望着什么,简单地说,是渴望着渺茫的自由,渴望着心灵的悟境,或者渴望着做一个更完整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