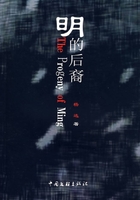黄昏月娘要出来的时候
开车从大溪到莺歌的路上,黄昏悄悄来临了,原本澄明碧绿的山景先是被艳红的晚霞染赤,然后在山风里静静地黯淡下来,大汉溪沿岸民房的灯盏一个一个被点亮。
夏天已经到了尾声,初秋的凉风从大汉溪那头绵绵地吹送过来。
我喜欢黄昏的时候,在乡间道路上开车或散步,这时可以把速度放慢,细细品味时空的一些变化,不管是时间或空间,黄昏都是一个令人警醒的节点,在时间上,黄昏预示了一天的消失,白日在黑暗里隐遁,使我们有了被时间推迫而不能自主的悲感;在空间上,黄昏似乎使我们的空间突然缩小,我们的视野再也不能自由放怀了,那种感觉就像电影里的大远景被一下子跳接到特写一般,我们白天不在乎的广大世界,黄昏时成为片段的焦点——我们会看见橙红的落日、涌起的山岚、斑灿的彩霞、墨绿的山线、飘忽的树影,都有如定格一般。
事实上,黄昏与白天、黑夜之间并没有断绝,日与夜的空间并不因黄昏而有改变,日与夜的时间也没有断落,那么,为什么黄昏会给我们这么特别的感受呢?欢喜的人看见了黄昏的优美,苦痛的人看见了黄昏的凄凉;热恋的人在黄昏下许诺誓言;失恋的人则在黄昏时看见了光明绝望的沉落。
就像今天开车路过乡间的黄昏,坐在我车里的朋友都因为疲倦而沉沉睡去了,穿过麻竹防风林的晚风拍打着我的脸颊,我感觉到风的温柔、体贴与优雅,黄昏的风是多么静谧,没有一点声息。突然一轮巨大明亮的月亮从山头跳跃出来,这一轮月亮的明度与巨大,使我深深地震动,才想起今天是农历六月十八日,六月的明月是一点也不逊于中秋。
我说看见月亮的那一刻使我深深震动,一点也不夸张,因为我心里不觉地浮起两句有一些忧伤的歌词:
每日黄昏月娘要出来的时候
加添阮心内的悲哀
这两句歌词是一首闽南语歌《望你早归》的歌词,记得它的原作曲者杨三郎先生曾说过他作这首歌的背景,那时台湾刚刚光复,因为经历了战乱,他想到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离散在外,凡有人离散在外,就会有思念的人,而思念,在黄昏夜色将临时最为深沉和悠远,心里自然有更深的悲意,他于是自然地写下了这一首动人的歌,我最爱的正是这两句。
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战乱离散的悲剧不再和从前一样,但是大家还是爱唱这首歌,原因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埋藏着远方的人呀!我觉得在人的情感之中,最动人的不一定是死生相许的誓言,也不一定是缠绵悱恻的爱恋,而是对远方的人的思念。因为,死生相许的誓言与缠绵悱恻的爱恋都会破灭、淡化,甚至在人生中完全消失,唯有思念能穿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永久在情感的水面上开花,犹如每日黄昏时从山头升起的月亮一样。
远方的思念是情感中特别美丽的一种,可惜在这个时代的人已经逐渐消失了这种情感,就好像愈来愈少人能欣赏晚上的月色、秋天的白云、山间的溪流一般,人们总是想,爱就要轰轰烈烈,要情欲炽盛,要合乎时代的潮流,于是乎,爱的本质就完全的改变了。
思念的情感不是如此,它是心中有情,但眼睛犹能穿透情爱有一个清明的观点。一如太阳在白云之中,有时我们看不见太阳,而大地仍然是非常明亮,太阳是永远在的,一如我们所爱的人,不管他是远离、是死亡、是背弃,我们的思念永远不会失去。
佛经里告诉我们:“生为情有”,意思是人因为有情才会投生到这个世界。因此凡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必然会有许多情缘的纠缠,这些情缘使我们在爱河中载沉载浮,使我们在爱河中沉醉迷惑,如果我们不能在情爱中维持清明的距离,就会在情与爱的推迫之下,或贪恋、或仇恨、或愚痴、或苦痛、或堕落、或无知地过着一生。
尤其是情侣的失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了,通常,情感失散的时候会使我们愁苦、忧痛,甚至怀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愁苦、忧痛、怀恨都不能挽救或改变失散的事实,反而增添了心里的遗憾。有时我们会感叹,为什么自己没有菩萨那样伟大的情怀,能站在超拔的海面晴空丽日之处,来看人生中波涛汹涌如海的情爱。
其实也没有关系,假如我们不能忘情,我们也可以从情爱中拔起身影,有一个好的面对,这种心灵的拔起,即是以思念之情代替憾恨之念,以思念之情转换悲苦的心。思念虽有悲意,但那样的悲意是清明的,乃是认识了人生的无常、情爱不能永驻之实相,对自我、对人生、对伴侣的一种悲悯之心。
释迦牟尼佛早就看清了人间有免不了的八苦,就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所求不得、烦恼炽盛,这八苦的来由,归纳起来,就是一个“情”字,有情必然有苦,若能使情成为思念的流水,则苦痛会减轻,爱恨不至于使我们窒息。
我们都是薄地的凡夫,我很喜欢“凡夫”这两个字,凡夫的“凡”字中间有一颗大心,凡夫之所以永为凡夫,正是多了一颗心,这颗心有如铅锤,蒙蔽了我们自性的清明,拉坠使我们堕落,若能使凡夫之心有如黄昏时充满思念的明月,则即使有心,也是无碍了。能以思念之情来转换情爱失落败坏的人,就可以以自己为灯,作自己的归依处,纵是含悲忍泪,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光明。
佛陀曾说:“情感是由过去的缘分与今世的怜爱所产生,宛如莲花是由水和泥土这两样东西所孕育。”是的,过去的缘分是水,今生的怜爱是泥土,然后开出情感的莲花。
人的情感如果是莲花,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染着。假如我们会思念、懂得思念、珍惜思念,我们的思念就会化成情感莲花上清明的露水,在清晨或黄昏,闪着眩目的七彩。
每日黄昏月娘要出来的时候
加添阮心内的悲哀
我轻轻地唱起了这首《望你早归》的思念之歌,想象着这流动在山林中的和风,有可能是我们思念的远方的人轻轻地呼吸,在千山万水之外,在千年万岁之后,我们的思念是一枚清楚的戳印,它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失前世的尘缘;它让我们转入未来的时空,还带着今生的记忆。
引动我们悲意的月亮,如果我们能清明,也会使我们心中的明月在乌云密布的山水之间升起。
我想起两句偈:
心清水现月意定天无云
然后我踩下油门,穿过林间的小路,让风吹过,让月光肤触,心中响着夜曲一般小提琴的声音,琴声围绕中还有一盏灯火,我自问着:远方的人不知听不听得见这思念的琴声?不知看不看得见这光明的灯盏?
你呢?你听见了吗?你看见了吗?
朋友的情义是难以表明的,它在某些质地上比男女的爱情还要细致,若说爱情是彩陶,朋友则是白瓷。
怀君与怀珠
在清冷的秋天夜里,我穿过山中的麻竹林,偶尔抬头看见了金黄色的星星,一首韦应物的短诗从我的心头流过: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
我很为这瞬间浮起的诗句而感到一丝震动,因为我到竹林,并不是为了散步,而是到一间寺院的后山玩,不觉间天色就晚了(秋天的夜有时来得出奇的早),我就赶着回家的路,步履是有点匆忙的。并且,四周也没有幽静到能听见松子的落声,根本是没有一株松树的,耳朵里所听见的是秋风飒飒的竹叶(夜里有风的竹林还不断发出伊伊歪歪的声音),为什么这一首诗会这样自然地从心田里开了出来?
也许是我走得太急切了,心境突然陷于空茫,少年时期特别钟爱的诗就映现出来了。
我想起了上一次这首诗流出心田的时空,那是前年秋天我到金门去,夜里住在招待所里,庭院外种了许多松树,金门的松树到秋冬之际会结出许多硕大的松子。那一天,我洗了热乎乎的澡,正坐在窗前擦拭湿了的发,忽然听见院子里传来哔哔剥剥的声音,我披衣走到庭中,发现原来是松子落地的声音,“呀!原来松子落下的声音是如此的巨大!”我心里轻轻地惊叹着。
捡起了松子捧在手上,韦应物的诗就跑出来了。
于是,我真的在院子里独自地散步,虽然不在空山,却想起了从前的、远方的朋友,那些朋友有许多已经多年不见了,有一些也失去了消息,可是在那一刻仿佛全在时光里会聚。一张张脸孔,清晰而明亮。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平凡的,几乎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在静夜里想到曾经一起成长的朋友,却觉得生活是可歌可泣的。
我们在人生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其实是一种老去),会发现每一个阶段都拥有了不同的朋友,友谊虽不至于散失,聚散却随因缘流转,常常转到我们一回首感到惊心的地步。比较可悲的是,那些特别相知的朋友往往远在天际,泛泛之交却在眼前,因此,生活里经常令我们陷入一种人生寂寥的境地。“会者必离”,“当门相送”,真能令人感受到朋友的可贵,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感觉到能相与共话的,只有手里的松子,或者只有林中正在落下的松子!
在金门散步的秋夜,我还想到《菜根谭》里的几句话:“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朋友的相聚,情侣的和合,有时心境正是如此,好像风吹过了竹林,互相有了声音的震颤,又仿佛雁子飞过静止的潭面,互相有了影子的照映,但是当风吹过,雁子飞离,声音与影子并不会留下来。可惜我们做不到那么清明一如君子,可以“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却留下了满怀的惆怅、思念,与惘然。
平凡人总有平凡人的悲哀,这种悲哀乃是寸缕缠绵,在撕裂的地方、分离的处所,留下了丝丝的穗子。不过,平凡人也有平凡人的欢喜,这种欢喜是能感受到风的声音与雁的影子,在吹过飞离之后,还能记住一些椎心的怀念与无声的誓言。悲哀有如橄榄,甘甜后总有涩味;欢喜则如梅子,辛酸里总有回味。
那远去的记忆是自己,现在面对的还是自己,将来不得不生活的也是自己,为什么在自己里还有另一个自己呢?站在时空之流的我,是白马还是芦花?是银碗或者是雪呢?
我感觉怀抱着怀念生活的人,有时候像白马走入了芦花的林子,是白茫茫的一片;有时候又像银碗里盛着新落的雪片,里外都晶莹剔透。
在想起往事的时候,我常惭愧于做不到佛家的境界,能对境而心不起,我时常有的是对于逝去的时空有一些残存的爱与留恋,那种心情是很难言说的,就好像我会珍惜不小心碰破口的茶杯,或者留下那些笔尖磨平的钢笔;明知道茶杯与钢笔都已经不能用了,也无法追回它们如新的样子。但因为这只茶杯曾在无数的冬夜里带来了清香和温暖,而那支钢笔则陪伴我度过许多思想的险峰,记录了许多过往的历史,我不舍得丢弃它们。
人也是一样,对那些曾经有恩于我的人,那些曾经爱过我的朋友,或者那些曾经在一次偶然的会面启发过我的人,甚至那些曾践踏我的情感,背弃我的友谊的人,我都有一种不忘的本能。有时不免会苦痛地想,把这一切都忘得干净吧!让我每天都有全新的自己!可是又觉得人生的一切如果都被我们忘却,包括一切的忧欢,那么生活里还有什么情趣呢?
我就不断地在这种自省之中,超越出来,又沦陷进去,好像在野地无人的草原放着风筝,风筝以竹骨隔成两半,一半写着生命的喜乐,一半写着生活的忧恼,手里拉着丝线,飞高则一起飞高,飘落就同时飘落,拉着线的手时松时紧,虽然渐去渐远,牵挂还是在手里。
但,在深处里的疼痛,还不是那些生命中一站一站的欢喜或悲愁,而是感觉在举世滔滔中,真正懂得情感,知道无私地付出的人,是愈来愈少见了。我走在竹林里听见飒飒的风声,心里却浮起“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的句子正是这样的心情。
韦应物寄给朋友的这首诗,我感受最深的是“怀君”与“幽人”两词,怀君不只是思念,而有一种置之怀袖的情致,是温暖、明朗、平静的,当我们想起一位朋友,能感到有如怀袖般贴心,这才是“怀君”!而幽人呢?是清雅、温和、细腻的人,这样的朋友一生里遇不见几个,所以特别能令人在秋夜里动容。
朋友的情义是难以表明的,它在某些质地上比男女的爱情还要细致,若说爱情是彩陶,朋友则是白瓷,在黑暗中,白瓷能现出它那晶明的颜色,而在有光的时候,白瓷则有玉的温润,还有水晶的光泽。君不见在古董市场里,那些没有瑕疵的白瓷,是多么名贵呀!
当然,朋友总有人的缺点,我的哲学是,如果要交这个朋友,就要包容一切的缺点,这样,才不会互相折磨、相互受伤。
包容朋友就有如贝壳包容珍珠一样,珍珠虽然宝贵而明亮,但它是有可能使贝舌受伤的,贝壳要不受伤只有两个法子,一是把珍珠磨圆,呈现出其最温润光芒的一面;一面是使自己的血肉更柔软,才能包容那怀里外来的珍珠。前者是帮助朋友,使他成为“幽人”,后者是打开心胸,使自己常能“怀君”。
我们在混乱的世界希望能活得有味,并不在于能断除一切或善或恶的因缘,而要学习怀珠的贝壳,要有足够广大的胸怀来包容,还要有足够柔软的风格来承受!
但愿我们的父母、夫妻、儿女、伴侣、朋友都成为我们怀中的明珠,甚至那些曾经见过一面的、偶尔擦身而过的、有缘无缘的人都成为我怀中的明珠,在白日、在黑夜都能散放互相映照的光芒。
在空中我看见年轻的自己正在路上,身影极小,吹着口哨,哨音里有忧伤凄楚的调子。
无常两则
我们认识的第一个秋天
我们认识的第一个秋天,确是在这里,我在巷子里走了很久才认出来。
我们曾坐在一起看云的阶梯,现在已经完全崩坏了,只剩下一些石块的残迹。
我们曾站着彻夜谈天的那一棵凤凰木,有半边的枝桠被雷劈断了,另一边零落地开着花。
我们曾无数次在黄昏走过的草地,现在是一排灰色的公寓,上面装满了锈去的铁窗,以及努力从铁窗探头的盆栽植物。
我们曾在湖边谈诗的榕树不见了,湖已完全填平,现在是一个养鸡场。
这些都不是我认出这个地方的理由,我认出这个地方是因为偶然走过,而又有一些当年秋天的心情。还有那一年刚种上去的相思树,现在开满鹅黄色的小花,那相思树虽长大开花,树形一点也没有改变。
站在相思树前,我的心情和那绒绒的黄花一样茫然,我的思绪被这种茫然一把抓住,使我对自己、对青春的岁月感到非常陌生,不敢确定我是不是真的认识过自己或认识过你,那种感觉,仿佛有一条蛇从心头轻轻地滑过去。
我们认识的第一个秋天,竟是在这里吗?
离去的小路
这竟是当年你离去的那一条小路吗?阶梯上的榕树还是原来的样子(似乎又老了一些),路旁的金急雨花仍然盛开(仿佛没有从前那么艳黄),巷子口的路灯也在原来的位置(如若缺乏昔日的光明),你家的窗口还是有我熟悉的灯光(但是窗帘好像换过了)。
这竟是当年你离去的那一条小路吗?你说过你不是轻易道别的人(你的话总像春天的风吹过),你说过你愿意一生只爱一次(你的誓言有如夏日午后的西北雨),你常常用泪来印证某些情爱的不朽(你的泪轻忽得似秋日流过的浮云),你说天下总会有一种永恒的情意(你这样说时,就像很冷很冷的冬天清晨我们口中所呼出的雾气)。
这竟是当年你离去的那一条小路吗?我试着用年轻时欢跃的碎步来走(但我已胖了),我试着以深深的呼吸来探触(但空气污染了),我试着想象你的的唇、你的表情、你的气息、你的五官(但真像电影的柔焦镜头,带着模糊的一种忧郁)。
这竟是我看着你离去的小路吗?我看到红砖已全部换新了,路竟像自己走了起来,我站着,让路带着我,然后我们高高地飞起。
在空中我看见年轻的自己正在路上,身影极小,吹着口哨,哨音里有忧伤凄楚的调子。
人死了,爱情不死,总比爱情死了,人还活着更有动人的质地。